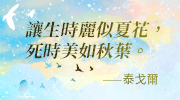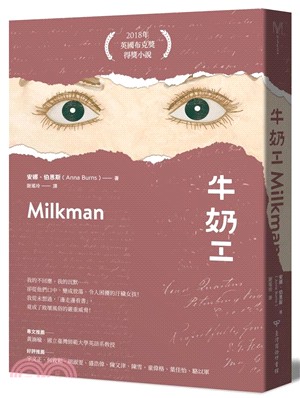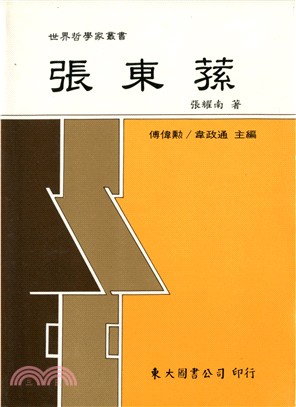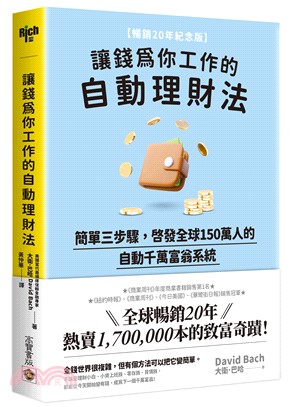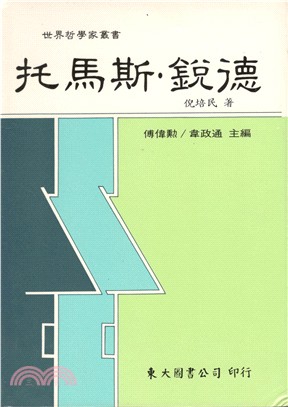開著房車走北美:歷時三年北美野生圈生動紀實(簡體書)
商品資訊
人民幣定價:36.8 元
定價
:NT$ 221 元優惠價
:87 折 192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商品簡介
《開著房車走北美》內容簡介:世界到底有多美?我們根本說不清。她開著房車游走在北美的土地上,以一種特別的旅行方式感受自然之美。她觀察野生動物,觀賞野生植物,關注那些熱愛自然的人,然後通過這樣一本小書,讓備受現實生活壓力的我們跟著她一起突圍出水泥森林,用奢侈的體驗方式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文字往往更能給人一種無邊無際的想象空間,融融的文字引領著我們涉足從未見過的野生環境,仿佛那排成兩隊整齊前行的野豬部隊正從面前經過,而抬頭的瞬間又看到藍鳥夫婦為了保護雛鳥四處制造假象,蒙蔽那些想靠近他們鳥屋的人們……《開著房車走北美》一書記錄了作者三年來的野外紀實,靈動真切的語言讓你有透過文字身臨野外的感覺,大量高清晰度的照片真實展現了野外景物。我們都有兩只眼睛,很多人被現實紛擾阻撓,無暇去了解身邊的世界有多美。而融融比我們多長了一只眼睛。第三只眼睛來自心靈,來自對自然的熱愛、敏感和默契。人不能脫離自然而談論,人與自然中的生物是平等的,自然的偉大,造物的神奇,生命的感應,這一切都能在融融的文字里感受到。眼睛掃過這些文字,口中輕輕念出聲音,一起來看世界到底有多美。
作者簡介
融融,著名美籍華人作家,祖籍上海,早年留學夏威夷,後遷居美國,自1997年開始文學創作以來,先後在《世界日報》、《僑報》、《星島日報》等大型中文報刊發表書評、隨筆、游記、影評、小說等百萬字。2003年起為星島日報副刊等多家美國知名刊物專欄作家。美國輕舟出版社主編。其散文以自然文學和野外攝影為特色,被海內外多家報紙雜志選用,獲得多國媒體好評。著有長篇小說《素素的美國戀情》《夫妻筆記》《中國棄嬰愛蜜麗》;文化散文集《吃一道美國風情菜》《天涯志異》等多部。主編《一代飛鴻——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精選和點評》《我和洋老板的故事》《吃到天涯》等。其中,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棄嬰愛蜜麗》獲得美國東方文學華文佳作獎,短篇小說《早安,野熊先生!》被上海文藝出版社收入《中國留學生文學大系》。短篇小說《海上生明月》獲2007年海外新移民華語短篇小說“情為何物”大賽二等獎。
序
“文學即人學”曾是個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基本文學理論”。它本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以人為本”思潮的理論概述。而中國文人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提倡的“新文化”運動把人文主義的種種思想又進一步簡化為口號,就使“文學即人學”成了深入人心的一種偏見。把原來頗為廣泛的文學概念限定為自戀的獨白。時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在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壓力下,悄悄地放棄了這口號和理論偏見,再回過頭來重讀幾千年的文學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學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先民總是沿著河流創建他們的文明,而與我們共同生存的飛禽走獸也逐水草而居,是我們的緊鄰,是我們的生活伙伴、朋友——當然也難免淪為給我們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正如我們也有可能淪為它們的食物一樣。這種亦敵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關系注定了我們人類行為之一——文學活動——不可能把它們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將我們與它們連在一起的那張疏而不漏的生態大網排除在外。翻開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章第一篇,我們看到的首先是與我們共享自然棲息地的水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我們沿河而居,雎鳩則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動催促鳥兒為物種繁衍而歡唱求偶,而它們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類生命的共鳴,就有了緊接在後面的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一章曾被“以君為本”的文人處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頌“後妃之德”;後來信奉“以人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擊了這種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學術語,說這兩句詩是“賦、比、興”中的一個“興”字,以水鳥為“引子”,“興”起對人間男歡女愛的熱烈謳歌。這樣一來,本來平行、平等的人鳥關系一下子就變成了以人為主、以鳥為輔的主次關系。更有甚者,人、鳥所賴以生存的共同棲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這兩種文學解讀中都失蹤了,充其量也只變成“背景”,而失去了它們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體位置。女愛之所以值得謳歌,因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間,而是作為一個結點,與一張大網,生命之網,生態之網,人作為一個結點與在同一網上的其他結點——隨水漂浮的荇菜,關關高唱的雎鳩——相連相通,相依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間的男歡女愛;人間的男歡女愛,也豐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淪為背景,這張網頂多就是一張花花綠綠的幕布,只能為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悲、喜、鬧劇提供呆板無言的陪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古文學作品竟能和現代先進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態文學的稱號。可惜的是,過去之外,凌駕于自然之上,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文學分類——自然文學,專指山水游記、田園詩文一類的作品。說它可笑,是因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學呢?因此,“自然文學”這個類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含有貶義的,因為它把文學的一個基本共性變得狹隘,使之成為只代表某類題材作品的特性。現代的環境文學概念是在自然文學的基礎上發生、發展出來的。囿于個人認知范圍,這里只談一談用英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中從狹義“自然文學”向廣義“環境文學”轉化的代表作。說是轉化,其實也可看做某種意義上的回歸,即恢復上古文學天人合一,天生厚德,眾生相通相連的廣闊視角。這樣的作品吸收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還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環境文學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學家,自吉爾伯特?懷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這兩部著作問世以後,用英文寫作的環境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它們也些共同的特點,就是突出自然生態的網狀聯系,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提倡對環境壓力小的簡樸生活方式,和對自然萬物的熱愛。作家們把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代入到文學作品,宣示人并非舞臺上顧影自憐、唱獨角戲的優伶,而是一方水土養育出的蕓蕓眾生中的平等一員。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識,并可用語言文字記錄表達自己對養育萬物的那方水土的認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鏈條上有著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樣。把這些共性總結起來,作為環境文學的特征,就發現類似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稀如星鳳。從《桃花源記》到《徐霞客游記》,從《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到《北方和河》,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往往是為人類行為提供“背景”,或獵奇志異,以供文人雅士消閑“臥游”之用。但這描寫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詳細而具體的資訊激發興趣,也沒有把自然放在網狀主體的地位。換言之,當代中國文學中,“文學即人學”的影子還太深,太重。2009年的元旦,我們這個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飄起了鵝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對著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書頁,竟扇起絲絲清風,因為我不但看到了傳統中國作品中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看到了現代生態文學中對細節的重視。在“Loon媽媽”一章中,我們不但得知所謂Loons名下包含了許多亞類,而且還學到了它們的“語言”習慣:它們冬天沉默,春天鳴叫,夏天“健談”。作家不單把話語權還給了鳥類,而且暗示我們,如果我們聽不懂鳥語,那就應該認真面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給野豬拜年》一章中,我們更進一步,居然讀懂了鳥兒的歡快“肢體語言”。這一章已經觸及了生態系統的網狀聯系:虱子寄生在豬鬃里,鳥兒在豬鬃里覓食,同時為野豬解除痛癢;這一連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鏈才是鳥兒歡快的物質原因,也是我們自稱了解鳥語的證據。我們的祖先曾為了“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問題爭論不休,而這本小書里的個別章節已經初步地,雖然尚為朦朧地,看到了生態系統那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網;這網“舉華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載天地,更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帶來驅除各種污染物的陣陣清風。時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在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壓力下,悄悄地放棄了這口號和理論偏見,再回過頭來重讀幾千年的文學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學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先民總是沿著河流創建他們的文明,而與我們共同生存的飛禽走獸也逐水草而居,是我們的緊鄰,是我們的生活伙伴、朋友——當然也難免淪為給我們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正如我們也有可能淪為它們的食物一樣。這種亦敵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關系注定了我們人類行為之一——文學活動——不可能把它們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將我們與它們連在一起的那張疏而不漏的生態大網排除在外。翻開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章第一篇,我們看到的首先是與我們共享自然棲息地的水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我們沿河而居,雎鳩則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動催促鳥兒為物種繁衍而歡唱求偶,而它們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類生命的共鳴,就有了緊接在後面的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一章曾被“以君為本”的文人處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頌“後妃之德”;後來信奉“以人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擊了這種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學術語,說這兩句詩是“賦、比、興”中的一個“興”字,以水鳥為“引子”,“興”起對人間男歡女愛的熱烈謳歌。這樣一來,本來平行、平等的人鳥關系一下子就變成了以人為主、以鳥為輔的主次關系。更有甚者,人、鳥所賴以生存的共同棲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這兩種文學解讀中都失蹤了,充其量也只變成“背景”,而失去了它們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體位置。女愛之所以值得謳歌,因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間,而是作為一個結點,與一張大網,生命之網,生態之網,人作為一個結點與在同一網上的其他結點——隨水漂浮的荇菜,關關高唱的雎鳩——相連相通,相依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間的男歡女愛;人間的男歡女愛,也豐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淪為背景,這張網頂多就是一張花花綠綠的幕布,只能為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悲、喜、鬧劇提供呆板無言的陪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古文學作品竟能和現代先進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態文學的稱號。可惜的是,過去之外,凌駕于自然之上,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文學分類——自然文學,專指山水游記、田園詩文一類的作品。說它可笑,是因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學呢?因此,“自然文學”這個類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含有貶義的,因為它把文學的一個基本共性變得狹隘,使之成為只代表某類題材作品的特性。現代的環境文學概念是在自然文學的基礎上發生、發展出來的。囿于個人認知范圍,這里只談一談用英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中從狹義“自然文學”向廣義“環境文學”轉化的代表作。說是轉化,其實也可看做某種意義上的回歸,即恢復上古文學天人合一,天生厚德,眾生相通相連的廣闊視角。這樣的作品吸收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還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環境文學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學家,自吉爾伯特·懷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這兩部著作問世以後,用英文寫作的環境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它們也些共同的特點,就是突出自然生態的網狀聯系,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提倡對環境壓力小的簡樸生活方式,和對自然萬物的熱愛。作家們把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代入到文學作品,宣示人并非舞臺上顧影自憐、唱獨角戲的優伶,而是一方水土養育出的蕓蕓眾生中的平等一員。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識,并可用語言文字記錄表達自己對養育萬物的那方水土的認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鏈條上有著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樣。把這些共性總結起來,作為環境文學的特征,就發現類似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稀如星鳳。從《桃花源記》到《徐霞客游記》,從《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到《北方和河》,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往往是為人類行為提供“背景”,或獵奇志異,以供文人雅士消閑“臥游”之用。但這描寫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詳細而具體的資訊激發興趣,也沒有把自然放在網狀主體的地位。換言之,當代中國文學中,“文學即人學”的影子還太深,太重。2009年的元旦,我們這個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飄起了鵝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對著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書頁,竟扇起絲絲清風,因為我不但看到了傳統中國作品中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看到了現代生態文學中對細節的重視。在“Loon媽媽”一章中,我們不但得知所謂Loons名下包含了許多亞類,而且還學到了它們的“語言”習慣:它們冬天沉默,春天鳴叫,夏天“健談”。作家不單把話語權還給了鳥類,而且暗示我們,如果我們聽不懂鳥語,那就應該認真面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給野豬拜年》一章中,我們更進一步,居然讀懂了鳥兒的歡快“肢體語言”。這一章已經觸及了生態系統的網狀聯系:虱子寄生在豬鬃里,鳥兒在豬鬃里覓食,同時為野豬解除痛癢;這一連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鏈才是鳥兒歡快的物質原因,也是我們自稱了解鳥語的證據。我們的祖先曾為了“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問題爭論不休,而這本小書里的個別章節已經初步地,雖然尚為朦朧地,看到了生態系統那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網;這網“舉華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載天地,更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帶來驅除各種污染物的陣陣清風。時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在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壓力下,悄悄地放棄了這口號和理論偏見,再回過頭來重讀幾千年的文學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學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先民總是沿著河流創建他們的文明,而與我們共同生存的飛禽走獸也逐水草而居,是我們的緊鄰,是我們的生活伙伴、朋友——當然也難免淪為給我們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正如我們也有可能淪為它們的食物一樣。這種亦敵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關系注定了我們人類行為之一——文學活動——不可能把它們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將我們與它們連在一起的那張疏而不漏的生態大網排除在外。翻開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章第一篇,我們看到的首先是與我們共享自然棲息地的水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我們沿河而居,雎鳩則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動催促鳥兒為物種繁衍而歡唱求偶,而它們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類生命的共鳴,就有了緊接在後面的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一章曾被“以君為本”的文人處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頌“後妃之德”;後來信奉“以人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擊了這種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學術語,說這兩句詩是“賦、比、興”中的一個“興”字,以水鳥為“引子”,“興”起對人間男歡女愛的熱烈謳歌。這樣一來,本來平行、平等的人鳥關系一下子就變成了以人為主、以鳥為輔的主次關系。更有甚者,人、鳥所賴以生存的共同棲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這兩種文學解讀中都失蹤了,充其量也只變成“背景”,而失去了它們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體位置。女愛之所以值得謳歌,因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間,而是作為一個結點,與一張大網,生命之網,生態之網,人作為一個結點與在同一網上的其他結點——隨水漂浮的荇菜,關關高唱的雎鳩——相連相通,相依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間的男歡女愛;人間的男歡女愛,也豐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淪為背景,這張網頂多就是一張花花綠綠的幕布,只能為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悲、喜、鬧劇提供呆板無言的陪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古文學作品竟能和現代先進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態文學的稱號。可惜的是,過去之外,凌駕于自然之上,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文學分類——自然文學,專指山水游記、田園詩文一類的作品。說它可笑,是因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學呢?因此,“自然文學”這個類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含有貶義的,因為它把文學的一個基本共性變得狹隘,使之成為只代表某類題材作品的特性。現代的環境文學概念是在自然文學的基礎上發生、發展出來的。囿于個人認知范圍,這里只談一談用英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中從狹義“自然文學”向廣義“環境文學”轉化的代表作。說是轉化,其實也可看做某種意義上的回歸,即恢復上古文學天人合一,天生厚德,眾生相通相連的廣闊視角。這樣的作品吸收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還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環境文學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學家,自吉爾伯特·懷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這兩部著作問世以後,用英文寫作的環境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它們也些共同的特點,就是突出自然生態的網狀聯系,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提倡對環境壓力小的簡樸生活方式,和對自然萬物的熱愛。作家們把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代入到文學作品,宣示人并非舞臺上顧影自憐、唱獨角戲的優伶,而是一方水土養育出的蕓蕓眾生中的平等一員。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識,并可用語言文字記錄表達自己對養育萬物的那方水土的認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鏈條上有著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樣。把這些共性總結起來,作為環境文學的特征,就發現類似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稀如星鳳。從《桃花源記》到《徐霞客游記》,從《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到《北方和河》,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往往是為人類行為提供“背景”,或獵奇志異,以供文人雅士消閑“臥游”之用。但這描寫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詳細而具體的資訊激發興趣,也沒有把自然放在網狀主體的地位。換言之,當代中國文學中,“文學即人學”的影子還太深,太重。2009年的元旦,我們這個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飄起了鵝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對著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書頁,竟扇起絲絲清風,因為我不但看到了傳統中國作品中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看到了現代生態文學中對細節的重視。在“Loon媽媽”一章中,我們不但得知所謂Loons名下包含了許多亞類,而且還學到了它們的“語言”習慣:它們冬天沉默,春天鳴叫,夏天“健談”。作家不單把話語權還給了鳥類,而且暗示我們,如果我們聽不懂鳥語,那就應該認真面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給野豬拜年》一章中,我們更進一步,居然讀懂了鳥兒的歡快“肢體語言”。這一章已經觸及了生態系統的網狀聯系:虱子寄生在豬鬃里,鳥兒在豬鬃里覓食,同時為野豬解除痛癢;這一連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鏈才是鳥兒歡快的物質原因,也是我們自稱了解鳥語的證據。我們的祖先曾為了“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問題爭論不休,而這本小書里的個別章節已經初步地,雖然尚為朦朧地,看到了生態系統那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網;這網“舉華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載天地,更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帶來驅除各種污染物的陣陣清風。時移世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在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的壓力下,悄悄地放棄了這口號和理論偏見,再回過頭來重讀幾千年的文學史,就很容易看到古代文學作品本身根本不支持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先民總是沿著河流創建他們的文明,而與我們共同生存的飛禽走獸也逐水草而居,是我們的緊鄰,是我們的生活伙伴、朋友——當然也難免淪為給我們提供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正如我們也有可能淪為它們的食物一樣。這種亦敵亦友、相生相克、密不可分的關系注定了我們人類行為之一——文學活動——不可能把它們排除在外,更不可能把將我們與它們連在一起的那張疏而不漏的生態大網排除在外。翻開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第一章第一篇,我們看到的首先是與我們共享自然棲息地的水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我們沿河而居,雎鳩則在水中沙洲上筑巢。到了春天,生命本身的律動催促鳥兒為物種繁衍而歡唱求偶,而它們的歌唱引起了河岸上人類生命的共鳴,就有了緊接在後面的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一章曾被“以君為本”的文人處于政治目的而曲解成歌頌“後妃之德”;後來信奉“以人為本”的文人猛烈地抨擊了這種曲解,并引用了一套文學術語,說這兩句詩是“賦、比、興”中的一個“興”字,以水鳥為“引子”,“興”起對人間男歡女愛的熱烈謳歌。這樣一來,本來平行、平等的人鳥關系一下子就變成了以人為主、以鳥為輔的主次關系。更有甚者,人、鳥所賴以生存的共同棲息地——沙洲、水流、河岸——在這兩種文學解讀中都失蹤了,充其量也只變成“背景”,而失去了它們在原作品中所具有的主體位置。女愛之所以值得謳歌,因為它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但生命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間,而是作為一個結點,與一張大網,生命之網,生態之網,人作為一個結點與在同一網上的其他結點——隨水漂浮的荇菜,關關高唱的雎鳩——相連相通,相依為命。大自然生生不息之厚德,孕育了人間的男歡女愛;人間的男歡女愛,也豐富了大自然的美德。相反,一旦淪為背景,這張網頂多就是一張花花綠綠的幕布,只能為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悲、喜、鬧劇提供呆板無言的陪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古文學作品竟能和現代先進思想吻合,不愧于生態文學的稱號。可惜的是,過去之外,凌駕于自然之上,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文學分類——自然文學,專指山水游記、田園詩文一類的作品。說它可笑,是因為哪里有不涉及自然的文學呢?因此,“自然文學”這個類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含有貶義的,因為它把文學的一個基本共性變得狹隘,使之成為只代表某類題材作品的特性。現代的環境文學概念是在自然文學的基礎上發生、發展出來的。囿于個人認知范圍,這里只談一談用英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中從狹義“自然文學”向廣義“環境文學”轉化的代表作。說是轉化,其實也可看做某種意義上的回歸,即恢復上古文學天人合一,天生厚德,眾生相通相連的廣闊視角。這樣的作品吸收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有的竟然還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一些環境文學家本人就算得上自然科學家,自吉爾伯特·懷特《塞耳彭自然史》和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這兩部著作問世以後,用英文寫作的環境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它們也些共同的特點,就是突出自然生態的網狀聯系,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提倡對環境壓力小的簡樸生活方式,和對自然萬物的熱愛。作家們把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代入到文學作品,宣示人并非舞臺上顧影自憐、唱獨角戲的優伶,而是一方水土養育出的蕓蕓眾生中的平等一員。人唯一特殊的地方是具有意識,并可用語言文字記錄表達自己對養育萬物的那方水土的認知和感受。因此在自然的鏈條上有著自己特殊的位置,就像那貌似卑微的蚯蚓一樣。把這些共性總結起來,作為環境文學的特征,就發現類似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稀如星鳳。從《桃花源記》到《徐霞客游記》,從《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到《北方和河》,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往往是為人類行為提供“背景”,或獵奇志異,以供文人雅士消閑“臥游”之用。但這描寫往往缺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詳細而具體的資訊激發興趣,也沒有把自然放在網狀主體的地位。換言之,當代中國文學中,“文學即人學”的影子還太深,太重。2009年的元旦,我們這個很少下雪的地方居然飄起了鵝毛大雪;然而,白窗下對著女作家融融的文集,翻翻書頁,竟扇起絲絲清風,因為我不但看到了傳統中國作品中對自然的熱愛,同時也看到了現代生態文學中對細節的重視。在“Loon媽媽”一章中,我們不但得知所謂Loons名下包含了許多亞類,而且還學到了它們的“語言”習慣:它們冬天沉默,春天鳴叫,夏天“健談”。作家不單把話語權還給了鳥類,而且暗示我們,如果我們聽不懂鳥語,那就應該認真面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在《給野豬拜年》一章中,我們更進一步,居然讀懂了鳥兒的歡快“肢體語言”。這一章已經觸及了生態系統的網狀聯系:虱子寄生在豬鬃里,鳥兒在豬鬃里覓食,同時為野豬解除痛癢;這一連串相生相克的生物鏈才是鳥兒歡快的物質原因,也是我們自稱了解鳥語的證據。我們的祖先曾為了“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問題爭論不休,而這本小書里的個別章節已經初步地,雖然尚為朦朧地,看到了生態系統那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大網;這網“舉華岳而不重,振江海而不泄”,既能載天地,更能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帶來驅除各種污染物的陣陣清風。
目次
序 言:自然文學到環境文學 俞寧引言第一章 愛上加拿大野生圈第一節 野外攝影師第二節 瓊湖度假村(Lac Le Jeune Resort)第三節 綠色(Organic)生活第四節Loon(潛鳥)媽媽第五節 高原藍鳥第六節 天然舞臺第七節 盈盈魚水情第八節 生命的挑選——加拿大亞當斯(Adams)河觀魚回歸第二章 房車生活第一節 過暖冬第二節 奢侈旅游 純樸享受第三節 福瑪沙的白鷺 第四節 馬丁湖的神秘面紗 (Lake Martin )第五節 好也鱷魚,壞也鱷魚 (Alligators in FL)——美南驚險游第六節 沙漠綠珠——德州寶墨海公園第七節 波光 ,鳥影 ,幽徑——巖石漁港一瞥第八節 給野豬拜年 ( Happy New Year Javelina !)第三章 深入土地第一節 多一只美麗的眼睛 第二節 飛翔的寶石(Flying Gems)第三節 海豚情歌第四節 相遇荒原第五節 沙麗娜的生日第六節 人造島上的野生景觀——訪Jetty Island第七節 葉紅情濃好個秋第八節 森林的蘇醒第九節 枯樹的命運第十節 雪花爛漫四月天第十一節 西紅柿手記第十二節 賞鷹盛宴又見融融 陳瑞琳來自沃特康森林的中國女人──記北美女作家融融 張志東從買房子說開去(代後記)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