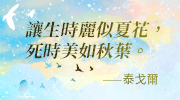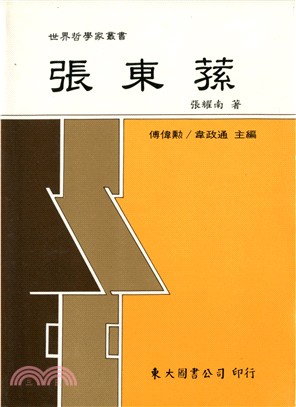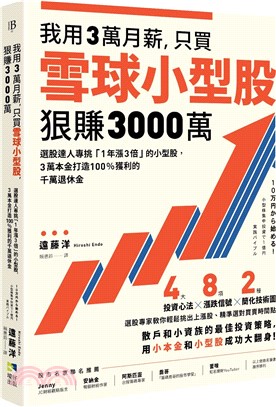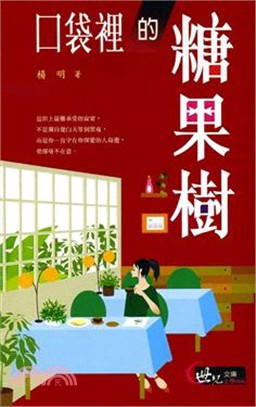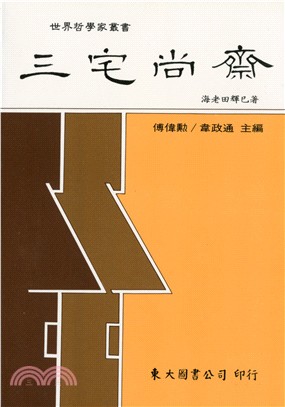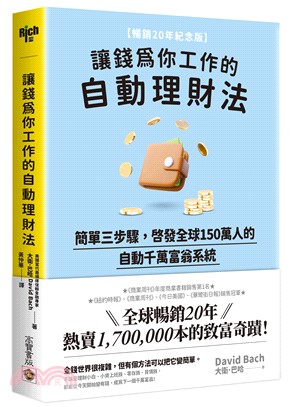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以詩之名》為席慕蓉的第七本詩集,收錄了其最新的詩歌創作。詩集中收錄的大部分作品寫成于2005年之後。詩人也在其中特意放進了精心挑選的一些舊作,有些是從來沒有發表過的,有些是雖然發表了卻從沒有收入到詩集里的,因此這就成為一本以詩之名將時光層疊交錯的集子。詩人近年多次往返于臺灣與蒙古草原之間,作為那個遠離族群遠離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蒙古人,詩人借此次詩集的出版重溫了自己的精神回鄉之旅,并終于在心中、在詩里找到屬于自己的故鄉。關于原鄉經驗的書寫,終于靠著一次又一次的行走,將故鄉草原上的月光引入詩行。
詩集《以詩之名》離第一冊詩集《七里香》的面世正好隔了三十年。漫漫歲月的雕琢與淬煉,使一顆詩心更加溫潤、澄澈。從亞洲到歐洲,從四川到蒙古,歲月的河流洗去綿長的喜悅與哀愁,也卷進了無盡的懷想與堅貞。
從創作第一首詩的一九五九年三月算起,到此次新詩集的出版,總數不過四百首的詩歌連接了詩人生命里超過五十年的時光。用詩人借用朋友的話說,“回頭省視自己一路走來,可能忽然發現,原來走了這麼久,現在才正要開始。”這本詩集記錄了詩人幾十年的故鄉尋覓之路。如今,詩人站在故鄉的月光里,回望來時路,再翹首未來。舊的情懷依然發酵,新的體悟繼續涌現,是愛詩之人不可錯過的珠玉之作。
詩集《以詩之名》離第一冊詩集《七里香》的面世正好隔了三十年。漫漫歲月的雕琢與淬煉,使一顆詩心更加溫潤、澄澈。從亞洲到歐洲,從四川到蒙古,歲月的河流洗去綿長的喜悅與哀愁,也卷進了無盡的懷想與堅貞。
從創作第一首詩的一九五九年三月算起,到此次新詩集的出版,總數不過四百首的詩歌連接了詩人生命里超過五十年的時光。用詩人借用朋友的話說,“回頭省視自己一路走來,可能忽然發現,原來走了這麼久,現在才正要開始。”這本詩集記錄了詩人幾十年的故鄉尋覓之路。如今,詩人站在故鄉的月光里,回望來時路,再翹首未來。舊的情懷依然發酵,新的體悟繼續涌現,是愛詩之人不可錯過的珠玉之作。
作者簡介
席慕蓉,祖籍蒙古,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于臺灣。于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及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等。擔任臺灣新竹師范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余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
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余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
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名人/編輯推薦
《以詩之名》是席慕蓉最新詩集,臺灣大陸同步上市,漫漫歲月的雕琢與淬煉,新的體悟繽紛涌現……
席慕蓉第一部詩集《七里香》,距今正好三十年。漫漫歲月的雕琢與淬煉,使一顆詩心更加溫潤、澄澈。從亞洲到歐洲,從四川到蒙古,歲月的河流洗去綿長的喜悅與哀愁,也卷進了無盡的懷想與堅貞。
《以詩之名》為席慕蓉最新詩集,也是其第七本詩集,收錄了2006年以來未收錄、甚至未發表過的作品。舊的情懷依然發酵,新的體悟繼續涌現,是愛詩之人不可錯過的珠玉之作。
《以詩之名》延續了席慕蓉一貫的豐厚的簡單。人生感悟依然在其筆端緩緩流淌,伴隨著每一次晨鐘暮鼓。“一生或許只是幾頁/不斷在修改與謄抄著的詩稿/從青絲改到白發有人/還在燈下”。經歷過太多的云卷云舒,人生于她,早已不是一種誘惑,而是一出寧靜的風景,其中,沉淀了太多的人生智慧,和回憶,和遙想。
席慕蓉第一部詩集《七里香》,距今正好三十年。漫漫歲月的雕琢與淬煉,使一顆詩心更加溫潤、澄澈。從亞洲到歐洲,從四川到蒙古,歲月的河流洗去綿長的喜悅與哀愁,也卷進了無盡的懷想與堅貞。
《以詩之名》為席慕蓉最新詩集,也是其第七本詩集,收錄了2006年以來未收錄、甚至未發表過的作品。舊的情懷依然發酵,新的體悟繼續涌現,是愛詩之人不可錯過的珠玉之作。
《以詩之名》延續了席慕蓉一貫的豐厚的簡單。人生感悟依然在其筆端緩緩流淌,伴隨著每一次晨鐘暮鼓。“一生或許只是幾頁/不斷在修改與謄抄著的詩稿/從青絲改到白發有人/還在燈下”。經歷過太多的云卷云舒,人生于她,早已不是一種誘惑,而是一出寧靜的風景,其中,沉淀了太多的人生智慧,和回憶,和遙想。
序
回望
——自序
幾年前,馬來西亞的水彩畫家謝文釧先生,托人給我寄來一張小畫,是我自己的舊時習作,應該是大學畢業之前交到系里的一張水墨畫。文釧是我的同班同學,畢業後的那個夏天,去系辦公室辭行的時候,見到這些已經無人認領的作業,在助教的建議之下,他就當作紀念品帶回馬來西亞去了。多年之後,才又輾轉寄還給我。
這張小畫是臨稿的習作,畫得不很用心,乏善可陳。倒是畫面左上角我用拙劣的書法所提的那些字句,喚醒了我的記憶:關山夢,夢斷故園寒。塞外英豪何處去,天涯鴻雁幾時還,拭淚話陰山。
生硬的字句,早已忘卻的過去,可是我知道這是我填的詞。應該是大學四年級上學期,在溥心畬老師的課堂里開始學習,胡亂試著填的吧?後來在別的課堂里交作業的時候,又把它寫了上去。
這真正應該是早已被我遺忘了的“少作”了。但是,多年之後,重新交到我的手上,怎么越看越像是一封預留的書信?
原來,為了那不曾謀面的原鄉,我其實是一直在作著準備的。
年輕的我還寫過一些,依稀記得的還有:
“……頭白人前效爭媚,烏鞘忘了,犀甲忘了,上馬先呼累。”等等幼稚又怪異的句子,交到溥老師桌上的時候,他看著吟著就微微笑了起來,是多么溫暖的笑容,佇立在桌前的我,整個人也放松了,就安靜地等待著老師的批改和解說……
是多么遙遠的記憶。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會開始寫詩?又為什么還在繼續寫詩?我或許可以用生活中的轉折來回答,譬如戰亂,譬如寂寞,并且也曾經多次這樣回答過了。可是,心里卻總是有些不安,覺得這些答案都并不完全,甚至也不一定正確。
什么才是那個正確而又完全的答案?
或者,我應該說,對于“寫詩”這件事,有沒有一個正確而又完全的答案?
我是一直在追問著的。
是不是因為這不斷的追問與自省,詩,也就不知不覺地繼續寫下去了?
《以詩之名》是我的第七本詩集。
預定在今年的七月出版,那時,離第一冊詩集《七里香》的面世,其間正好隔了三十年。而如果從放進第二冊詩集中最早的那一首是寫成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來作計算的話,這總數不過四百首左右的詩,就連接了我生命里超過五十年的時光了。
五十年之間的我,是不斷在改變呢還是始終沒有改變?
記得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第四本詩集《邊緣光影》出版,在極為簡短的序言里,我曾經斬釘截鐵地宣稱:“詩,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自己。”
我現在也不會反對這句話。可是,我也慢慢發現,在這一生里,我們其實很難以現有之身的種種經驗,來為“詩中的那個自己”發言。
是的,詩,當然是自己,可是為什么有時候卻好像另有所本?
一個另有所本的自己?
在這本新的詩集里,大部分的作品都寫成于二○○五年之後,但是,我也特意放進了一些舊作。有的是從沒發表過的,有些是雖然發表了卻從沒收進到自己詩集里來的,因此,這本新詩集就成為一本以詩之名來將時光層疊交錯在一起的書冊了。
時光層疊交錯,卻讓我無限驚詫地發現,詩,在此刻,怎么就像是什么人給我預留的一封又一封的書信?
時光層疊交錯,當年無人能夠預知卻早已寫在詩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現——故土變貌,恩愛成灰,原鄉與我素面相見……
我并不想在此一一舉例,但是,重新回望之時,真是震懾于詩中那些“逼真精確”的預言。是何人?早在一切發生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前,就已經為我這現有之身寫出了歷歷如繪的此刻的生命場景了。(是那個另有所本的自己嗎?)
原來,五十年的時光,在詩中,真有可能是層疊交錯的。
原來,窮五十年的時光,也不過就只是讓我明白了“我的不能明白”。
原來,關于寫詩這件事,我所知的是多么表面!多么微小!
可是,盡管如此,在今天這篇文字的最後,我還是忍不住想為我這現有之身與“詩”的關聯多說幾句話,譬如那詩中的原鄉。
向溥老師交出的作業“天涯鴻雁幾時還,拭淚話陰山”,應該是一九六二年秋天之後的填詞習作。一九七九年,我寫了一首《狂風沙》,這首詩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一個從沒見過的地方竟是故鄉
所有的知識只有一個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親啊母親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這首詩寫成之後的十年,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臺灣解除了公教人員不得前往中國大陸的禁令,我在八月下旬就又搭飛機,又坐火車,又轉乘吉普車地終于站在我父親的草原上了。盤桓了幾天之後,再轉往母親的河源故里。然後,然後就此展開了我往後這二十多年在蒙古高原上的探尋和行走,一如有些朋友所說的“瘋狂”或者“詭異”的原鄉之旅。
朋友的評語其實并無惡意,他們只是覺得在這一代的還鄉經驗里,我實在“太超過了現實”而已。
我的朋友,我們這一代人,生在亂世,生在年輕父母流離生涯中的某一個驛站,真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完全來不及為自己準備一個故鄉。
我們終于在臺灣尋到一處家鄉,得以定居,得以成長,甚至得以為早逝的母親(或者父親)構筑了一處墓地。所以,在幾十年之後,這突然獲得的所謂“回鄉”,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回的都只是父母的故鄉而已。不管是陪著父母,或者只能自己一個人回去,也都只是去認一認地方,修一修祖墳,了了一樁心愿,也就很可以了。朋友說,沒見過像我這樣一去再去,回個沒完沒了的。
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為的是什么,所以,只好保持沉默。一直到今年,二○一一年的春天,我寫出了《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與去年完成的《英雄噶爾丹》一起,放進這本《以詩之名》的詩集里,成為書中的第九輯,篇名定為《英雄組曲》,在那種完成了什么的興奮與快樂里,我好像才終于得到了解答。
我發現,這三首詩放在一起之後,我最大的快樂,并不在于是不是寫了一首可以重現歷史現場的詩,更不是他人所說的什么使命感的完成,不是,完全不是。我發現,我最大的快樂是一種可以稱之為“竊喜”的滿足和愉悅。
只因為,在這三首詩里,在詩中的某些細節上,我可以放進了自己的親身體驗。
我終于可以與詩中的那個自己攜手合作,寫出了屬于我們的可以觸摸可以感受的故鄉。
靠著一次又一次的行走,我終于可以把草原上那明亮的月光引入詩行。我還知道斡難河水在夏夜里依舊冰涼,我知道河岸邊上雜樹林的茂密以及林下水流溫潤的光影,我知道黎明前草尖上的露水忽然會變成一大片模糊的灰白,我知道破曉前東方天穹之上那逼人的彤紅,我甚至也知道了一面歷經滄桑的旌旗,或者一尊供奉了八百年的神聖蘇力德,在族人心中的分量,有多么沉重……
這些以我這現有之身所獲得的關于原鄉的經驗,雖然依舊是有限的表面和微小,可是,無論如何,在此刻,那個名字再也不會是只能躲在我的心中,卻又時時讓我疼痛的那一根刺了。
靠著不斷的行走與書寫,當然,還有上天的厚賜,我終于得以在心中,在詩里找到了屬于我自己的故鄉。這對于許多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存在,因而是毫不費力的擁有。可是,對于我這個遠離族群遠離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蒙古人,卻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故鄉啊!
原來,我要的就是這個。
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尋找,我現在終于明白,我要的就是這個。
而且,我還希望能夠再多要一些。
我多么希望,能像好友蔣勛寫給我的那幾句話一樣:
“書寫者回頭省視自己一路走來,可能忽然發現,原來走了那么久,現在才正要開始。”
我多么希望是如此!
我多么希望能如此。
二○一一年四月廿五日于淡水鄉居
附錄三家之言
席慕蓉詩有感
三木直大
我之所以有這份榮幸為席慕蓉女士的新詩集獻上賀辭,緣于邀請席慕蓉女士和焦桐先生參加二○一○年十月在東京召開的臺灣現代詩研究會。我一直在構思建立一個臺灣詩人和日本詩人一同談詩并彼此朗讀詩,且讓研究者一同議論的平臺。主要的成員,包括席慕蓉女士翻譯詩集《契丹的玫瑰》的譯者池上貞子教授,和?弦的翻譯詩集《深淵》的譯者松浦恒雄教授,以及即將出版的陳育虹詩集譯者佐藤普美子教授,還有我。邀請席慕蓉女士和焦桐先生蒞臨時的籌辦者,是兩位詩集的譯者池上貞子教授。我在大會提供的資料集里,對席慕蓉女士的詩寫了短評。在此引用部分文句。
在席慕蓉女士的詩里,從初期開始,“我”“你”“我們”的構造便屢次登場。有時候“你”比起“你們”的呼喚更有廣度。作為被呼喚對象的“你”,在不同的作品中展現的相異的蘊含和樣貌,我們或可說席慕蓉女士的寫詩歷程是“尋找”“發現”“確認”“凝視”“你”的旅程。與此同時,也是尋找“我”的旅行。透過寫詩,席慕蓉女士發現了“你”,發現了“我”。當然,這樣的追問,在開始寫詩之前便存在席慕蓉女士心中,雖說是發現,卻有多層次的意思,從中“到底認同為何物”的問題于焉發生。因而,現在這個“你”邀請“我”到蒙古,席慕蓉女士的寫詩歷程正顯示了這個過程。
老實說,以前的我并不是席慕蓉詩的熱情讀者。真正大量閱讀,是從攬讀池上貞子教授的翻譯詩集開始。當時的感想,便是前述的思索。因而這回,我一邊注意人稱用法,一邊再次展讀了席慕蓉女士的詩集。從而,我意外地發現,本以為是戀愛詩的作品,重新展現了多樣意涵的廣度與深度。而且,經過歲月的積累,其呼喚更演奏出多重意義的樂章。并且,從他的呼喚中,終于她的祖籍內蒙古的身影開始忽隱忽現。
在東京舉辦的研討會上,聚集了眾多的旅日蒙古人。他們多出身于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我驚訝的是,日本有如此多的蒙古人。而且他們全都是席慕蓉詩的狂熱讀者。研討會翌日,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系舉行的活動也是如此。我十分能理解,離開故鄉的蒙古人之所以愛讀席慕蓉女士詩的理由。席慕蓉詩與蒙古的關系,池上貞子教授在日語詩集《譯者後記》中有詳盡的論述,我不在此贅言。我衷心期盼池上貞子教授的《譯者後記》早日被中譯。
然而,離鄉背井的人們之所以愛讀她的詩,不僅僅出于思鄉之情,其中更有著不能單純歸因于技術純熟的深刻情感。這份深刻的情感,成為席慕蓉詩的不絕的泉源,這也是她的詩吸引臺灣眾多讀者背後的原因。
我認為她的詩風靡一九八○年代的臺灣,正好與迎接解嚴的臺灣,在時代的變化中,人們開始欲求嶄新表現的時期重疊。雖然以臺灣的族群來說,她是外省詩人,不過她體內流的是蒙古血統。從而她尋求的不是“想象的中華”,而是“想象的蒙古”。況且,其背後更背負著蒙古慘烈的近現代史。而這等慘烈的近現代史與臺灣的處境相互疊合。讀者不正是為這重層性所吸引的嗎?我想,這種結構便是不僅吸引臺灣讀者,并且每當詩集在各國和各地區被翻譯時都能引人入勝之處。
席慕蓉詩的這種構造,也同樣呈現在此次詩集《以詩之名》之中。即便其中收錄的作品創作年代不一,在各處都還是能聆聽到她想演奏的樂音。再者,吾人也能察覺詩人為了追尋樂音音色的豐潤,做了創作的嘗試。如此,透過詩集的形式,一部交響樂于焉響起。
這部交響樂,根據生存本身與圍繞著我們的世界多義性而譜成。其中揉合了殘酷和純粹的愛等各式要素。重新思考到席慕蓉詩這種結構之後,我認為,不僅應該在臺灣現代詩史和中文現代詩史之中,更有必要在世界文學的維度中賦予席慕蓉詩相當的地位才是。
附注:作者三木直大為廣島大學教授,本文由謝蕙貞女士翻譯。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論席慕蓉之以詩談詩
李瑞騰
席慕蓉在一篇題為《追尋之歌》的散文中說過:
有些詩人,可以把自己的創作經驗和作品分析,寫成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
有些詩人,則是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
而我呢?我當然絕對做不成前者,但是,也更做不成後者。(《寧靜的巨大》,頁36)
我初步的體會是,她真的做不成後者,作為一位現時代的詩人,尤其是成名詩人,要做到“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詩評家會逼你說,媒體記者會要你說,你的讀者會希望你說;但是她并非“做不成前者”,而是不想;她其實是經常分析自己的創作經驗,有時也會分析自己的作品,只是方式并非論述,不是“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而是用她自己擅長的文類——詩和散文,認認真真地談著自己詩之經驗。
用散文談詩,不管說得多么輕快,就是在講理——一種從創作實踐中得到的詩之理。我們相信,經驗的系統化即可成理論,因此詩人也可能成為詩論家。而用詩談詩,在漢語詩史上早有先例,唐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開啟了論詩絕句的傳統,司空圖《詩品》是論詩之風格的詩話,許多詩人在相互贈答的詩作中無可避免地觸及寫詩之事。
席慕蓉以散文談詩,《寫生者》中有《詩教》《詩人啊!詩人!》,《黃羊·玫瑰·飛魚》中有《論席慕蓉》《詩與詩人》,《寧靜的巨大》中有《追尋之歌》《詩人與寫詩的人》等;至于以詩談詩,例子不少,可以合組成“慕蓉詩話”,以下我將擇要討論,借此了解席慕蓉對詩的看法。
詩的本質、詩的價值,以及恐怖的說法
詩到底是什么?性質與功能如何?這些都是大哉問,詩論家真可以寫一本又一本的書去討論。席慕蓉在她上一本詩集《我折疊著我的愛》中有一首《詩的本質》(頁44),寫一位女性詩人讀自己詩集的校樣(從印刷的字體上重新再閱讀一次自己的詩),“她真切地感覺到了生命正在一頁頁地展現,再一頁頁地隱沒,如海浪一次又一次地漫過沙岸。”她因此而感到“這是何等的幸運”!
從“生命”,她進一步想到“歲月”之“如此豐美而又憂傷,平靜而又暗潮洶涌”,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拿起筆來,誠實地注記下生命內里的觸動,好讓日後的自己可以從容回顧,這是何等的幸運”。接著,她又想到“時光”,想到詩之寫作“越寫越慢”,想到紀伯倫說的“愛是自足于愛的”,想到“詩是自足于詩的”;而這就是“詩的本質”。
在時光的移動中,如何生活?如何展現生命?這是人的根本問題;而聞見之間有所觸動,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意理應相應,關鍵在于是否“誠實地注記”。因為有這樣的一些注記,再閱讀時,生命才會逐次展現并隱沒。
這詩寫在二○○二年,前此二十余年,她在《詩的價值》(《無怨的青春》,頁6)一詩中把寫詩比擬成金匠之“日夜捶擊敲打”,“只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蟬翼的金飾”,就詩之表現來說,即是“把憂傷的來源轉化成/光澤細柔的詞句”。和前一首詩對照,“憂傷”只是生活中的一種“觸動”,其他的情感類型亦然。詩價值之所在正如是。
後此七八年,席慕蓉用一首《恐怖的說法》(《以詩之名》,頁90)將“自足”作了演繹:
詩是何等奇怪的個體
出生之後就會站起來走開
薄薄的一頁瘦瘦的幾行
不需衣衫不畏凍餓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有一種恐怖的說法:
詩繼續活著無關詩人是否存在
還有一種更恐怖的說法,是——要到了詩人終于離席之後
詩才開始真正完整的
顯露出來
前段指詩脫離創作母體之後,成了“何等奇怪的個體”,不只是有自己的生命,而且一出生即會站會走會跑,其形雖薄弱,卻不需衣衫,不畏凍餓。“野外”是一個寬闊的天地,可任詩馳騁。二段扣題,兩種說法,一種比一種“恐怖”:詩之存活,與詩人無關;要等到詩人身後,詩之形構、意義等才能真正顯露出來。我們都記得,上世紀前葉在英美流行一時的新批評,一九六○、七○年代影響臺灣很大,他們無視于文學活動空間的前後兩端(作者、讀者)之存在,認為文本獨立自足,雖也曾造成一些解讀上的問題,但重視文本的完整、嚴密、藝術性等,于作家之寫作、讀者之賞讀,也有相當程度之助益。對于席慕蓉來說,雖以“恐怖”形容,但應也有寫好作品才最重要的體悟。
詩的成因、詩成、執筆的欲望、一首詩的進行
在席慕蓉的詩里,我們頻頻聽到她的叩問:我為什么要寫詩?我為什么還在寫詩?一九八三年,她有一首《詩的成因》(《時光九篇》,頁3),前二段寫她整個上午都在調整步伐好進入行列,卻沒人注意到她的加入;整個下午都在尋找自我而走出人群,但也沒人發現她的背離。每天“為了爭得那些終必要丟棄的”,卻得付出整整一日,甚且整整一生。必須等到日落以後才開始:
不斷地回想
回想在所有溪流旁的
淡淡的陽光
淡淡的花香
她顯然體悟到,在現實之爭中付出的代價太大,自然界卻有許多被忽略的美好景物。在去取之間的調適,這就是她的詩之成因。
二○○○年,她另有一首《詩成》(《迷途詩冊》,頁4),前二段分列物色之變的“無從回答”“無法辨識”,然後,有什么在“慢慢浮現”?有什么在“逐漸隱沒”?取舍由誰在決定?那真正的渴望是什么?等等,喻指詩心之萌發。詩之所以成,有其緣由,有其過程,正對應著不知能完成些什么的一生:“如熾熱的火炭投身于寒夜之湖/這絕無勝算的爭奪與對峙啊。”這就是為什么“窗外時光正橫掃一切萬物寂滅”,而“窗內的我為什么還要寫詩?”。
二○○九年,她有二首叩問與回答都更深刻的作品:《執筆的欲望——敬致詩人池上貞子》(《以詩之名》,頁14)、《一首詩的進行——寄呈齊老師》(同上,頁16)。
池上貞子以日文翻譯了席慕蓉的詩,席慕蓉用詩告訴她自己為什么要寫詩,為什么到現在都還沒停筆:
這執筆的欲望從何生成?
其實不容易回答
我只知道
絕非來自眼前肉身
有沒有可能
是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
無邪又熱烈的靈魂
冀望借文字而留存
她雖然用的是問句,但應是有感卻不十分確定。我們都知道,持續性寫作是極不容易的,特別是寫詩,有人說三十歲以後如果還在寫詩,很可能就會寫一輩子,那是因為有不得不寫的理由,而且一定是內生的,所謂“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無邪又熱烈的靈魂/冀望借文字而留存”,聽來略顯抽象,但這大約也就和意內而言外的說法相近,那存于心的意念,總要向外表現,才能留存。席慕蓉在自我交代,觸及了詩之寫作的原理。
《一首詩的進行》為寄呈齊邦媛老師之作,可以說是席慕蓉的詩之創作論,相當復雜,可能得另文分析。詩人一開始說“一首詩的進行/在可測與不可測之間”,結筆處說:
是否只因為
愛與記憶曾經無限珍惜
才讓我們至今猶得以得以
執筆?
這“愛與記憶”可說是這一系列叩問的總回應。
詩的曠野、詩的囹圄、詩的蹉跎、詩的末路
在漫長歲月的寫詩生涯中,席慕蓉總期待一個寬闊的馳騁空間,那就是《詩的曠野》(《以詩之名》,頁54):
在詩的曠野里
不求依附不去投靠
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
其實也并非一無所有
有游蕩的云有玩耍的風
有潺潺而過的溪流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
自由和圓滿
真實的曠野空間廣袤,有云游蕩,有風嬉耍,有溪流潺潺而過,自在自如;詩的天地亦如是,然已抽象化,在其中,詩人可以不依附任何幫派勢力,不投靠任何達官顯貴,這不去不求,特有一種獨立自足的生命形態,在這樣的空間,詩人“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這野馬之獨行的譬喻,說明“詩的曠野”之可貴;進一步我們看到具象的曠野和心靈的曠野的融合,也看到二者與詩的關系重組:詩即“來自曠野的呼喚/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自由和圓滿”。
用另外一種說辭,也就是《詩的囹圄》(《迷途詩冊》,頁54)前段所描述的遼闊的天地,不論是巨如鷹雕,或細如一只小灰蝶,都可以“盡量舒展雙翼”。詩人不解的是:
這天地何其遼闊
我愛為什么總有人不能明白
他們苦守的王國其實就是
我們從來也不想進入的囹圄
這“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曠野”與“囹圄”的對比,只能說人各有志吧,所以還是回到自我的省思上,在這里我想談席慕蓉所謂詩的“蹉跎”與“末路”。
“蹉跎”本是“失足”,後引申為“失時”、“失志”。寫詩一事與“時”與“志”關系密切,蓋“志”為詩的內容,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大序》);“詩”與“時”皆從“寺”得聲,聲韻學上有凡從某聲皆有某義的說法,我一直以為時間根本就是詩的靈魂。因之,《詩的蹉跎》(《邊緣光影》,頁4)即從時間寫起,說“消失了的是時間/累積起來的也是/時間”,這等于是說“時”其實是可以失而不失;然而“志”呢?詩接著的二、三段如下:
在薄暮的岸邊誰來喟嘆
這一艘又一艘
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的舟船
一如我們那些暗自熄滅了的欲望
那些從來不敢去試穿的新衣和夢想
即使夏日豐美透明即使在那時
海洋曾經那樣飽滿與平靜
我們的語言曾經那樣年輕
薄暮蒼茫中,有那么一艘又一艘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的舟船。對一個寫詩的人來說,觸這個景會生出什么樣的情?是舟船,就該下水,就該航行在萬頃碧波之中,但是它們卻“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形同廢棄,更嚴重地說,那就死亡了。詩人說“誰來喟嘆”?這是“詩的蹉跎”。進一步用了“那些”“那些”“那時”景況,全都是。結筆處的“我們的語言曾經那樣/年輕”,言下之意應是說,如不再蹉跎,可以用更成熟、更厚重的詩語去面對那些“欲望”“夢想”以及豐美透明的夏日、飽滿與平靜的海洋。
這頗有寫詩要及時、要持續、要挖深的意味,但即便如此,席慕蓉感受過不斷重復而來的悲傷與寂默,了解“生命里能讓人/強烈懷想的快樂實在太少”,她曾有過更深層的思索,在《詩的末路》(《邊緣光影》,頁22)中,她寫道:
我因此而逐漸膽怯
對每一個字句都猶疑難決
當要刪除的終于
超過了要吐露的那一部分之時
我就不再寫詩
“字句都猶疑難決”并非單純的遣詞造句問題,“膽怯”是心理問題,是生命的困境引發了寫詩的瓶頸,這很嚴重,根本已是詩人角色認同危機,“當……之時”“我就不再寫詩”是一種假設,但也是一種宣告,對于詩人來說,當然是“詩的末路”了;而那是一種什么情況呢?“要刪除的”“超過了要吐露的”,就詩之表現來說,是詩心與詩筆的沖突,其苦痛不言可喻。
母語、以詩之名
席慕蓉在她的詩中談詩之處當然不只上述,連“譯詩”一事她都有詩《譯詩》,(《我折疊著我的愛》,頁13)。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逐冊逐頁搜尋點讀,我就不再多引述了。最後想談她的一首《母語》。
本詩送給一位蒙古國詩人巴?拉哈巴蘇榮,大意是“你”為什么“可以一生都用母語來寫詩”,而我卻不能。
從母親懷中接受的
是生命最珍貴的本質
而我又是何人啊
竟然竟然任由它
隨風而逝……
不能用母語寫詩的遺憾,我們可以理解,但在事實上,席慕蓉并非在主觀上愿意“任由它/隨風而逝”。在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一位出生四川、臺灣成長的蒙古孩子,注定已喪失了學習母語的環境,多年以後,她以成長過程中習得的漢字,不斷地書寫蒙古草原之美及其困境,父親的蒙古已漸轉成她的了,無法使用母語寫詩的遺憾,也算有所補償了。
二○○八年,她寫下《以詩之名》:以詩之名,“搜尋記憶”、“呼求繁星”、“重履斯地”、“重塑記憶”,其“實”即“原是千萬株白樺的故居”,有“何等悠久又豐厚的腐植層”的“這林間”,以及“過去了的過去”。我們能肯定地說,那正是蒙古的土地。
“以詩之名”成了席慕蓉最新一本詩集的書名,她自己、她的詩、她的蒙古,三者已然合體了。
附注:作者李瑞騰為臺灣文學館館長,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地平線
林文義
“竟能那般沉穩,一條直線橫過就是大地蒼茫了……”已然過世的故人,多年以前如此說。
那是風雪凜冽的北美東岸,離鄉半生的小說家在初見後,向我問及:是否認識席慕蓉?我提及席氏之詩,小說家談的是席氏之畫:你知道長年被家鄉拒絕的小說家父親乃是高齡的膠彩畫名家,日本領臺時代,列之“臺展三少年”之一,以之家學淵源,想見對繪畫藝術自有心得。小說家表明雖長居紐約,卻不喜涉足美術館細賞真跡,寧可靜閱畫冊,再三反復尋索。
“一條直線橫過……”小說家停頓半晌,略為思忖地接續:“她的地平線就有色彩了。”回憶所及,似乎用心、莊重地詢我關于席氏的文學著作及在臺灣讀者的評價云云。身置小說家服務的聯合國二十三樓,他專屬研究室窗下正是東河,指著河中一塊突兀的巖石,中間竟有一株結冰若水晶的獨立樹:小說家形容冬冷之前,樹上有窩斑鳩家族:“雪融後的春末,它們會按時回來,好像約定。”他溫暖地笑了,而後邀我近窗俯望,若有深意地自語:“你看那植物,多像席慕蓉畫里,地平線的孤樹。”
幽幽地,半睡半醒的我,竟會仿佛依稀地夢見十多年前,與小說家初見時的談話,卻是從席慕蓉的繪畫說起。
——自序
幾年前,馬來西亞的水彩畫家謝文釧先生,托人給我寄來一張小畫,是我自己的舊時習作,應該是大學畢業之前交到系里的一張水墨畫。文釧是我的同班同學,畢業後的那個夏天,去系辦公室辭行的時候,見到這些已經無人認領的作業,在助教的建議之下,他就當作紀念品帶回馬來西亞去了。多年之後,才又輾轉寄還給我。
這張小畫是臨稿的習作,畫得不很用心,乏善可陳。倒是畫面左上角我用拙劣的書法所提的那些字句,喚醒了我的記憶:關山夢,夢斷故園寒。塞外英豪何處去,天涯鴻雁幾時還,拭淚話陰山。
生硬的字句,早已忘卻的過去,可是我知道這是我填的詞。應該是大學四年級上學期,在溥心畬老師的課堂里開始學習,胡亂試著填的吧?後來在別的課堂里交作業的時候,又把它寫了上去。
這真正應該是早已被我遺忘了的“少作”了。但是,多年之後,重新交到我的手上,怎么越看越像是一封預留的書信?
原來,為了那不曾謀面的原鄉,我其實是一直在作著準備的。
年輕的我還寫過一些,依稀記得的還有:
“……頭白人前效爭媚,烏鞘忘了,犀甲忘了,上馬先呼累。”等等幼稚又怪異的句子,交到溥老師桌上的時候,他看著吟著就微微笑了起來,是多么溫暖的笑容,佇立在桌前的我,整個人也放松了,就安靜地等待著老師的批改和解說……
是多么遙遠的記憶。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會開始寫詩?又為什么還在繼續寫詩?我或許可以用生活中的轉折來回答,譬如戰亂,譬如寂寞,并且也曾經多次這樣回答過了。可是,心里卻總是有些不安,覺得這些答案都并不完全,甚至也不一定正確。
什么才是那個正確而又完全的答案?
或者,我應該說,對于“寫詩”這件事,有沒有一個正確而又完全的答案?
我是一直在追問著的。
是不是因為這不斷的追問與自省,詩,也就不知不覺地繼續寫下去了?
《以詩之名》是我的第七本詩集。
預定在今年的七月出版,那時,離第一冊詩集《七里香》的面世,其間正好隔了三十年。而如果從放進第二冊詩集中最早的那一首是寫成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來作計算的話,這總數不過四百首左右的詩,就連接了我生命里超過五十年的時光了。
五十年之間的我,是不斷在改變呢還是始終沒有改變?
記得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第四本詩集《邊緣光影》出版,在極為簡短的序言里,我曾經斬釘截鐵地宣稱:“詩,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自己。”
我現在也不會反對這句話。可是,我也慢慢發現,在這一生里,我們其實很難以現有之身的種種經驗,來為“詩中的那個自己”發言。
是的,詩,當然是自己,可是為什么有時候卻好像另有所本?
一個另有所本的自己?
在這本新的詩集里,大部分的作品都寫成于二○○五年之後,但是,我也特意放進了一些舊作。有的是從沒發表過的,有些是雖然發表了卻從沒收進到自己詩集里來的,因此,這本新詩集就成為一本以詩之名來將時光層疊交錯在一起的書冊了。
時光層疊交錯,卻讓我無限驚詫地發現,詩,在此刻,怎么就像是什么人給我預留的一封又一封的書信?
時光層疊交錯,當年無人能夠預知卻早已寫在詩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現——故土變貌,恩愛成灰,原鄉與我素面相見……
我并不想在此一一舉例,但是,重新回望之時,真是震懾于詩中那些“逼真精確”的預言。是何人?早在一切發生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前,就已經為我這現有之身寫出了歷歷如繪的此刻的生命場景了。(是那個另有所本的自己嗎?)
原來,五十年的時光,在詩中,真有可能是層疊交錯的。
原來,窮五十年的時光,也不過就只是讓我明白了“我的不能明白”。
原來,關于寫詩這件事,我所知的是多么表面!多么微小!
可是,盡管如此,在今天這篇文字的最後,我還是忍不住想為我這現有之身與“詩”的關聯多說幾句話,譬如那詩中的原鄉。
向溥老師交出的作業“天涯鴻雁幾時還,拭淚話陰山”,應該是一九六二年秋天之後的填詞習作。一九七九年,我寫了一首《狂風沙》,這首詩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一個從沒見過的地方竟是故鄉
所有的知識只有一個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親啊母親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這首詩寫成之後的十年,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臺灣解除了公教人員不得前往中國大陸的禁令,我在八月下旬就又搭飛機,又坐火車,又轉乘吉普車地終于站在我父親的草原上了。盤桓了幾天之後,再轉往母親的河源故里。然後,然後就此展開了我往後這二十多年在蒙古高原上的探尋和行走,一如有些朋友所說的“瘋狂”或者“詭異”的原鄉之旅。
朋友的評語其實并無惡意,他們只是覺得在這一代的還鄉經驗里,我實在“太超過了現實”而已。
我的朋友,我們這一代人,生在亂世,生在年輕父母流離生涯中的某一個驛站,真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完全來不及為自己準備一個故鄉。
我們終于在臺灣尋到一處家鄉,得以定居,得以成長,甚至得以為早逝的母親(或者父親)構筑了一處墓地。所以,在幾十年之後,這突然獲得的所謂“回鄉”,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回的都只是父母的故鄉而已。不管是陪著父母,或者只能自己一個人回去,也都只是去認一認地方,修一修祖墳,了了一樁心愿,也就很可以了。朋友說,沒見過像我這樣一去再去,回個沒完沒了的。
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為的是什么,所以,只好保持沉默。一直到今年,二○一一年的春天,我寫出了《英雄哲別》《鎖兒罕失剌》,與去年完成的《英雄噶爾丹》一起,放進這本《以詩之名》的詩集里,成為書中的第九輯,篇名定為《英雄組曲》,在那種完成了什么的興奮與快樂里,我好像才終于得到了解答。
我發現,這三首詩放在一起之後,我最大的快樂,并不在于是不是寫了一首可以重現歷史現場的詩,更不是他人所說的什么使命感的完成,不是,完全不是。我發現,我最大的快樂是一種可以稱之為“竊喜”的滿足和愉悅。
只因為,在這三首詩里,在詩中的某些細節上,我可以放進了自己的親身體驗。
我終于可以與詩中的那個自己攜手合作,寫出了屬于我們的可以觸摸可以感受的故鄉。
靠著一次又一次的行走,我終于可以把草原上那明亮的月光引入詩行。我還知道斡難河水在夏夜里依舊冰涼,我知道河岸邊上雜樹林的茂密以及林下水流溫潤的光影,我知道黎明前草尖上的露水忽然會變成一大片模糊的灰白,我知道破曉前東方天穹之上那逼人的彤紅,我甚至也知道了一面歷經滄桑的旌旗,或者一尊供奉了八百年的神聖蘇力德,在族人心中的分量,有多么沉重……
這些以我這現有之身所獲得的關于原鄉的經驗,雖然依舊是有限的表面和微小,可是,無論如何,在此刻,那個名字再也不會是只能躲在我的心中,卻又時時讓我疼痛的那一根刺了。
靠著不斷的行走與書寫,當然,還有上天的厚賜,我終于得以在心中,在詩里找到了屬于我自己的故鄉。這對于許多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存在,因而是毫不費力的擁有。可是,對于我這個遠離族群遠離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蒙古人,卻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故鄉啊!
原來,我要的就是這個。
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尋找,我現在終于明白,我要的就是這個。
而且,我還希望能夠再多要一些。
我多么希望,能像好友蔣勛寫給我的那幾句話一樣:
“書寫者回頭省視自己一路走來,可能忽然發現,原來走了那么久,現在才正要開始。”
我多么希望是如此!
我多么希望能如此。
二○一一年四月廿五日于淡水鄉居
附錄三家之言
席慕蓉詩有感
三木直大
我之所以有這份榮幸為席慕蓉女士的新詩集獻上賀辭,緣于邀請席慕蓉女士和焦桐先生參加二○一○年十月在東京召開的臺灣現代詩研究會。我一直在構思建立一個臺灣詩人和日本詩人一同談詩并彼此朗讀詩,且讓研究者一同議論的平臺。主要的成員,包括席慕蓉女士翻譯詩集《契丹的玫瑰》的譯者池上貞子教授,和?弦的翻譯詩集《深淵》的譯者松浦恒雄教授,以及即將出版的陳育虹詩集譯者佐藤普美子教授,還有我。邀請席慕蓉女士和焦桐先生蒞臨時的籌辦者,是兩位詩集的譯者池上貞子教授。我在大會提供的資料集里,對席慕蓉女士的詩寫了短評。在此引用部分文句。
在席慕蓉女士的詩里,從初期開始,“我”“你”“我們”的構造便屢次登場。有時候“你”比起“你們”的呼喚更有廣度。作為被呼喚對象的“你”,在不同的作品中展現的相異的蘊含和樣貌,我們或可說席慕蓉女士的寫詩歷程是“尋找”“發現”“確認”“凝視”“你”的旅程。與此同時,也是尋找“我”的旅行。透過寫詩,席慕蓉女士發現了“你”,發現了“我”。當然,這樣的追問,在開始寫詩之前便存在席慕蓉女士心中,雖說是發現,卻有多層次的意思,從中“到底認同為何物”的問題于焉發生。因而,現在這個“你”邀請“我”到蒙古,席慕蓉女士的寫詩歷程正顯示了這個過程。
老實說,以前的我并不是席慕蓉詩的熱情讀者。真正大量閱讀,是從攬讀池上貞子教授的翻譯詩集開始。當時的感想,便是前述的思索。因而這回,我一邊注意人稱用法,一邊再次展讀了席慕蓉女士的詩集。從而,我意外地發現,本以為是戀愛詩的作品,重新展現了多樣意涵的廣度與深度。而且,經過歲月的積累,其呼喚更演奏出多重意義的樂章。并且,從他的呼喚中,終于她的祖籍內蒙古的身影開始忽隱忽現。
在東京舉辦的研討會上,聚集了眾多的旅日蒙古人。他們多出身于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我驚訝的是,日本有如此多的蒙古人。而且他們全都是席慕蓉詩的狂熱讀者。研討會翌日,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系舉行的活動也是如此。我十分能理解,離開故鄉的蒙古人之所以愛讀席慕蓉女士詩的理由。席慕蓉詩與蒙古的關系,池上貞子教授在日語詩集《譯者後記》中有詳盡的論述,我不在此贅言。我衷心期盼池上貞子教授的《譯者後記》早日被中譯。
然而,離鄉背井的人們之所以愛讀她的詩,不僅僅出于思鄉之情,其中更有著不能單純歸因于技術純熟的深刻情感。這份深刻的情感,成為席慕蓉詩的不絕的泉源,這也是她的詩吸引臺灣眾多讀者背後的原因。
我認為她的詩風靡一九八○年代的臺灣,正好與迎接解嚴的臺灣,在時代的變化中,人們開始欲求嶄新表現的時期重疊。雖然以臺灣的族群來說,她是外省詩人,不過她體內流的是蒙古血統。從而她尋求的不是“想象的中華”,而是“想象的蒙古”。況且,其背後更背負著蒙古慘烈的近現代史。而這等慘烈的近現代史與臺灣的處境相互疊合。讀者不正是為這重層性所吸引的嗎?我想,這種結構便是不僅吸引臺灣讀者,并且每當詩集在各國和各地區被翻譯時都能引人入勝之處。
席慕蓉詩的這種構造,也同樣呈現在此次詩集《以詩之名》之中。即便其中收錄的作品創作年代不一,在各處都還是能聆聽到她想演奏的樂音。再者,吾人也能察覺詩人為了追尋樂音音色的豐潤,做了創作的嘗試。如此,透過詩集的形式,一部交響樂于焉響起。
這部交響樂,根據生存本身與圍繞著我們的世界多義性而譜成。其中揉合了殘酷和純粹的愛等各式要素。重新思考到席慕蓉詩這種結構之後,我認為,不僅應該在臺灣現代詩史和中文現代詩史之中,更有必要在世界文學的維度中賦予席慕蓉詩相當的地位才是。
附注:作者三木直大為廣島大學教授,本文由謝蕙貞女士翻譯。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論席慕蓉之以詩談詩
李瑞騰
席慕蓉在一篇題為《追尋之歌》的散文中說過:
有些詩人,可以把自己的創作經驗和作品分析,寫成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
有些詩人,則是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
而我呢?我當然絕對做不成前者,但是,也更做不成後者。(《寧靜的巨大》,頁36)
我初步的體會是,她真的做不成後者,作為一位現時代的詩人,尤其是成名詩人,要做到“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詩評家會逼你說,媒體記者會要你說,你的讀者會希望你說;但是她并非“做不成前者”,而是不想;她其實是經常分析自己的創作經驗,有時也會分析自己的作品,只是方式并非論述,不是“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而是用她自己擅長的文類——詩和散文,認認真真地談著自己詩之經驗。
用散文談詩,不管說得多么輕快,就是在講理——一種從創作實踐中得到的詩之理。我們相信,經驗的系統化即可成理論,因此詩人也可能成為詩論家。而用詩談詩,在漢語詩史上早有先例,唐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開啟了論詩絕句的傳統,司空圖《詩品》是論詩之風格的詩話,許多詩人在相互贈答的詩作中無可避免地觸及寫詩之事。
席慕蓉以散文談詩,《寫生者》中有《詩教》《詩人啊!詩人!》,《黃羊·玫瑰·飛魚》中有《論席慕蓉》《詩與詩人》,《寧靜的巨大》中有《追尋之歌》《詩人與寫詩的人》等;至于以詩談詩,例子不少,可以合組成“慕蓉詩話”,以下我將擇要討論,借此了解席慕蓉對詩的看法。
詩的本質、詩的價值,以及恐怖的說法
詩到底是什么?性質與功能如何?這些都是大哉問,詩論家真可以寫一本又一本的書去討論。席慕蓉在她上一本詩集《我折疊著我的愛》中有一首《詩的本質》(頁44),寫一位女性詩人讀自己詩集的校樣(從印刷的字體上重新再閱讀一次自己的詩),“她真切地感覺到了生命正在一頁頁地展現,再一頁頁地隱沒,如海浪一次又一次地漫過沙岸。”她因此而感到“這是何等的幸運”!
從“生命”,她進一步想到“歲月”之“如此豐美而又憂傷,平靜而又暗潮洶涌”,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拿起筆來,誠實地注記下生命內里的觸動,好讓日後的自己可以從容回顧,這是何等的幸運”。接著,她又想到“時光”,想到詩之寫作“越寫越慢”,想到紀伯倫說的“愛是自足于愛的”,想到“詩是自足于詩的”;而這就是“詩的本質”。
在時光的移動中,如何生活?如何展現生命?這是人的根本問題;而聞見之間有所觸動,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意理應相應,關鍵在于是否“誠實地注記”。因為有這樣的一些注記,再閱讀時,生命才會逐次展現并隱沒。
這詩寫在二○○二年,前此二十余年,她在《詩的價值》(《無怨的青春》,頁6)一詩中把寫詩比擬成金匠之“日夜捶擊敲打”,“只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蟬翼的金飾”,就詩之表現來說,即是“把憂傷的來源轉化成/光澤細柔的詞句”。和前一首詩對照,“憂傷”只是生活中的一種“觸動”,其他的情感類型亦然。詩價值之所在正如是。
後此七八年,席慕蓉用一首《恐怖的說法》(《以詩之名》,頁90)將“自足”作了演繹:
詩是何等奇怪的個體
出生之後就會站起來走開
薄薄的一頁瘦瘦的幾行
不需衣衫不畏凍餓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有一種恐怖的說法:
詩繼續活著無關詩人是否存在
還有一種更恐怖的說法,是——要到了詩人終于離席之後
詩才開始真正完整的
顯露出來
前段指詩脫離創作母體之後,成了“何等奇怪的個體”,不只是有自己的生命,而且一出生即會站會走會跑,其形雖薄弱,卻不需衣衫,不畏凍餓。“野外”是一個寬闊的天地,可任詩馳騁。二段扣題,兩種說法,一種比一種“恐怖”:詩之存活,與詩人無關;要等到詩人身後,詩之形構、意義等才能真正顯露出來。我們都記得,上世紀前葉在英美流行一時的新批評,一九六○、七○年代影響臺灣很大,他們無視于文學活動空間的前後兩端(作者、讀者)之存在,認為文本獨立自足,雖也曾造成一些解讀上的問題,但重視文本的完整、嚴密、藝術性等,于作家之寫作、讀者之賞讀,也有相當程度之助益。對于席慕蓉來說,雖以“恐怖”形容,但應也有寫好作品才最重要的體悟。
詩的成因、詩成、執筆的欲望、一首詩的進行
在席慕蓉的詩里,我們頻頻聽到她的叩問:我為什么要寫詩?我為什么還在寫詩?一九八三年,她有一首《詩的成因》(《時光九篇》,頁3),前二段寫她整個上午都在調整步伐好進入行列,卻沒人注意到她的加入;整個下午都在尋找自我而走出人群,但也沒人發現她的背離。每天“為了爭得那些終必要丟棄的”,卻得付出整整一日,甚且整整一生。必須等到日落以後才開始:
不斷地回想
回想在所有溪流旁的
淡淡的陽光
淡淡的花香
她顯然體悟到,在現實之爭中付出的代價太大,自然界卻有許多被忽略的美好景物。在去取之間的調適,這就是她的詩之成因。
二○○○年,她另有一首《詩成》(《迷途詩冊》,頁4),前二段分列物色之變的“無從回答”“無法辨識”,然後,有什么在“慢慢浮現”?有什么在“逐漸隱沒”?取舍由誰在決定?那真正的渴望是什么?等等,喻指詩心之萌發。詩之所以成,有其緣由,有其過程,正對應著不知能完成些什么的一生:“如熾熱的火炭投身于寒夜之湖/這絕無勝算的爭奪與對峙啊。”這就是為什么“窗外時光正橫掃一切萬物寂滅”,而“窗內的我為什么還要寫詩?”。
二○○九年,她有二首叩問與回答都更深刻的作品:《執筆的欲望——敬致詩人池上貞子》(《以詩之名》,頁14)、《一首詩的進行——寄呈齊老師》(同上,頁16)。
池上貞子以日文翻譯了席慕蓉的詩,席慕蓉用詩告訴她自己為什么要寫詩,為什么到現在都還沒停筆:
這執筆的欲望從何生成?
其實不容易回答
我只知道
絕非來自眼前肉身
有沒有可能
是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
無邪又熱烈的靈魂
冀望借文字而留存
她雖然用的是問句,但應是有感卻不十分確定。我們都知道,持續性寫作是極不容易的,特別是寫詩,有人說三十歲以後如果還在寫詩,很可能就會寫一輩子,那是因為有不得不寫的理由,而且一定是內生的,所謂“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無邪又熱烈的靈魂/冀望借文字而留存”,聽來略顯抽象,但這大約也就和意內而言外的說法相近,那存于心的意念,總要向外表現,才能留存。席慕蓉在自我交代,觸及了詩之寫作的原理。
《一首詩的進行》為寄呈齊邦媛老師之作,可以說是席慕蓉的詩之創作論,相當復雜,可能得另文分析。詩人一開始說“一首詩的進行/在可測與不可測之間”,結筆處說:
是否只因為
愛與記憶曾經無限珍惜
才讓我們至今猶得以得以
執筆?
這“愛與記憶”可說是這一系列叩問的總回應。
詩的曠野、詩的囹圄、詩的蹉跎、詩的末路
在漫長歲月的寫詩生涯中,席慕蓉總期待一個寬闊的馳騁空間,那就是《詩的曠野》(《以詩之名》,頁54):
在詩的曠野里
不求依附不去投靠
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
其實也并非一無所有
有游蕩的云有玩耍的風
有潺潺而過的溪流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
自由和圓滿
真實的曠野空間廣袤,有云游蕩,有風嬉耍,有溪流潺潺而過,自在自如;詩的天地亦如是,然已抽象化,在其中,詩人可以不依附任何幫派勢力,不投靠任何達官顯貴,這不去不求,特有一種獨立自足的生命形態,在這樣的空間,詩人“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這野馬之獨行的譬喻,說明“詩的曠野”之可貴;進一步我們看到具象的曠野和心靈的曠野的融合,也看到二者與詩的關系重組:詩即“來自曠野的呼喚/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自由和圓滿”。
用另外一種說辭,也就是《詩的囹圄》(《迷途詩冊》,頁54)前段所描述的遼闊的天地,不論是巨如鷹雕,或細如一只小灰蝶,都可以“盡量舒展雙翼”。詩人不解的是:
這天地何其遼闊
我愛為什么總有人不能明白
他們苦守的王國其實就是
我們從來也不想進入的囹圄
這“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曠野”與“囹圄”的對比,只能說人各有志吧,所以還是回到自我的省思上,在這里我想談席慕蓉所謂詩的“蹉跎”與“末路”。
“蹉跎”本是“失足”,後引申為“失時”、“失志”。寫詩一事與“時”與“志”關系密切,蓋“志”為詩的內容,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大序》);“詩”與“時”皆從“寺”得聲,聲韻學上有凡從某聲皆有某義的說法,我一直以為時間根本就是詩的靈魂。因之,《詩的蹉跎》(《邊緣光影》,頁4)即從時間寫起,說“消失了的是時間/累積起來的也是/時間”,這等于是說“時”其實是可以失而不失;然而“志”呢?詩接著的二、三段如下:
在薄暮的岸邊誰來喟嘆
這一艘又一艘
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的舟船
一如我們那些暗自熄滅了的欲望
那些從來不敢去試穿的新衣和夢想
即使夏日豐美透明即使在那時
海洋曾經那樣飽滿與平靜
我們的語言曾經那樣年輕
薄暮蒼茫中,有那么一艘又一艘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的舟船。對一個寫詩的人來說,觸這個景會生出什么樣的情?是舟船,就該下水,就該航行在萬頃碧波之中,但是它們卻“從來不曾解纜出發過”,形同廢棄,更嚴重地說,那就死亡了。詩人說“誰來喟嘆”?這是“詩的蹉跎”。進一步用了“那些”“那些”“那時”景況,全都是。結筆處的“我們的語言曾經那樣/年輕”,言下之意應是說,如不再蹉跎,可以用更成熟、更厚重的詩語去面對那些“欲望”“夢想”以及豐美透明的夏日、飽滿與平靜的海洋。
這頗有寫詩要及時、要持續、要挖深的意味,但即便如此,席慕蓉感受過不斷重復而來的悲傷與寂默,了解“生命里能讓人/強烈懷想的快樂實在太少”,她曾有過更深層的思索,在《詩的末路》(《邊緣光影》,頁22)中,她寫道:
我因此而逐漸膽怯
對每一個字句都猶疑難決
當要刪除的終于
超過了要吐露的那一部分之時
我就不再寫詩
“字句都猶疑難決”并非單純的遣詞造句問題,“膽怯”是心理問題,是生命的困境引發了寫詩的瓶頸,這很嚴重,根本已是詩人角色認同危機,“當……之時”“我就不再寫詩”是一種假設,但也是一種宣告,對于詩人來說,當然是“詩的末路”了;而那是一種什么情況呢?“要刪除的”“超過了要吐露的”,就詩之表現來說,是詩心與詩筆的沖突,其苦痛不言可喻。
母語、以詩之名
席慕蓉在她的詩中談詩之處當然不只上述,連“譯詩”一事她都有詩《譯詩》,(《我折疊著我的愛》,頁13)。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逐冊逐頁搜尋點讀,我就不再多引述了。最後想談她的一首《母語》。
本詩送給一位蒙古國詩人巴?拉哈巴蘇榮,大意是“你”為什么“可以一生都用母語來寫詩”,而我卻不能。
從母親懷中接受的
是生命最珍貴的本質
而我又是何人啊
竟然竟然任由它
隨風而逝……
不能用母語寫詩的遺憾,我們可以理解,但在事實上,席慕蓉并非在主觀上愿意“任由它/隨風而逝”。在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一位出生四川、臺灣成長的蒙古孩子,注定已喪失了學習母語的環境,多年以後,她以成長過程中習得的漢字,不斷地書寫蒙古草原之美及其困境,父親的蒙古已漸轉成她的了,無法使用母語寫詩的遺憾,也算有所補償了。
二○○八年,她寫下《以詩之名》:以詩之名,“搜尋記憶”、“呼求繁星”、“重履斯地”、“重塑記憶”,其“實”即“原是千萬株白樺的故居”,有“何等悠久又豐厚的腐植層”的“這林間”,以及“過去了的過去”。我們能肯定地說,那正是蒙古的土地。
“以詩之名”成了席慕蓉最新一本詩集的書名,她自己、她的詩、她的蒙古,三者已然合體了。
附注:作者李瑞騰為臺灣文學館館長,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地平線
林文義
“竟能那般沉穩,一條直線橫過就是大地蒼茫了……”已然過世的故人,多年以前如此說。
那是風雪凜冽的北美東岸,離鄉半生的小說家在初見後,向我問及:是否認識席慕蓉?我提及席氏之詩,小說家談的是席氏之畫:你知道長年被家鄉拒絕的小說家父親乃是高齡的膠彩畫名家,日本領臺時代,列之“臺展三少年”之一,以之家學淵源,想見對繪畫藝術自有心得。小說家表明雖長居紐約,卻不喜涉足美術館細賞真跡,寧可靜閱畫冊,再三反復尋索。
“一條直線橫過……”小說家停頓半晌,略為思忖地接續:“她的地平線就有色彩了。”回憶所及,似乎用心、莊重地詢我關于席氏的文學著作及在臺灣讀者的評價云云。身置小說家服務的聯合國二十三樓,他專屬研究室窗下正是東河,指著河中一塊突兀的巖石,中間竟有一株結冰若水晶的獨立樹:小說家形容冬冷之前,樹上有窩斑鳩家族:“雪融後的春末,它們會按時回來,好像約定。”他溫暖地笑了,而後邀我近窗俯望,若有深意地自語:“你看那植物,多像席慕蓉畫里,地平線的孤樹。”
幽幽地,半睡半醒的我,竟會仿佛依稀地夢見十多年前,與小說家初見時的談話,卻是從席慕蓉的繪畫說起。
目次
自序
篇一 執筆的欲望
時光長卷
執筆的欲望
一首詩的進行
明鏡
寒夜書案
秘教的花朵
春天的演出
篇二 最後的折疊
白堊紀
琥珀的由來
晨起
寂靜的時刻
別後——之一
夢中的畫面
紀念冊
最後的折疊
小篆
別後——之二
篇三 旦暮之間
詮釋者
翩翩的時光
旦暮之間
櫻之約
關于“美”以及“美學”
詩的曠野
篇四 雕刀
雕刀
恨晚
別後
等待
偶遇
淡化
篇五 霧里
桐花
眠月站
獨白
孤獨的行路者
霧里
篇六 浪子的告白
我的愿望
昨日
晚慧的詩人
恐怖的說法
呼喚五則
揭曉
陌生的戀人
浪子的告白
篇七 以詩之名
胡馬之歌
以詩之名
母語
素描巴爾虎草原
封號
黑駿馬
塔克拉瑪干
當時間走過
篇八 聆聽《伊金桑》
聆聽《伊金桑》
祖先的姓氏
夢中篝火
“退牧還草”?
因你而留下的歌
熱血青春
送別查嘎黎
他們的聲音
篇九 英雄組曲
英雄噶爾丹
英雄哲別
鎖兒罕失剌
附錄 三家之言
席慕蓉詩有感三木直大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李瑞騰
——論席慕蓉之以詩談詩
地平線林文義
篇一 執筆的欲望
時光長卷
執筆的欲望
一首詩的進行
明鏡
寒夜書案
秘教的花朵
春天的演出
篇二 最後的折疊
白堊紀
琥珀的由來
晨起
寂靜的時刻
別後——之一
夢中的畫面
紀念冊
最後的折疊
小篆
別後——之二
篇三 旦暮之間
詮釋者
翩翩的時光
旦暮之間
櫻之約
關于“美”以及“美學”
詩的曠野
篇四 雕刀
雕刀
恨晚
別後
等待
偶遇
淡化
篇五 霧里
桐花
眠月站
獨白
孤獨的行路者
霧里
篇六 浪子的告白
我的愿望
昨日
晚慧的詩人
恐怖的說法
呼喚五則
揭曉
陌生的戀人
浪子的告白
篇七 以詩之名
胡馬之歌
以詩之名
母語
素描巴爾虎草原
封號
黑駿馬
塔克拉瑪干
當時間走過
篇八 聆聽《伊金桑》
聆聽《伊金桑》
祖先的姓氏
夢中篝火
“退牧還草”?
因你而留下的歌
熱血青春
送別查嘎黎
他們的聲音
篇九 英雄組曲
英雄噶爾丹
英雄哲別
鎖兒罕失剌
附錄 三家之言
席慕蓉詩有感三木直大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李瑞騰
——論席慕蓉之以詩談詩
地平線林文義
書摘/試閱
執筆的欲望
——敬致詩人池上貞子
一生或許只是幾頁
不斷在修改與謄抄著的詩稿
從青絲改到白發有人
還在燈下
這執筆的欲望從何生成?
其實不容易回答
我只知道
絕非來自眼前的肉身
有沒有可能
是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
無邪又熱烈的靈魂
冀望借文字而留存?
是隱藏也是釋放
為那一路行來
頻頻撿拾入懷的記憶芳香
是癡狂并且神傷
為那許多曾經擦肩而過之後
就再也不會重逢的光影圖像
是隱約的呼喚
是永遠伴隨著追悔的背叛
是絕美的誘惑同時不也是那
絕對無力改變的承諾?
如暗夜里的飛蛾不得不趨向燭火
就此急急奔赴向前
頭也不回的我們的一生啊
請問
還能有些什么不一樣的解說?
今夜窗里窗外
宇宙依然在不停地消蝕崩壞
這執筆的欲望究竟
從何而來?
為什么有人
有人在燈下
還遲遲不肯離開?
2009.1.7
時光長卷
誰說綿延不絕?
誰又說不舍晝夜?
其實我們的一生只是個
空間有限的展示柜
時光是畫在絹上的河流
這一生的青綠山水
無論再怎么精心繪制
再怎么廢寢忘食
也只能漸次鋪開再漸次收起
凡不再展示的
就緊緊卷入畫軸
成為昨日
2010.7.4
浪子的告白
何等奢華又荒涼的一生啊!
散盡的豈止是萬貫家財
當最後
我們只能在記憶中不斷確認
彼此的曾經相愛
2009.3.9
秘教的花朵
詩的秘密在于出走或者隱藏
集中所有的意念于筆尖然後
背道而馳
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地
也并非為了去取悅于你
那魅惑
如薰香蜜蠟雕琢出的秘教的花朵
來自靈魂所選擇的信仰
似近又遠仿佛是自身那幽微的心房
時而又仿佛是那難以觸及的
渺茫的穹蒼
2010.11.13
晨起
——給H.P
仿佛有青鳥引路
有花香伴著我們登岸
豐饒的叢林
就在前面延展著綠色的濃蔭
生命美如
一個剛剛開始的夢境
而我是那個衷心感激的女子
醒來之後發現
你依然在我身旁
靜靜的衾枕間
一如夢中靜靜的湖面
漂浮著青草的芳香
窗外曙光微涼
1986.11.5
琥珀的由來
在黑暗中我開始
重新回想
那些蕪雜的光影
那些片刻的歡娛曾經
如何映照過
松脂靜靜溢出的淚滴
沉埋之後光澤與芳香依舊
這不肯消失的印記我愛
就是琥珀的由來
2003.7.3
詩的曠野
——給年輕的詩人
文字并非全部
生活也不是我們其實
不需要逼迫自己
去證明這一生的意義和價值
在詩的曠野里
不求依附不去投靠
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
其實也并非一無所有
有游蕩的云有玩耍的風
有潺潺而過的溪流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
自由和圓滿
2006.5.16
我的愿望
不希望我愛的詩人
最後成為一間面目模糊的
小雜貨鋪
也不希望他成為一本
眾人推崇的百科全書
我只希望
他能依照著生命的要求去成長
開自己的花結自己的果
在陽光下
或者長成松長成柏
或者長成為一株
在高高的巖岸上正隨風搖曳的
瘦削的野百合
2005.4.5
雕刀
——給立霧溪
縱然你已去遠
想此刻又已隔了幾重山
我依然停頓在水流的中央
努力回溯那剛剛過去的時光
想你從千里之遙奔赴到我的身邊
原也只為了這一刻的低回和繾綣
從云到霧到雨露最後匯成流泉
也不過只是為了想讓這世界知道
反復與堅持之後
柔水終成雕刀
1988
以詩之名
以詩之名我們搜尋記憶
縱使一切都已是過去了的過去
在溪流的兩岸目光迂回之處
畢竟有人曾經深深地愛過
稍早如拓跋鮮卑更遠如戎狄
這里原是千萬株白樺的故居
有巫有覡在暗夜里一一點燃的篝火前
擊鼓高歌齊聲頌唱
以詩之名呼求繁星
其旁有杜鵑盛開如粉紫色的汪洋
秋霜若降落葉松滿山層疊金黃
而眼前的濕潤與枯干其實
同屬時光細細打磨之後的質感
所謂永恒原來就在腳下
是這林間何等悠久又豐厚的腐植層
仿佛我們的一生總是在等待
何時何人(他會不會踏月而來?)
以詩之名重履斯地
以沙沙作響的跫音逐步深入
好將洞穴里沉睡著的昨日
(那所有的百般不舍的昨日啊!)
輕
輕
喚
醒
是的一切都已是過去了的過去
(為什么還讓我如此癡迷?)
以詩之名我們重塑記憶
在溪流的兩岸我與你相遇之處
畢竟有人曾經深深地愛過
或許是你
或許只是我自己而已
2008.3.31
晚慧的詩人
如果
想要把一天
或者七日都全部荒廢
可以去
試著寫一首詩
不過如果
想要讓一生都不會後悔
今夜她才敢說
除了寫詩恐怕
也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2010.10.31
恐怖的說法
詩是何等奇怪的個體
出生之後就會站起來走開
薄薄的一頁瘦瘦的幾行
不需衣衫不畏凍餓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甚至只要有幾句
寫到誰的心里面去了就可以
從商周到隋唐
一直活到所謂的當代)
有一種恐怖的說法:
詩繼續活著無關詩人是否存在
還有一種更恐怖的說法是——
要到了詩人終于離席之後
詩
才開始真正完整地
顯露出來
2009.12.17
——敬致詩人池上貞子
一生或許只是幾頁
不斷在修改與謄抄著的詩稿
從青絲改到白發有人
還在燈下
這執筆的欲望從何生成?
其實不容易回答
我只知道
絕非來自眼前的肉身
有沒有可能
是盤踞在內難以窺視的某一個
無邪又熱烈的靈魂
冀望借文字而留存?
是隱藏也是釋放
為那一路行來
頻頻撿拾入懷的記憶芳香
是癡狂并且神傷
為那許多曾經擦肩而過之後
就再也不會重逢的光影圖像
是隱約的呼喚
是永遠伴隨著追悔的背叛
是絕美的誘惑同時不也是那
絕對無力改變的承諾?
如暗夜里的飛蛾不得不趨向燭火
就此急急奔赴向前
頭也不回的我們的一生啊
請問
還能有些什么不一樣的解說?
今夜窗里窗外
宇宙依然在不停地消蝕崩壞
這執筆的欲望究竟
從何而來?
為什么有人
有人在燈下
還遲遲不肯離開?
2009.1.7
時光長卷
誰說綿延不絕?
誰又說不舍晝夜?
其實我們的一生只是個
空間有限的展示柜
時光是畫在絹上的河流
這一生的青綠山水
無論再怎么精心繪制
再怎么廢寢忘食
也只能漸次鋪開再漸次收起
凡不再展示的
就緊緊卷入畫軸
成為昨日
2010.7.4
浪子的告白
何等奢華又荒涼的一生啊!
散盡的豈止是萬貫家財
當最後
我們只能在記憶中不斷確認
彼此的曾經相愛
2009.3.9
秘教的花朵
詩的秘密在于出走或者隱藏
集中所有的意念于筆尖然後
背道而馳
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地
也并非為了去取悅于你
那魅惑
如薰香蜜蠟雕琢出的秘教的花朵
來自靈魂所選擇的信仰
似近又遠仿佛是自身那幽微的心房
時而又仿佛是那難以觸及的
渺茫的穹蒼
2010.11.13
晨起
——給H.P
仿佛有青鳥引路
有花香伴著我們登岸
豐饒的叢林
就在前面延展著綠色的濃蔭
生命美如
一個剛剛開始的夢境
而我是那個衷心感激的女子
醒來之後發現
你依然在我身旁
靜靜的衾枕間
一如夢中靜靜的湖面
漂浮著青草的芳香
窗外曙光微涼
1986.11.5
琥珀的由來
在黑暗中我開始
重新回想
那些蕪雜的光影
那些片刻的歡娛曾經
如何映照過
松脂靜靜溢出的淚滴
沉埋之後光澤與芳香依舊
這不肯消失的印記我愛
就是琥珀的由來
2003.7.3
詩的曠野
——給年輕的詩人
文字并非全部
生活也不是我們其實
不需要逼迫自己
去證明這一生的意義和價值
在詩的曠野里
不求依附不去投靠
如一匹離群的野馬獨自行走
其實也并非一無所有
有游蕩的云有玩耍的風
有潺潺而過的溪流
詩就是來自曠野的呼喚
是生命擺脫了一切束縛之後的
自由和圓滿
2006.5.16
我的愿望
不希望我愛的詩人
最後成為一間面目模糊的
小雜貨鋪
也不希望他成為一本
眾人推崇的百科全書
我只希望
他能依照著生命的要求去成長
開自己的花結自己的果
在陽光下
或者長成松長成柏
或者長成為一株
在高高的巖岸上正隨風搖曳的
瘦削的野百合
2005.4.5
雕刀
——給立霧溪
縱然你已去遠
想此刻又已隔了幾重山
我依然停頓在水流的中央
努力回溯那剛剛過去的時光
想你從千里之遙奔赴到我的身邊
原也只為了這一刻的低回和繾綣
從云到霧到雨露最後匯成流泉
也不過只是為了想讓這世界知道
反復與堅持之後
柔水終成雕刀
1988
以詩之名
以詩之名我們搜尋記憶
縱使一切都已是過去了的過去
在溪流的兩岸目光迂回之處
畢竟有人曾經深深地愛過
稍早如拓跋鮮卑更遠如戎狄
這里原是千萬株白樺的故居
有巫有覡在暗夜里一一點燃的篝火前
擊鼓高歌齊聲頌唱
以詩之名呼求繁星
其旁有杜鵑盛開如粉紫色的汪洋
秋霜若降落葉松滿山層疊金黃
而眼前的濕潤與枯干其實
同屬時光細細打磨之後的質感
所謂永恒原來就在腳下
是這林間何等悠久又豐厚的腐植層
仿佛我們的一生總是在等待
何時何人(他會不會踏月而來?)
以詩之名重履斯地
以沙沙作響的跫音逐步深入
好將洞穴里沉睡著的昨日
(那所有的百般不舍的昨日啊!)
輕
輕
喚
醒
是的一切都已是過去了的過去
(為什么還讓我如此癡迷?)
以詩之名我們重塑記憶
在溪流的兩岸我與你相遇之處
畢竟有人曾經深深地愛過
或許是你
或許只是我自己而已
2008.3.31
晚慧的詩人
如果
想要把一天
或者七日都全部荒廢
可以去
試著寫一首詩
不過如果
想要讓一生都不會後悔
今夜她才敢說
除了寫詩恐怕
也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2010.10.31
恐怖的說法
詩是何等奇怪的個體
出生之後就會站起來走開
薄薄的一頁瘦瘦的幾行
不需衣衫不畏凍餓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甚至只要有幾句
寫到誰的心里面去了就可以
從商周到隋唐
一直活到所謂的當代)
有一種恐怖的說法:
詩繼續活著無關詩人是否存在
還有一種更恐怖的說法是——
要到了詩人終于離席之後
詩
才開始真正完整地
顯露出來
2009.12.17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