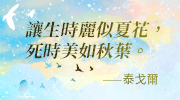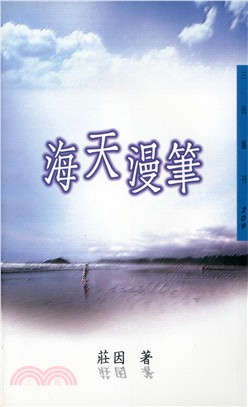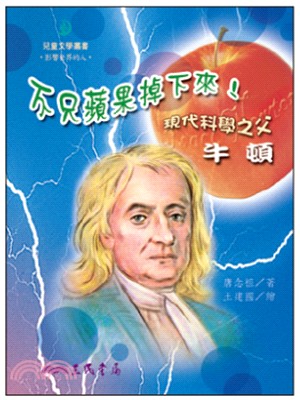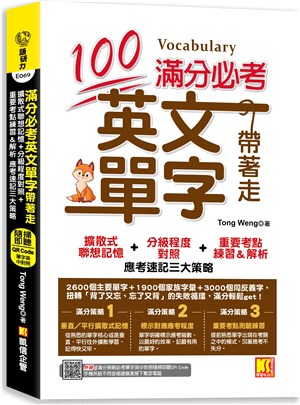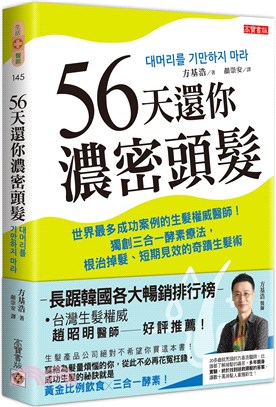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馬相伯卷(簡體書)
商品資訊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馬相伯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章太炎列舉清末“西學”人物,曾以“嚴(復)、馬(相伯)、辜(鴻銘)、伍(廷芳)”并稱,梁啟超、蔡元培等人率眾弟子求教于他,可見時人之推崇。馬相伯著述大多散失,方豪輯錄為《馬相伯先生文集》(1948),復旦大學出版社《馬相伯集》(1996)續有搜羅,今本《馬相伯卷》又收集了多篇軼文,力圖呈現馬相伯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卷中關于改良、變法、政體、國體、民族、政教關系和宗教信仰之地位的論述,尤其值得關注。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馬相伯(1840—1939),江蘇丹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1851年遷居上海,畢業于徐匯公學,加入耶穌會,為神父。1876年脫離教會,任李鴻章幕僚,參與洋務活動,后回歸天主教,創辦震旦學院(1903)、復旦公學(1905)。辛亥革命后,擔任總統府高級政治顧問,兼任北京大學校長,籌建輔仁大學。馬相伯學貫中西,精于歐洲語言、宗教、哲學和歷史,思想通達、公允、理性,為學界尊奉。晚年參與抗戰宣傳,隨遷大后方,在越南諒山去世。
編者簡介
天綱,1957年生于上海,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專業,獲博士學位。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2003年起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宗教學系主任、利徐學社主任。著有《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1998)、《人文上海》(2004)、《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2007)、《增訂徐光啟年譜》(2011)等,與業師朱維錚先生一起主編《徐光啟全集》(2011),編輯《馬相伯集》(1996)。
馬相伯(1840—1939),江蘇丹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1851年遷居上海,畢業于徐匯公學,加入耶穌會,為神父。1876年脫離教會,任李鴻章幕僚,參與洋務活動,后回歸天主教,創辦震旦學院(1903)、復旦公學(1905)。辛亥革命后,擔任總統府高級政治顧問,兼任北京大學校長,籌建輔仁大學。馬相伯學貫中西,精于歐洲語言、宗教、哲學和歷史,思想通達、公允、理性,為學界尊奉。晚年參與抗戰宣傳,隨遷大后方,在越南諒山去世。
編者簡介
天綱,1957年生于上海,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專業,獲博士學位。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2003年起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宗教學系主任、利徐學社主任。著有《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1998)、《人文上海》(2004)、《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2007)、《增訂徐光啟年譜》(2011)等,與業師朱維錚先生一起主編《徐光啟全集》(2011),編輯《馬相伯集》(1996)。
目次
導言
上朝鮮國王條陳(約1882)
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約1882)
改革招商局建議(1885)
致汪康年(1896)
務農會條議(1897)
論葉君《條議書》(1897)
槍不殺人(1897)
炮臺新制(1897)
利瑪竇遺像題詞(1897)
徐光啟遺像題詞(1897)
湯若望遺像題詞(1897)
南懷仁遺像題詞(1897)
致汪康年(1897)
致汪康年(1898) 導言
上朝鮮國王條陳(約1882)
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約1882)
改革招商局建議(1885)
致汪康年(1896)
務農會條議(1897)
論葉君《條議書》(1897)
槍不殺人(1897)
炮臺新制(1897)
利瑪竇遺像題詞(1897)
徐光啟遺像題詞(1897)
湯若望遺像題詞(1897)
南懷仁遺像題詞(1897)
致汪康年(1897)
致汪康年(1898)
捐獻家產興學子據(1900)
致朱志堯(1900)
開鐵路以圖自強論(1901)
興學筆錄(1902)
震旦學院章程(1902)
致英華(1902)
《拉丁文通》敘言(1903)
致汪康年(1903)
明故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
前十字記(1903)
前震旦學院全體干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1905)
復旦公學章程(1905)
復旦公學廣告(1905)
中國圖書有限公司招股緣起啟(1906)
《也是集》序(1907)
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1908)
《墨井集》序(1908)
《古文拾級》序(1909)
《求新廠出品圖》敘(1911)
復旦學院廣告(1911)
勸勿為盜布告(1912)
復旦公學招生廣告(1912)
辛亥政見(南華錄)(1912)
致孫中山(1912)
上總統書(1912)
致熊希齡(1912)
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1912)
致董恂士(1913)
致英華(1913)
致英貞淑(1913)
覆丁義華(1913)
《〈新史合編直講〉音譯名稱合璧》引言(1913)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種(1913)
北京法國文術研究會開幕詞(1914)
代擬宋氏山莊碑記(1914)
一國元首應兼主祭主事否(1914)
宗教在良心(1914)
宗教之關系(1914)
信教自由(1914)
一九一五年(1914)
答客問一九一五年(1914)
致英貞淑(1914)
重刊《主制群征》序(1915)
重刊《辯學遺牘》跋(1915)
致英貞淑(1915)
致張漁珊(1915)
題贈楊佑廷(1916)
青年會開會演說詞(1916)
《圣經》與人群之關系(1916)
書《利先生行跡》后(1916)
《萬松野人言善錄》序(1916)
《憲法草案》大、二毛子問答錄(1916)
書《〈天壇草案〉第十九條問答錄》后(1916)
書《請定儒教為國教》后(1916)
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1916)
代擬《反對孔道請愿書》五篇(1916)
憲法向界(1916)
《約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
信教自由(1916)
書《分合表》后(1916)
國民大會說(1916)
農業改良友助社簡章(1916)
呈設農業改良社(1916)
致英華(1916)
致英貞淑(1916)
跋文澂明《懷歸詩》(1917)
《元代也里可溫考》序(1917)
致段祺瑞(約1917)
重刊《真主靈性理證》序(1918)
重刊《靈魂道體說》序(1918)
《言善錄》再版序(1918)
民國民照心鏡(1918)
《民治學會簽名簿》題詞(1918)
致英貞淑(1918)
致英華、英貞淑(1918)
致英華(約1918)
無題(1919)
《明李之藻傳》序(1919)
重刊《靈言蠡勺》序(1919)
答問中國教務(1919)
錄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巡閱使光主教致天津
華鐸書并按(1919)
題《愧林漫錄》(1919)
現今財政以組織收支細則為要務說(1919)
致英貞淑(1919)
致英華(1919)
致陳垣(1919)
致張漁珊(1919)
致張仲仁(1919)
致陳垣(約1919)
代擬《北京教友上教宗書》(1920)
《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跋(1920)
跋《造花園新法序》(1920)
《教宗本篤十五世通牒》譯文(1920)
教育培根社募捐小引(1920)
致英華(1920)
重刻《忍字輯略》序(1921)
無題(1921)
致英華(1921)
致英貞淑(1921)
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1922)
《康墨林戒弟書》書后(1922)
致英華(1922)
致英貞淑(1922)
致楊千里(1922)
《致知淺說》付刊敘(1923)
《致知淺說》小引(1923)
《原言》自序(1923)
致英華(1923)
致英貞淑(1923)
致劉少坪(1923)
致英華(約1923)
二黃司鐸輝烈、誠烈祖母劉太夫人百歲記(1924)
覆徐季龍先生電(1924)
《尤其反對基督教理由》書后(1924)
致英華(1924)
美國本篤會士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書稿(1925)
致英華(1925)
《芝加哥萬國圣體大會事理之說明》譯文(1926)
《天民報》發刊詞(1926)
致徐宗澤(1926)
致英華(1926)
致英千里(1926)
羅馬教廷錫封瓦嘉郡司牧代任宣化區司教趙公墓堂碑(1927)
問謀叛專制與謀叛共和其罪孰大(約1927)
《胡明復先生遺稿》序(1928)
致陸徵祥(1928)
謝剛總主教書(1928)
《圣難繹義》敘(1928)
釋景教(1928)
教廷使署志(1929)
代譯《教廷駐華代表上主席書》(1929)
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1929)
統一經文芻議(1929)
《納氏英文法講義》敘(1929)
致徐宗澤(1929)
致陳垣(1929)
威縣蘂軒張府君墓表(1930)
題《徐季龍先生墨跡》(1930)
題墨井道人畫(1930)
九一壽辰演說詞(1930)
《〈孝經〉之研究》序(1930)
江蘇省《通志》局宗教一門囑擬之稿(1930)
致徐宗澤(1930)
《歷代軍事分類詩選》敘(1931)
息焉公墓碑記(1931)
勸國人慰勞東北抗日軍隊(1931)
致陸徵祥(1931)
九二老人病中語(1931)
《世界雜志》題詞(1931)
致徐宗澤(1931)
備忘錄(約1931)
六十年來之上海(1932)
《李誦清堂述德錄》序(1932)
致陸徵祥(1932)
《勒賽夫人日記》與《日思錄》序(1932)
《宗座代表駐華十周年大慶特刊》發刊詞(1932)
題《磐石雜志》創刊號(1932)
跋《中國民治促成會發起宣言》(1932)
與熊希齡、章太炎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通電(1932)
致徐宗澤(1932)
國貨年獻詞(1933)
聯合宣言甲(1933)
聯合宣言乙(1933)
聯合宣言丙(1933)
警國人勿幸小勝(1933)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詞(1933)
求為徐上海列品誦(1933)
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1933)
贈科學研究會(1933)
致陸徵祥(1933)
勉馮玉祥電(1933)
致馮玉祥通電(1933)
致宋哲元通電(1933)
雙十節獻詞(1933)
國貨展覽會演說詞(1933)
《南海黃竹岐鄉何氏譜》序(1933)
十誡序論(1933)
宗教與文化(1933)
致陳垣(1934)
致于斌(1934)
贊許章太炎講學(1935)
民治私議(1935)
聯邦議(1935)
《童鮑斯高圣傳》序(1935)
題贈丁在君先生(1935)
題贈映珹(1935)
勸國人節約拯救水災書(1935)
致復旦大學學生書(1935)
耶穌圣心敬禮短誦(1936)
《救世福音對譯》敘(1936)
貝沙羅司牧馬師大裔族費來弟氏安德勒自序(1936)
教宗比阿九世答法文譯者饒寶褻封菜山巒司鐸
譯文及按語(1936)
蘇聯對中國毫無野心(1936)
題贈全救第二次執委會詞(1936)
致馮玉祥(1936)
題馬建忠著《東行三錄》(1936)
救國談話(1936)
學術傳教(1936)
致馮玉祥(1937)
南海何君墓志銘(1937)
家產立典記(1937)
致徐宗澤(1937)
致李蔭西(1937)
《申報》發行港版感言(1938)
精誠團結一致對外(1938)
家書選輯
馬相伯年譜簡編
上朝鮮國王條陳(約1882)
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約1882)
改革招商局建議(1885)
致汪康年(1896)
務農會條議(1897)
論葉君《條議書》(1897)
槍不殺人(1897)
炮臺新制(1897)
利瑪竇遺像題詞(1897)
徐光啟遺像題詞(1897)
湯若望遺像題詞(1897)
南懷仁遺像題詞(1897)
致汪康年(1897)
致汪康年(1898) 導言
上朝鮮國王條陳(約1882)
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約1882)
改革招商局建議(1885)
致汪康年(1896)
務農會條議(1897)
論葉君《條議書》(1897)
槍不殺人(1897)
炮臺新制(1897)
利瑪竇遺像題詞(1897)
徐光啟遺像題詞(1897)
湯若望遺像題詞(1897)
南懷仁遺像題詞(1897)
致汪康年(1897)
致汪康年(1898)
捐獻家產興學子據(1900)
致朱志堯(1900)
開鐵路以圖自強論(1901)
興學筆錄(1902)
震旦學院章程(1902)
致英華(1902)
《拉丁文通》敘言(1903)
致汪康年(1903)
明故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
前十字記(1903)
前震旦學院全體干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1905)
復旦公學章程(1905)
復旦公學廣告(1905)
中國圖書有限公司招股緣起啟(1906)
《也是集》序(1907)
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1908)
《墨井集》序(1908)
《古文拾級》序(1909)
《求新廠出品圖》敘(1911)
復旦學院廣告(1911)
勸勿為盜布告(1912)
復旦公學招生廣告(1912)
辛亥政見(南華錄)(1912)
致孫中山(1912)
上總統書(1912)
致熊希齡(1912)
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1912)
致董恂士(1913)
致英華(1913)
致英貞淑(1913)
覆丁義華(1913)
《〈新史合編直講〉音譯名稱合璧》引言(1913)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種(1913)
北京法國文術研究會開幕詞(1914)
代擬宋氏山莊碑記(1914)
一國元首應兼主祭主事否(1914)
宗教在良心(1914)
宗教之關系(1914)
信教自由(1914)
一九一五年(1914)
答客問一九一五年(1914)
致英貞淑(1914)
重刊《主制群征》序(1915)
重刊《辯學遺牘》跋(1915)
致英貞淑(1915)
致張漁珊(1915)
題贈楊佑廷(1916)
青年會開會演說詞(1916)
《圣經》與人群之關系(1916)
書《利先生行跡》后(1916)
《萬松野人言善錄》序(1916)
《憲法草案》大、二毛子問答錄(1916)
書《〈天壇草案〉第十九條問答錄》后(1916)
書《請定儒教為國教》后(1916)
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1916)
代擬《反對孔道請愿書》五篇(1916)
憲法向界(1916)
《約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
信教自由(1916)
書《分合表》后(1916)
國民大會說(1916)
農業改良友助社簡章(1916)
呈設農業改良社(1916)
致英華(1916)
致英貞淑(1916)
跋文澂明《懷歸詩》(1917)
《元代也里可溫考》序(1917)
致段祺瑞(約1917)
重刊《真主靈性理證》序(1918)
重刊《靈魂道體說》序(1918)
《言善錄》再版序(1918)
民國民照心鏡(1918)
《民治學會簽名簿》題詞(1918)
致英貞淑(1918)
致英華、英貞淑(1918)
致英華(約1918)
無題(1919)
《明李之藻傳》序(1919)
重刊《靈言蠡勺》序(1919)
答問中國教務(1919)
錄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巡閱使光主教致天津
華鐸書并按(1919)
題《愧林漫錄》(1919)
現今財政以組織收支細則為要務說(1919)
致英貞淑(1919)
致英華(1919)
致陳垣(1919)
致張漁珊(1919)
致張仲仁(1919)
致陳垣(約1919)
代擬《北京教友上教宗書》(1920)
《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跋(1920)
跋《造花園新法序》(1920)
《教宗本篤十五世通牒》譯文(1920)
教育培根社募捐小引(1920)
致英華(1920)
重刻《忍字輯略》序(1921)
無題(1921)
致英華(1921)
致英貞淑(1921)
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1922)
《康墨林戒弟書》書后(1922)
致英華(1922)
致英貞淑(1922)
致楊千里(1922)
《致知淺說》付刊敘(1923)
《致知淺說》小引(1923)
《原言》自序(1923)
致英華(1923)
致英貞淑(1923)
致劉少坪(1923)
致英華(約1923)
二黃司鐸輝烈、誠烈祖母劉太夫人百歲記(1924)
覆徐季龍先生電(1924)
《尤其反對基督教理由》書后(1924)
致英華(1924)
美國本篤會士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書稿(1925)
致英華(1925)
《芝加哥萬國圣體大會事理之說明》譯文(1926)
《天民報》發刊詞(1926)
致徐宗澤(1926)
致英華(1926)
致英千里(1926)
羅馬教廷錫封瓦嘉郡司牧代任宣化區司教趙公墓堂碑(1927)
問謀叛專制與謀叛共和其罪孰大(約1927)
《胡明復先生遺稿》序(1928)
致陸徵祥(1928)
謝剛總主教書(1928)
《圣難繹義》敘(1928)
釋景教(1928)
教廷使署志(1929)
代譯《教廷駐華代表上主席書》(1929)
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1929)
統一經文芻議(1929)
《納氏英文法講義》敘(1929)
致徐宗澤(1929)
致陳垣(1929)
威縣蘂軒張府君墓表(1930)
題《徐季龍先生墨跡》(1930)
題墨井道人畫(1930)
九一壽辰演說詞(1930)
《〈孝經〉之研究》序(1930)
江蘇省《通志》局宗教一門囑擬之稿(1930)
致徐宗澤(1930)
《歷代軍事分類詩選》敘(1931)
息焉公墓碑記(1931)
勸國人慰勞東北抗日軍隊(1931)
致陸徵祥(1931)
九二老人病中語(1931)
《世界雜志》題詞(1931)
致徐宗澤(1931)
備忘錄(約1931)
六十年來之上海(1932)
《李誦清堂述德錄》序(1932)
致陸徵祥(1932)
《勒賽夫人日記》與《日思錄》序(1932)
《宗座代表駐華十周年大慶特刊》發刊詞(1932)
題《磐石雜志》創刊號(1932)
跋《中國民治促成會發起宣言》(1932)
與熊希齡、章太炎等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通電(1932)
致徐宗澤(1932)
國貨年獻詞(1933)
聯合宣言甲(1933)
聯合宣言乙(1933)
聯合宣言丙(1933)
警國人勿幸小勝(1933)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詞(1933)
求為徐上海列品誦(1933)
徐文定公與中國科學(1933)
贈科學研究會(1933)
致陸徵祥(1933)
勉馮玉祥電(1933)
致馮玉祥通電(1933)
致宋哲元通電(1933)
雙十節獻詞(1933)
國貨展覽會演說詞(1933)
《南海黃竹岐鄉何氏譜》序(1933)
十誡序論(1933)
宗教與文化(1933)
致陳垣(1934)
致于斌(1934)
贊許章太炎講學(1935)
民治私議(1935)
聯邦議(1935)
《童鮑斯高圣傳》序(1935)
題贈丁在君先生(1935)
題贈映珹(1935)
勸國人節約拯救水災書(1935)
致復旦大學學生書(1935)
耶穌圣心敬禮短誦(1936)
《救世福音對譯》敘(1936)
貝沙羅司牧馬師大裔族費來弟氏安德勒自序(1936)
教宗比阿九世答法文譯者饒寶褻封菜山巒司鐸
譯文及按語(1936)
蘇聯對中國毫無野心(1936)
題贈全救第二次執委會詞(1936)
致馮玉祥(1936)
題馬建忠著《東行三錄》(1936)
救國談話(1936)
學術傳教(1936)
致馮玉祥(1937)
南海何君墓志銘(1937)
家產立典記(1937)
致徐宗澤(1937)
致李蔭西(1937)
《申報》發行港版感言(1938)
精誠團結一致對外(1938)
家書選輯
馬相伯年譜簡編
書摘/試閱
導言
導言本文原為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拍攝《大師?馬相伯》(2004)一片的策劃稿,修改后作為本書導言。文中的引文和事跡未能一一附上注釋和考訂,具體細節可對照參看本書《馬相伯年譜簡編》。另外,還可在朱維錚主編,李天綱、陸永玲、廖梅編校的《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中核實和參看其他事實。
——“百年之子”馬相伯
1876年,一位三十七歲的神父告別了孤寂的教會生活,離開了上海天主教耶穌會在徐家匯的住院,走進了正在蓬勃發展的上海洋場。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當時已經精通法、英、拉丁、希臘、意大利文,后來在外交場合又學會了日文、朝鮮文。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會培養出的江南才俊,實際上是被急需洋務人才的李鴻章用強硬手段從上海挖掘出來的。舉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馬建忠,很難找出第二個“精通七國語文”的人。李鴻章搞洋務,辦外交,最需要這樣“一以當十”的人才。從此,李鴻章的幕府人才庫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國之命運相終始的馬相伯。
馬相伯(1840—1939),學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歲,被稱為“人瑞”,實在是近現代中國的“百年之子”。1840年,馬相伯誕生在江蘇省鎮江府丹徒縣的一個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陽縣的馬家村。那一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鴉片戰爭爆發。1939年,馬相伯參與抗戰,從上海輾轉到越南諒山,在一座荒涼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國東部的大片疆土在日軍的炮火中淪陷。按中國傳統的紀歲方法,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歲老人”,稱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國人在清朝的專制統治下,拖著辮子艱難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順利。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長壽,對本人來說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馬相伯常常不喜歡自己的高壽,自陳“壽則多辱”。1939年,抗戰大后方的《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用大幅版面為這位“人瑞”祝壽,歷經滄桑的馬相伯卻自嘲地說:“我是一條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拿破侖有一個著名預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醒來將震動世界。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國各方面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但是沒有“蘇醒”,更談不上“振興”。一百年里,變則變矣,巡撫、總督和皇帝不見了,代之以軍閥、省長和大總統;縣學、書院和翰林院不見了,代之以中學、大學和科學院;秀才、舉人和進士不見了,代之以學士、碩士和博士……不斷的社會運動,并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貧困、混亂、腐敗、貪婪、不公正、不負責任的現象到處都是,中國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是,“多難興邦”,“亂世出英雄”,激蕩的一百年里,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們擔當起“振興中華”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特立獨行,艱難問學,最終卓然成家。
說實在,作為一個學者和思想家,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盡管后人編的《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與他學富五車的中西學問相比,實在還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統性不夠。作為學者,他留下的有系統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學教材《致知淺說》。1903年,他創辦的震旦學院開學,即行編寫了這部有關西方哲學的教材。從《致知淺說》來看,馬相伯確實是20世紀初難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學含義的中國人。他借用朱熹《大學章句集注》中對“致知”一詞的定義來翻譯“Philosophy”。“‘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殆即西庠所謂Philosophia,譯言‘愛智學’者歟?”按,Philosophy的本義為“愛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譯的《名理探》已經用了“愛知學”。清末外國傳教士傾向于用“格致學”來對譯Science(科學)而不是Philosophy(哲學),如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萬國公報》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譯為《培根格致新機》,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編的《格致匯編》收入的是聲光化電的新技術。馬相伯受天主教耶穌會訓練,并沒有把科學和哲學完全分離,仍然把格致學廣義地理解為哲學。或者說,把科學歸入哲學,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種階段,一種手段。馬相伯對Philosophy的理解比較傳統,具有天主教哲學的印記,但從今天科學主義思潮過后的哲學史觀點來看,倒是比較全面,比較深入,因而也比較正確一些。
1851年,馬相伯從家鄉江蘇丹徒來上海,先是投親在他的姐夫朱家,當年就進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穌會剛剛創辦的依納爵公學。這所學校對外也稱徐匯公學,后來就發展為有名的徐匯中學。此前,除了馬六甲、澳門和香港有新教傳教士舉辦的西式學校之外,中國內地的西式中等學校以徐匯公學為最早。按耶穌會的本土化策略,也鑒于當時中國文化的強大態勢,徐匯公學給天主教會培養人才,就必須讓中國孩子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徐匯公學除了研習西學之外,也必須教授經學。馬相伯在家鄉已經發蒙,“四書五經”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帶教其他學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親近的老師,意大利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漢學家。晁德蒞精通中國經典,一生的功業就是把“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譯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馬相伯幫助晁德蒞解讀“四書五經”,晁德蒞也教會了馬相伯從歐洲學術傳統來理解中國經典。這種跨文化的學問互動增進了師生間的友誼,他們兩人是一生的朋友。馬相伯之所以能夠比其他學者更早地會通中西學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馬相伯升入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成為修士,決心投身教會事業。經過二十余年的通商、傳教,上海人已經注意到“堅船利炮”背后的西學。據后來的回憶,這一時期的馬相伯和三弟馬建忠仍然還在嘗試舉業,但真正的學問取向顯然已經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已經打下基礎,神學、哲學和科學方面的知識也是造詣不淺。據教會材料,徐家匯的耶穌會神學院辦學水準相當高,課程水平達到巴黎的標準。上海徐匯公學和耶穌會神學院教授的歐洲哲學和科學知識,在遠東沒有第二家。馬相伯的高水準西學,并非個案。他的同班同學李杕(問漁,1840—1911)神父后來在徐匯公學、震旦學院都擔任科學、哲學教習,同光年間也做了大量西學研究、教授和傳播工作,只是很不為外界了解。
1876年,馬相伯在按立為神父之后,終于因為各種原因脫離了教會,離開了徐家匯,轉而投身到淮軍系統將官主持的洋務事業。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馬建忠已經于1874年脫離教會,加入李鴻章的幕府,并留學巴黎,一時看去前程遠大。馬相伯的學問興趣,也在這幾年里從神學和哲學,轉向了天文學、幾何學和力學等科學知識。馬相伯刻苦鉆研,到了夜不能寐、晝生幻覺的程度。同光中興時期,科學是新政的學問,可見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經世之志已定。他決計步二哥馬建勛和三弟的后塵,加入如日中天的淮軍系統,充當幕僚。
在淮軍系統當幕僚期間,馬相伯到過神戶、平壤,也去過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寫公文,辦洋務,處理中外糾紛,推動新式事業,無須著述做學問。馬相伯夠得上大學問家和思想家的標準,他的長處在于能夠從歐洲古典文明的脈絡來理解西方的崛起,還能夠從近代歐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同經驗看清朝的新政,這在當時雖不能說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把馬相伯與王韜、鄭觀應、馬建忠、伍廷芳同列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按后來的教科書,把他們稱“早期改良派”,思想較康有為、梁啟超落后,則完全錯誤。他們是同光年間真正懂得世界事務,又對改革有切實主張的少數幾個人。非常可惜的是,作為一個大學問家,馬相伯這一時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他出眾的洞察力和廣闊的世界觀也沒有得到應有發揮。類似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的著述,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數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們暫時還只見到方豪先生搜集到的《上朝鮮國王條陳》、《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改革招商局建議》三篇。馬相伯投入李鴻章及其他淮軍將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馬建忠一起經歷過無數風浪,《中法新約》(1885)、《馬關條約》(1896)、《辛丑條約》(1900)的簽訂都和兩兄弟有關。1895年,馬建忠將自己游記、日記、奏折、條陳、電稿、書信集中,刊印了《適可齋記言記行》,馬相伯卻沒有留下自己的“記言記行”。
馬相伯述而不作的個性,大概和耶穌會注重口頭宣道,不鼓勵著書立說的神父訓練有關。但是,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在于天主教會與清朝士大夫社會懸隔太深,社會上不需要、不理解耶穌會的學問。同光年間,西方教會和中國社會之間還隔著一堵墻,馬相伯的西學只能在教會研習,它的社會傳播卻被隔離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學傳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9世紀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之前,西學并不流行。英、美新教傳教士的醫療、學校、出版、新聞等間接傳教事業雖早就舉辦,但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開來。所以,馬相伯沒有留下早期著作,和這樣保守的大環境有直接關系。
1893年以后,馬相伯連遭厄運。當年,他的妻子攜襁褓中的幼子回山東娘家探親,因海輪失事罹難;1895年,虔誠信教的母親沈氏去世前,對他離開教會深有責備;1896年,《馬關條約》簽訂,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黨”輿論指為漢奸。內憂外患,馬相伯很是沮喪,終于決定在離開耶穌會二十余年以后,回到徐家匯,息影在土山灣孤兒工藝院老樓。這時候的馬相伯,決心拋開紅塵,一心著述。馬相伯的歸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閡這堵墻,他可以把西學傳播到社會,也可以把外界對西學的需求引入教會。可惜,馬相伯這樣的著述開始得太晚!更有甚者,六十多歲的馬相伯,不久又復出了!人在徐家匯,心在張園、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憲、光復運動。辛亥革命以后,馬相伯又北上參政,經年不歸。種種活動令他不遑教課、寫作,很遺憾沒有留下更多的學術作品。
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學養未能充分彰顯,這是中國學術的重大缺憾。馬相伯是一流學者,這一點既可以從《致知淺說》中看到,也可以他審定、刊印的《馬氏文通》予以印證。學界對記在馬建忠名下的《馬氏文通》評價甚高,認定其是漢語言學的奠基之作。我們相信,馬相伯是本書的作者之一,馬氏兄弟的感情、經歷、學問和思想,幾乎完全一致。馬相伯的學識,肯定不在他的弟弟之下。1904年,馬建忠去世多年之后,馬相伯整理、刪定了《馬氏文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馬氏“難弟難兄”(王韜語)的學識,如當時學者承認的“嚴、馬、辜、伍”(章太炎語)一樣,均屬于第一流。
原想避開紅塵,避靜,反省,著述,終老于此。然而,風動,幡動,終而心動,馬相伯并不能逃離政治。無論是住在市區八仙橋附近的馬家豪宅,還是躲在土山灣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層樓房,門前一直都有青年學生來叩門,向他求教西學。到八仙橋、徐家匯跟他學拉丁文,聽他講西學、洋務掌故,談未來中國社會理想,這是從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戰前上海學界的時髦。包括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時、史良在內,連續有幾代人向馬相伯執弟子禮,拜這位老人為師。1901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師范特班,帶領全班24名學生,天天到徐家匯向馬相伯學拉丁文。清晨五點,蔡元培帶著學生從公學步行來到土山灣,等候馬相伯醒來,做完晨禱,跟著老人的口型練習外文。無論寒暑,畢恭畢敬,當得上程門立雪的故事。這批學生中,有后來彪炳中國文化史冊的黃炎培、胡敦復、胡仁源、李叔同、謝無量、于右任、邵力子等。為了傳授拉丁文,馬相伯編寫了《拉丁文通》,該書應該就是中國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為、梁啟超驟得光緒皇帝的信任,6月11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了百日維新。曾經在上海跟馬相伯學習拉丁文的梁啟超,從北京急電徐家匯,邀請已經退隱的馬相伯出山主持議定了的譯學館。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譯學館遷來上海,與徐家匯的耶穌會合作,兩人在書信往返地商議著。梁啟超還向光緒皇帝推薦這位奇才主持全國教育、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學科建設。因為百日維新的夭折,這些事業沒有成功,否則馬相伯就是第一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了。1907年,梁啟超在日本東京籌辦立憲團體政聞社,特請馬相伯前往擔任總務員,主持社政。清末民初,嚴復是西學大師,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這兩位學界泰斗,都尊敬馬相伯的中西學識。章太炎是革命文豪,談起西學,他只佩服“嚴、馬、辜、伍”四個人。“嚴”是嚴復,“馬”就是馬相伯,“辜”是辜鴻銘,“伍”是伍廷芳。馬相伯是西學大師,戊戌變法前后,梁啟超辦《時務報》(1896),張元濟辦商務印書館(1907),都曾到市區馬寓,甚至驅車到徐家匯,追隨馬相伯的西學。
六十歲之前,馬相伯把自己的才智貢獻給了清朝。為了一個扶不起的清朝,馬相伯貼進去二十多載的壯年生涯。1900年天下大亂的時候,馬相伯已經不在旋渦中心。1893年,在輪船招商局的一場海難中他喪妻失子。1895年,母親沈氏去世前,責備他沒有當個好神父。再一年后,因參與《馬關條約》談判,馬氏兄弟身受鋪天蓋地的“漢奸”罵名。清朝的前途和自己的命運,都令馬相伯失望。正是這時期,他決定退回上海,息影徐家匯。他的弟弟馬建忠則卷入太深,簽訂《辛丑條約》的時候,又被李鴻章找去,和八國聯軍代表沒日沒夜地談判。陷在翻譯不完的英、法、德、俄、意、日文的談判文件堆中,累死在案桌前。甲午戰爭前,朝鮮危亡。李鴻章曾對馬相伯說:“大清國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何況高麗?”清朝從內里腐敗掉了,快要滅亡,李鴻章、馬建忠、馬相伯這樣參與機密的官員看得最清楚。六十歲以后,馬相伯決計離開官場,為中國的年輕人,為民族的新文化作一點貢獻。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于古代君主來說,祭祀(宗教)和軍事是根本大事,強大的軍隊,宏大的宗廟,是王朝強盛和繁榮的象征。但是,中國要走出專制制度,步入文明社會,需要王朝之外的公共領域。對于19、20世紀中國的孔急之事,開辟、繼承和傳播現代知識的學術機構——大學才是最為重要的。大學是民族之魂,國家之本。現代社會的基礎是文化和教育,而不是宗教和軍事。沒有大學的引導,中國走不出傳統的王朝社會。在傳統的私塾、書院和縣學里,背“四書”,查“五經”,不學外語,不讀數、理、化,國家沒有出路。更重要的是,沒有大學,不培養專業精神,不鼓勵獨立人格,青年人蒙昧,成年人顢頇,老年人固執,正在把這個傳統文化深厚的民族拖入深淵。大學之道,是使中國擺脫困境的正途。老馬識途的馬相伯,是最早認識這一點的中國人。
中國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起源于基督教傳教士舉辦的教會學校。1903年,馬相伯決心創辦自己的大學時,他的周圍已經有了幾所私立學校。1879年,美國圣公會從本國募來巨款,在上海創辦了圣約翰書院。1901年,美國循道會傳教士合并了幾所中等學校,在蘇州創辦東吳大學。此外,在北京、武漢、杭州、長沙等地都陸續出現了一些教會學校。另一方面,面臨崩盤的清朝政府為了挽救局勢,不得不在甲午戰敗后創辦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由李鴻章策劃,盛宣懷籌辦了天津北洋大學堂;1896年,盛宣懷又籌建了上海南洋公學;1898年,為了落實維新條例,朝廷創辦了京師大學堂。這些學校,雖只能傳習一些簡單的英、法、俄、日文和零星的聲光化電知識,程度不高,但已經算是最早的國立大學了。
舉辦新式高等教育是國家大事,理應由政府來推動。但是,從官場上退出來的馬相伯深知朝廷做事,十九不成功。歷次挫折,使他對清朝早已失望,便決心以一己之力創辦大學。馬相伯要辦一所以歐洲為樣板的私立大學。搞實業賺錢,辦學校燒錢,辦大學需要的大筆資金哪里來?中外人士目睹了一場令人驚詫的豪舉:1900年8月25日,即“光緒庚子又八月一日”,馬相伯立下了《捐獻家產興學字據》,把自己名下的財產全部獻了出來,作為辦學基金,“愿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獻于江南司教日后所開中西大學堂,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這筆財產不是小數目,它們是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良田,上海法租界的十幾畝地產,還有其他不少零星的工商業資產。用這些基金,辦一所私立大學綽綽有余。馬相伯是震旦學院的出資人,復旦公學的籌款人,也是兩校的首任校長,稱他為“震旦之父”、“復旦之父”恰如其分。馬相伯一本淡泊名利的教友性格,沒有留下多少與二校相關的材料作為自己的榮耀。除了捐獻字據之外,我們只搜集到1905年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分裂之際發表在報紙上的《前震旦學院全體干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和《復旦公學章程》兩份資料。此外,馬相伯在北京參與了輔仁大學的籌建,也有不少捐助,還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對這些他都寡淡視之,只在別人保留的書信中偶爾提及,自己并不炫耀。
馬相伯是一介書生,兩袖清風。當修士和神父的時候,穿圣袍,吃食堂,手不摸鈔票。“下海”后雖然給李鴻章當幕僚,參與洋務,卻從來不掌管經濟實權。馬相伯富家子、士大夫和出家人的灑脫性格,使其視金錢如糞土,無心為自己私蓄財富。他晚年得到了巨額財富,但全不是他自己賺來的。財富來自家族,來自他大哥和大姐繼承的另一種善賈家風。馬氏兄弟中,二哥馬建勛從太平天國動亂時期起就給李鴻章的淮軍采辦軍火、糧草,是淮軍的“糧臺”。戰亂期間,馬家在上海八仙橋地區開商號,財富不下于在杭州為左宗棠“糧臺”的胡雪巖。大姐嫁給了董家渡朱家,馬相伯的外甥朱志堯,是上海最大的民營機器業求新造船廠的老板,擔任過上海總商會會長。馬家、朱家為同光時期上海商界翹楚。二哥去世后,沒有子嗣,全部財產都分給了二位弟弟。馬氏兄弟是上海驕子,在官場,馬家兄弟是淮軍的智囊,深與朝廷機密;在商場,馬家是上海開埠后少有的成功者,富甲一方;在學界,馬相伯、馬建忠是公認的人才,在外語、西學方面罕有匹敵。馬相伯完全可以留在政界、商界,充分享受權力和金錢帶來的世俗快樂。但是,就在人人都為財富奔忙,個個都嫌收入太少的上海,馬相伯拿出巨額的財富,拋卻洋場的繁華,毀家興學,重歸教會。
馬相伯是“裸捐”,財產捐光后,他留下兒子馬君遠在法租界獨立生活,自己只身回到徐家匯,重過隱修生活。息影徐家匯的時候,馬相伯開始翻譯《圣經》。天主教會對《圣經》翻譯比較謹慎,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白日升(Jean Basset, 1645—1715)曾翻譯過一部《四史攸編》,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也曾有過一部《古新圣經》,但是都沒有公開出版,只供神父自己參考用。20世紀中,羅馬教廷對《圣經》的翻譯逐漸放松,馬相伯帶著為中斷教會生活二十多年的贖罪心理,決心以他的中西學識來完成這項事業。從1897年開始,歷時十數年,他翻譯的《新史合編直講》終于在1913年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無論如何,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而且出版了的中文《圣經》。馬相伯忠誠于天主教會,這是無疑的。1897年,他撰寫了《利瑪竇遺像題詞》、《徐光啟遺像題詞》、《湯若望遺像題詞》、《南懷仁遺像題詞》。1915年,土山灣孤兒工藝院用上述題詞,創作了中國天主教四大重要人物畫像,參加了舊金山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現今真跡仍存于舊金山大學圖書館閱覽室。
本想推卻塵緣,在郊外教堂的鐘聲中摩挲《圣經》,了此殘生。但是,馬相伯沒有料想他長壽,他還有相當長的四十年生命路程要走。1900年以后,中國發生了那么多的變故,把他這位老人又拉了出來,卷到沖突的中心。徐家匯的土山灣離市區有七八里路,上海不斷引進西式馬車、轎車,交通已不是問題。張謇辦江蘇教育會、中國圖書公司,蔡元培辦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都來請教馬相伯。《中國圖書有限公司招股緣起啟》(1906)透露出馬相伯和辛亥革命前的上海精英人物融合在一起。在中國圖書公司的股東中,除了發起人張謇(狀元、實業家、江蘇巨紳)之外,嚴信厚(中國通商銀行總董、上海總商會會長創始人)、周晉鑣(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上海總商會會長)、李平書(上海縣自治運動領袖)、席裕光、席裕成、席裕福(三人均為銀行家)等之外,馬相伯把富豪外甥朱志堯(號開甲,上海總商會會長、實業家)拉進來,可見他在地方自治和預備立憲運動中有實質性的參與。中國圖書公司的股東結構和1909年預備立憲后建立的江蘇諮議局高度重合,可以證明馬相伯在1905年興辦復旦公學以后,又回到了上海的維新運動中,而且越來越卷到運動的中心。
我們從上海《申報》等報刊報道中知道,馬相伯在張園、福州路、南市有很多演講。例如:1904年5月16日,在上海商學會演講,主題為“商戰”;1905年8月6日,在務本女塾演講,主題為“抵制美貨”;1905年秋,在南京兩江總督府演講,主題為“憲法精神”;1907年11月9日,在上海張園江蘇鐵路公會集會演講,主題為“路權”;1907年11月20日,在上海愚園預備立憲公會集會演講,主題仍為“路權”;1911年6月11日,在上海張園中國國民公會總會成立大會上演講,主題為“尚武”、“民治”,準備光復。非常可惜,馬相伯的個性太瀟灑,真的是述而不作,這些第一流演講,生前都沒有好好整理成文,乃至不傳。
1903年,用馬相伯捐獻的基金,法國耶穌會派出師資,借徐家匯天文臺舊址開辦了震旦學院。馬相伯自訂章程,自任校長,這是一所后來以Aurora聞名于世的精英大學。震旦學院的開辦,正逢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變。清朝廢科舉的議論,已經攪得天下讀書人一片惶恐。士大夫們一肚皮的“四書”功夫將要爛在腸子里,對就要開考的“新科”知識卻一竅不通。很多人急忙從各地趕來上海,到新式學堂進修數理化,惡補西學。馬相伯說,震旦招收的一年級新生中,居然有“八個少壯的翰林(進士),二十幾個孝廉公(舉人)”。馬相伯曾回家鄉參加過科舉考試,雖得過學額,但只是個秀才。四十年之后,科舉制崩潰,大批進士、舉人們,反而投在他的震旦門下。1903年的震旦,法國耶穌會還沒有介入,辦學方針由馬相伯自己決定。按馬相伯自訂的《震旦學院章程》,“分文學Literature、質學(日本名之曰科學)Science兩科”。兩科內容,就是外語和哲學,都由馬相伯審定,外語學拉丁文,哲學學笛卡爾。震旦初期的馬相伯,還在猶豫是按明末西學傳統,把Science翻譯成“質學”(方以智用“質測”),還是按日本近世“蘭學”傳統,翻譯成“科學”。無論如何,震旦的課程在上海學子中普及了科學精神。輾轉相傳,遂在十多年后衍為北京《新青年》的“賽先生”。
震旦學生中,還有南洋公學轉來的另一批精英學生。當時,正逢南洋公學的學生鬧學潮,一大批學生退學。退學學生們一部分跟隨辭職的蔡元培,加入了新成立的愛國學社,另一部分學生則來到震旦學院,其中就有后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留美博士的胡敦復,此外還有民國元老于右任、邵力子。1905年,震旦學院學生又鬧起了學潮,結果就是復旦公學的誕生。20世紀的頭幾年,上海學生們動輒鬧學潮,這是有原因的。科舉制廢除前后,江南的讀書人忽然明白,未來將是英文、法文和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主宰的時代。于是,棄“四書五經”如敝屣,一等有錢留“西洋”(歐美),二等有錢留“東洋”(日本),三等有錢就到上海去,挑一個公立、私立的新學堂,算是“小出國”、“窮留學”。于是,上海傳教士和洋務人士冷冷清清辦了幾十年的新學校,忽然遇見了黃金時代。學生們對新學堂缺乏認識,對舊學問又恨又愛,心理浮躁。入學、退學,出國、回國成為時髦,一遇不滿,就鬧學潮。大量年輕的秀才、舉人拋棄舊學,涌到上海補習新學、西學。他們其實是清朝一次次失敗改革的受害者,在內地積累了很多不滿,遇到上海的學校里鼓勵獨立自主,租界里保障言論自由,就天不怕地不怕地爆發出來。
1905年震旦學院學潮中,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等帶領學生向掌管教學的法國耶穌會士抗議。這一次,學生們不是要脫離學校,而是要占領學校。學生們帶走了部分實驗設備、動植物標本和書籍等,趕走法國老師,宣稱自己要獨立舉辦震旦。按馬相伯后來的解釋,爭端的起因是震旦的“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我意見不合,遂脫離關系而另組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復旦”。當初情況比馬相伯的回憶要復雜得多。上海學生不愿意學法語,因為法語在洋場不及英語那樣有用。震旦學潮,并不起因于中、法民族之爭,而是英、法文何為“一外”的問題。馬相伯選了畢業于耶魯大學的李登輝來掌校,而后來的復旦公學改為商科為主,就是這個道理。剛剛接手校務的法國巴黎省耶穌會士一時難以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于是,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帶領學生,再度造反,脫離震旦。
學潮不是馬相伯發動的,甚至是有點沖著他去的。學生要學實用的英語,不愿學法文,更不用說拉丁文、歐洲哲學等古典學科。從經典轉為實用,并不是不可以商議,但與當初的震旦章程相違背。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和擔任教務長的法國耶穌會士南從周就法文教學鬧翻后,帶著學生們來見馬相伯,要求校長脫離法國人,自辦震旦。馬相伯捐款給教會的時候,立下了不得反悔的死約,學校基金不可能收回。在震旦和學生的僵持之中,學校難以為繼,學生將要失學,馬相伯急得哭起來。胡敦復、于右任和邵力子是馬相伯最好的學生,他們要走,馬相伯只好奉陪。最后,校長站在了學生“造反派”一邊,把震旦留給法國耶穌會管理,自己另起爐灶。花甲之年的馬相伯拼了老命,再創辦一所大學。復旦公學的創辦,基本上也是馬相伯一個人的功勞。馬相伯在震旦與復旦之間吃了三夾板,最終卻難能可貴地再創了一個后來愈顯重要的大學。可惜的是,這一時期的馬相伯也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文章、文獻、日記和回憶文章,只在晚年一番云淡風輕的談話中提到。
從戊戌到辛亥,這一時期全國變法、立憲和革命思想界唯馬相伯“馬首是瞻”,他發表的觀點、談話、演講和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南北議和的時候,一位暗探在和馬相伯談話后,密報惜陰堂主人趙鳳昌,作為代表南方共和派人物主張的《辛亥政見》。馬相伯的中西學識確實比他人高明,在非常復雜的宗教問題上尤其如此。戊戌變法以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以不同方式把宗教信仰與政治制度聯系起來。康有為提出要建立“孔教”,譚嗣同把佛學、儒學和神學融合為“仁學”,章太炎則提出了一種以佛學唯識論為根底的“建立宗教論”。1907年,在這方面比較沒有見解的梁啟超在東京籌建政聞社,采用了馬相伯的“神我憲政說”作為社綱。目前我們還未見到“神我憲政說”的完整文本,只是通過章太炎的《駁神我憲政說》了解到這一學說的基本看法。按馬相伯理解,人性有本于動物性的“形我”,有本于精神性的“神我”。人類基于“神我”的結合,是有信仰、有精神的結合,馬相伯宣布:“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政聞社。”馬相伯用“形我”、“神我”的概念表達宗教信徒的社會理想:以“神”的名義組織人間社群團體,而不是蠅營狗茍搞黨派。按現代政黨理論來判斷,這種帶有宗教理想主義的政黨主張,比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和孫中山的偏頗之論公允得當一些。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體制建設中出現了紛繁的宗教問題。例如:國體層面的政教關系問題,倫理層面的信仰自由問題,不同宗教之間的宗教寬容問題,很復雜地糾纏在一起。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搞了尊孔、讀經、祭天等國家宗教活動;康有為執拗地籌建著孔教會,企圖一面借著孔教組織的影響來參政,一面以孔教思想抵御基督教信仰;不少維新人士延續戊戌變法時期移風易俗、教產興學的主張,打擊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間;更多的一般民眾則感覺到時代更替中的道德淪喪,不斷呼吁宗教信仰的回歸,“大聲疾呼曰:提倡宗教!提倡宗教!”中國古代思想家,對現代國家制度中的政教分離、信仰自由、宗教寬容原則并沒有系統的理論,而徐家匯出來的馬相伯在這方面正好有著長期思考。比較起來,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談宗教,馬相伯既理解中國古代傳統,也懂得世界近代思潮,最站得住腳。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布尊崇孔圣令;冬至日,袁世凱到天壇親自祭天。馬相伯當然知道康有為、夏曾佑在此背后鼓搗的孔教,并且識別出這是一種政教合一和國家宗教的做法,有違中華民國設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憲法精神。馬相伯堅持現代國家原則,在《一國元首應兼主祭主事否》中明確堅持信教自由,認為中國歷代固然是天子祭天,但信教自由的民國,元首與主祭不得一人相兼,因為:“元首者,乃五族五教人唯一元首,非一族一教人所得而入主出奴之。”比一般人更加機智的是,馬相伯采用了儒家傳統的君師相分原理來說明政教分離,“不惟不兼主祭,而君與師之職亦不相兼焉”。按儒家原理,師者,儒也。君主接受儒教,君主不得為導師。既不得為導師,便不能為教主,更不能為偶像崇拜的對象,儒家確實是這樣堅守的。馬相伯懂得儒家精髓,向康有為、袁世凱怪誕扭曲的孔教予以有力一擊。
馬相伯同一時期的文章有《信教自由》(1914)、《〈憲法草案〉大、二毛子問答錄》(1916)、《書〈請定儒教為國教〉后》(1916)、《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1916)、《代擬〈反對孔道請愿書〉五篇》(1916)、《憲法向界》(1916)、《〈約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信教自由》(1916),都是他抗議袁世凱、康有為等人的孔教、國教行為,為政教合一方案辯護的文章。1916年的馬相伯似乎真是急了,寫了那么多的抗議文章。我們看到,身為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馬相伯卻堅決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的主張。他的抗議態度,肯定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天主教教會的利益。但是,細看馬相伯的分析,他主張中華民國的儒、道、佛、回、耶,無分本土還是外來,“五教”都要與政治生活分離。“五教”平等,相互之間則容易建立寬容、平等、對話和共融的關系。這些主張,無疑更符合當時中國的宗教格局。
中華民國肯定不能建立一個國家宗教,但是一般人群的生活是否還需要宗教?世俗社會的倫理建設是否還要用信仰來支撐?宗教信仰在中國人的民眾社會中應該起怎樣的作用?20世紀初年的大部分中國思想家,都是急急忙忙地臨時考慮這些問題。馬相伯畢竟當過神父,他是從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畢業出來的神學博士,因而對此問題有著比較長期的思考,回答起來也是比較從容。也是在北京從政期間,他在《宗教在良心》(1914)、《宗教之關系》(1914)、《青年會開會演說詞》(1916)、《〈圣經〉和人群之關系》(1916)一系列演講和論文中闡釋了自己的主張。馬相伯和大家一樣,也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風氣概括為“風俗澆漓,紀綱廢弛,世道人心,大壞大壞!”作為一個神學家,他也和大家一樣,認為:“思從而補救之,以為非有宗教不可。”但是,當時提倡宗教的大偉人、大名士、大政客、大官僚都認為,“宗教者,為下等社會而提倡”,言下之意是精英人士并不需要宗教。把宗教看做社會控制的工具,用以管理愚夫愚婦的下等人,這種陳腐見解為馬相伯所不屑。馬相伯的說法很簡單,無論貧富、貴賤、智愚,“宗教在良心”,人人都可以從宗教信仰中獲得道德資源。這種說法被幾年以后冒起來的“新青年”們忽視了,他們用科學打擊宗教,進而發展出一種徹底的無神論。終不能淹沒的是,一百年后,“馬相伯問題”又似曾相識地歸來了。馬相伯留下的作品,以1914年到1916年在北京和袁世凱、康有為、夏曾佑爭論時所發表的宗教論述最有思想價值。同時代的思想家中,包括章太炎、嚴復、梁啟超、蔡元培等人,也數馬相伯的觀點最能明心見性地切入信仰本身,最為全面地涉及了宗教與中國近代社會的關系,而且相對正確。
對國共兩黨的政治家而言,馬相伯的生命意義有所不同。按他們的看法,馬相伯的價值不在于從事洋務,主張立憲,也不在于創建震旦、復旦,參與辛亥革命,更不在于他反對國教,提倡宗教,豎立良心,而在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挺身而出,發表了眾多的抗戰言論。本來,馬相伯“八十后厭聞時事,宗教書外,間閱科學各月刊”,不打算過問政治。但是,1931年九一八后,各方為黨派利益爭執不下,仍然置日本入侵于不顧。馬相伯只得又一次走出徐家匯,在上海的會場、劇院、電臺、學校拼命演講,奮筆揮毫,主題都是“還我河山”!奇怪!一個民族,因為陷入內戰,無法協商政治、發展經濟,不能建立現代國防,坐視領土淪喪,民眾逃亡,居然還需要一位耄耋老人出來大聲疾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本身是件很不人道的事情!1937年八一三以后,馬相伯以九八之年,跟隨西遷的洪流,經廣西桂林,輾轉到越南諒山的一個山洞里躲避。顛沛流離,馬相伯于1939年11月4日遽然去世,良可嘆也!當年的4月5日,是馬相伯的百歲誕辰,國民黨中央發來了褒獎令,內稱“民族之英,國家之瑞”,中共中央的賀電則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馬相伯生命的最后意義,就是讓一些立場不同的黨派群體有一個擱置爭議,想到國家、民族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片段時刻。
馬相伯的抗戰言論,1933年有馬相伯秘書徐景賢編輯的《國難言論集》,由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刊行;1936年又有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的《一日一談》,由上海復興書局刊行。前書輯錄了馬相伯在上海、香港、天津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其中有演講、訪談、報道、題詞、回憶錄等等,不能完全算是馬相伯的親筆作品。后書是年輕人對馬相伯往事回憶的記錄,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核實,存在誤差。這兩部作品,均存于朱維錚主編、李天綱等編校的《馬相伯集》中,讀者可以自行參看,本書因篇幅限制,不加收入。另外,這次在《申報》等處找到一些確定屬于馬相伯自己撰寫的抗戰通電、文章,如與他人聯名發表的《聯合宣言甲》(1933)、《聯合宣言乙》(1933)、《聯合宣言丙》(1933)、《〈申報〉發行港版感言》(1938)、《精誠團結一致對外》(1938),則加以收入。
這一時期的馬相伯,受到救國會等組織年輕人的推崇,更加的被人“唯馬首是瞻”。因為支持抗戰政治家的活動,馬相伯與宋慶齡、楊杏佛、沈鈞儒、史良、王造時、鄒韜奮、章乃器等人有交誼,他甚至還是魯迅治喪委員會的成員。然而,這一時期和馬相伯在國家、民族和國學方面最為投契的,確是過去與他很是暌違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抗戰言論和馬相伯非常一致,他們在國家、民族、政體、黨派、國學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共識。為反對獨裁,停止黨治,政治協商,組織國民政府,挽救中華民族,兩人聯署了很多文件。章太炎去世之前在蘇州國學傳習所講學,馬相伯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在《申報》專門發文《贊許章太炎講學》(1935),稱贊他:“樸學鴻儒,當今碩德。優游世外,卜筑吳中。……值風雨如晦之秋,究乾坤演進之道。體仁以長,嘉會為群。網羅百家,鉆研六藝。綱紀禮本,冠冕人倫。……”這樣的贊語,挑剔如章太炎,也是應該滿意的。
現代學者追求著作等身,古人卻更加推崇述而不作,馬相伯基本上是個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孔子、蘇格拉底、朱熹、王陽明,大都是靠聚眾講學和身體力行留下自己的思想和學問。從此情景來看,馬相伯沒有留下很多專著,或許是可以理解。馬相伯辦了震旦、復旦,稱他為老師的后來都成了大師: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黃炎培……馬相伯似乎應該就是大師的大師了。問題在于,這些晚輩大師們雖然都愛他,敬他,利用他,實際上卻都沒有傳承馬相伯的學問。然而,思想是可以口傳的。清末的上海,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誰都可以發表政見,表達思想。政客要人、文豪大家、熱血青年中,總是馬相伯的演講有理有據,還最具表現魅力。梁啟超聽過馬相伯的演講,佩服地說他是“中國第一演說家”。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報紙曾經把兩個“反串”角色評論為:“馬相伯演講象唱戲,潘月樵唱戲象演講。”那是海派名角潘月樵喜歡在唱京戲時高喊革命口號,馬相伯的政治演講則繪聲繪色,詼諧有趣。幸虧馬相伯還能演講,晚年尤其如此,現今才留下了一些作品。
馬相伯不是一個強人,三十五歲以前的耶穌會士訓練,使得他養成了豁達、服從的個性;六十歲以前給李鴻章做幕僚的生涯,更發展了他敏銳、謹慎的個性。馬相伯的詼諧幽默,超然豁達,是作為神父的基本功而訓練出來的。天主教徒的身份,還有他曾經是耶穌會神父的經歷,讓他能夠透視中國問題,成為超然于黨派政治之外,為中國社會的長遠利益考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馬相伯絕無那種爭勇好斗的強辯性格,也沒有明顯的黨派色彩。馬相伯固然是一個未能盡職的神父,其實也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或者說他根本就是一個不斷被政客們利用的學問家。
歷史學家總是把鴉片戰爭看做中國文化由盛轉衰的關節點。一百年間,大師輩出。以年齡論,生于1840年的馬相伯正可以說是這鴉片戰爭后涌現的幾代偉人中的第一位大師。馬相伯出生以前的儒者,可能飽讀經書,舊學精湛,但是對西方文化終究隔膜;馬相伯逝世以后的學者,留學歐美,新學熟練,但是與中國文化傳統漸行漸遠。馬相伯和他的學生們,夾在古今中外當中,既熟悉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又剛剛經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這是他們的時代特權。他們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傳統,馬相伯,真的是大師中的大師。
本書選編,若無特別說明,均出自朱維錚主編、李天綱等編校的《馬相伯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收文稿中凡屬明顯錯字的,以〔〕內之字改正之;明顯脫字,以〈〉內之字補充之。
導言本文原為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拍攝《大師?馬相伯》(2004)一片的策劃稿,修改后作為本書導言。文中的引文和事跡未能一一附上注釋和考訂,具體細節可對照參看本書《馬相伯年譜簡編》。另外,還可在朱維錚主編,李天綱、陸永玲、廖梅編校的《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中核實和參看其他事實。
——“百年之子”馬相伯
1876年,一位三十七歲的神父告別了孤寂的教會生活,離開了上海天主教耶穌會在徐家匯的住院,走進了正在蓬勃發展的上海洋場。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當時已經精通法、英、拉丁、希臘、意大利文,后來在外交場合又學會了日文、朝鮮文。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會培養出的江南才俊,實際上是被急需洋務人才的李鴻章用強硬手段從上海挖掘出來的。舉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馬建忠,很難找出第二個“精通七國語文”的人。李鴻章搞洋務,辦外交,最需要這樣“一以當十”的人才。從此,李鴻章的幕府人才庫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國之命運相終始的馬相伯。
馬相伯(1840—1939),學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歲,被稱為“人瑞”,實在是近現代中國的“百年之子”。1840年,馬相伯誕生在江蘇省鎮江府丹徒縣的一個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陽縣的馬家村。那一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鴉片戰爭爆發。1939年,馬相伯參與抗戰,從上海輾轉到越南諒山,在一座荒涼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國東部的大片疆土在日軍的炮火中淪陷。按中國傳統的紀歲方法,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歲老人”,稱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國人在清朝的專制統治下,拖著辮子艱難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順利。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長壽,對本人來說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馬相伯常常不喜歡自己的高壽,自陳“壽則多辱”。1939年,抗戰大后方的《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用大幅版面為這位“人瑞”祝壽,歷經滄桑的馬相伯卻自嘲地說:“我是一條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拿破侖有一個著名預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醒來將震動世界。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國各方面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但是沒有“蘇醒”,更談不上“振興”。一百年里,變則變矣,巡撫、總督和皇帝不見了,代之以軍閥、省長和大總統;縣學、書院和翰林院不見了,代之以中學、大學和科學院;秀才、舉人和進士不見了,代之以學士、碩士和博士……不斷的社會運動,并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貧困、混亂、腐敗、貪婪、不公正、不負責任的現象到處都是,中國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是,“多難興邦”,“亂世出英雄”,激蕩的一百年里,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們擔當起“振興中華”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特立獨行,艱難問學,最終卓然成家。
說實在,作為一個學者和思想家,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盡管后人編的《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與他學富五車的中西學問相比,實在還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統性不夠。作為學者,他留下的有系統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學教材《致知淺說》。1903年,他創辦的震旦學院開學,即行編寫了這部有關西方哲學的教材。從《致知淺說》來看,馬相伯確實是20世紀初難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學含義的中國人。他借用朱熹《大學章句集注》中對“致知”一詞的定義來翻譯“Philosophy”。“‘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殆即西庠所謂Philosophia,譯言‘愛智學’者歟?”按,Philosophy的本義為“愛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譯的《名理探》已經用了“愛知學”。清末外國傳教士傾向于用“格致學”來對譯Science(科學)而不是Philosophy(哲學),如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萬國公報》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譯為《培根格致新機》,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編的《格致匯編》收入的是聲光化電的新技術。馬相伯受天主教耶穌會訓練,并沒有把科學和哲學完全分離,仍然把格致學廣義地理解為哲學。或者說,把科學歸入哲學,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種階段,一種手段。馬相伯對Philosophy的理解比較傳統,具有天主教哲學的印記,但從今天科學主義思潮過后的哲學史觀點來看,倒是比較全面,比較深入,因而也比較正確一些。
1851年,馬相伯從家鄉江蘇丹徒來上海,先是投親在他的姐夫朱家,當年就進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穌會剛剛創辦的依納爵公學。這所學校對外也稱徐匯公學,后來就發展為有名的徐匯中學。此前,除了馬六甲、澳門和香港有新教傳教士舉辦的西式學校之外,中國內地的西式中等學校以徐匯公學為最早。按耶穌會的本土化策略,也鑒于當時中國文化的強大態勢,徐匯公學給天主教會培養人才,就必須讓中國孩子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徐匯公學除了研習西學之外,也必須教授經學。馬相伯在家鄉已經發蒙,“四書五經”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帶教其他學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親近的老師,意大利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漢學家。晁德蒞精通中國經典,一生的功業就是把“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譯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馬相伯幫助晁德蒞解讀“四書五經”,晁德蒞也教會了馬相伯從歐洲學術傳統來理解中國經典。這種跨文化的學問互動增進了師生間的友誼,他們兩人是一生的朋友。馬相伯之所以能夠比其他學者更早地會通中西學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馬相伯升入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成為修士,決心投身教會事業。經過二十余年的通商、傳教,上海人已經注意到“堅船利炮”背后的西學。據后來的回憶,這一時期的馬相伯和三弟馬建忠仍然還在嘗試舉業,但真正的學問取向顯然已經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已經打下基礎,神學、哲學和科學方面的知識也是造詣不淺。據教會材料,徐家匯的耶穌會神學院辦學水準相當高,課程水平達到巴黎的標準。上海徐匯公學和耶穌會神學院教授的歐洲哲學和科學知識,在遠東沒有第二家。馬相伯的高水準西學,并非個案。他的同班同學李杕(問漁,1840—1911)神父后來在徐匯公學、震旦學院都擔任科學、哲學教習,同光年間也做了大量西學研究、教授和傳播工作,只是很不為外界了解。
1876年,馬相伯在按立為神父之后,終于因為各種原因脫離了教會,離開了徐家匯,轉而投身到淮軍系統將官主持的洋務事業。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馬建忠已經于1874年脫離教會,加入李鴻章的幕府,并留學巴黎,一時看去前程遠大。馬相伯的學問興趣,也在這幾年里從神學和哲學,轉向了天文學、幾何學和力學等科學知識。馬相伯刻苦鉆研,到了夜不能寐、晝生幻覺的程度。同光中興時期,科學是新政的學問,可見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經世之志已定。他決計步二哥馬建勛和三弟的后塵,加入如日中天的淮軍系統,充當幕僚。
在淮軍系統當幕僚期間,馬相伯到過神戶、平壤,也去過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寫公文,辦洋務,處理中外糾紛,推動新式事業,無須著述做學問。馬相伯夠得上大學問家和思想家的標準,他的長處在于能夠從歐洲古典文明的脈絡來理解西方的崛起,還能夠從近代歐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同經驗看清朝的新政,這在當時雖不能說是絕無僅有,也是鳳毛麟角。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把馬相伯與王韜、鄭觀應、馬建忠、伍廷芳同列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按后來的教科書,把他們稱“早期改良派”,思想較康有為、梁啟超落后,則完全錯誤。他們是同光年間真正懂得世界事務,又對改革有切實主張的少數幾個人。非常可惜的是,作為一個大學問家,馬相伯這一時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他出眾的洞察力和廣闊的世界觀也沒有得到應有發揮。類似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的著述,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數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們暫時還只見到方豪先生搜集到的《上朝鮮國王條陳》、《致朝鮮京畿道金宏集書》、《改革招商局建議》三篇。馬相伯投入李鴻章及其他淮軍將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馬建忠一起經歷過無數風浪,《中法新約》(1885)、《馬關條約》(1896)、《辛丑條約》(1900)的簽訂都和兩兄弟有關。1895年,馬建忠將自己游記、日記、奏折、條陳、電稿、書信集中,刊印了《適可齋記言記行》,馬相伯卻沒有留下自己的“記言記行”。
馬相伯述而不作的個性,大概和耶穌會注重口頭宣道,不鼓勵著書立說的神父訓練有關。但是,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在于天主教會與清朝士大夫社會懸隔太深,社會上不需要、不理解耶穌會的學問。同光年間,西方教會和中國社會之間還隔著一堵墻,馬相伯的西學只能在教會研習,它的社會傳播卻被隔離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學傳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9世紀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譯西書之前,西學并不流行。英、美新教傳教士的醫療、學校、出版、新聞等間接傳教事業雖早就舉辦,但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開來。所以,馬相伯沒有留下早期著作,和這樣保守的大環境有直接關系。
1893年以后,馬相伯連遭厄運。當年,他的妻子攜襁褓中的幼子回山東娘家探親,因海輪失事罹難;1895年,虔誠信教的母親沈氏去世前,對他離開教會深有責備;1896年,《馬關條約》簽訂,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黨”輿論指為漢奸。內憂外患,馬相伯很是沮喪,終于決定在離開耶穌會二十余年以后,回到徐家匯,息影在土山灣孤兒工藝院老樓。這時候的馬相伯,決心拋開紅塵,一心著述。馬相伯的歸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閡這堵墻,他可以把西學傳播到社會,也可以把外界對西學的需求引入教會。可惜,馬相伯這樣的著述開始得太晚!更有甚者,六十多歲的馬相伯,不久又復出了!人在徐家匯,心在張園、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憲、光復運動。辛亥革命以后,馬相伯又北上參政,經年不歸。種種活動令他不遑教課、寫作,很遺憾沒有留下更多的學術作品。
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學養未能充分彰顯,這是中國學術的重大缺憾。馬相伯是一流學者,這一點既可以從《致知淺說》中看到,也可以他審定、刊印的《馬氏文通》予以印證。學界對記在馬建忠名下的《馬氏文通》評價甚高,認定其是漢語言學的奠基之作。我們相信,馬相伯是本書的作者之一,馬氏兄弟的感情、經歷、學問和思想,幾乎完全一致。馬相伯的學識,肯定不在他的弟弟之下。1904年,馬建忠去世多年之后,馬相伯整理、刪定了《馬氏文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馬氏“難弟難兄”(王韜語)的學識,如當時學者承認的“嚴、馬、辜、伍”(章太炎語)一樣,均屬于第一流。
原想避開紅塵,避靜,反省,著述,終老于此。然而,風動,幡動,終而心動,馬相伯并不能逃離政治。無論是住在市區八仙橋附近的馬家豪宅,還是躲在土山灣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層樓房,門前一直都有青年學生來叩門,向他求教西學。到八仙橋、徐家匯跟他學拉丁文,聽他講西學、洋務掌故,談未來中國社會理想,這是從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戰前上海學界的時髦。包括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時、史良在內,連續有幾代人向馬相伯執弟子禮,拜這位老人為師。1901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師范特班,帶領全班24名學生,天天到徐家匯向馬相伯學拉丁文。清晨五點,蔡元培帶著學生從公學步行來到土山灣,等候馬相伯醒來,做完晨禱,跟著老人的口型練習外文。無論寒暑,畢恭畢敬,當得上程門立雪的故事。這批學生中,有后來彪炳中國文化史冊的黃炎培、胡敦復、胡仁源、李叔同、謝無量、于右任、邵力子等。為了傳授拉丁文,馬相伯編寫了《拉丁文通》,該書應該就是中國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為、梁啟超驟得光緒皇帝的信任,6月11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了百日維新。曾經在上海跟馬相伯學習拉丁文的梁啟超,從北京急電徐家匯,邀請已經退隱的馬相伯出山主持議定了的譯學館。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譯學館遷來上海,與徐家匯的耶穌會合作,兩人在書信往返地商議著。梁啟超還向光緒皇帝推薦這位奇才主持全國教育、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學科建設。因為百日維新的夭折,這些事業沒有成功,否則馬相伯就是第一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了。1907年,梁啟超在日本東京籌辦立憲團體政聞社,特請馬相伯前往擔任總務員,主持社政。清末民初,嚴復是西學大師,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這兩位學界泰斗,都尊敬馬相伯的中西學識。章太炎是革命文豪,談起西學,他只佩服“嚴、馬、辜、伍”四個人。“嚴”是嚴復,“馬”就是馬相伯,“辜”是辜鴻銘,“伍”是伍廷芳。馬相伯是西學大師,戊戌變法前后,梁啟超辦《時務報》(1896),張元濟辦商務印書館(1907),都曾到市區馬寓,甚至驅車到徐家匯,追隨馬相伯的西學。
六十歲之前,馬相伯把自己的才智貢獻給了清朝。為了一個扶不起的清朝,馬相伯貼進去二十多載的壯年生涯。1900年天下大亂的時候,馬相伯已經不在旋渦中心。1893年,在輪船招商局的一場海難中他喪妻失子。1895年,母親沈氏去世前,責備他沒有當個好神父。再一年后,因參與《馬關條約》談判,馬氏兄弟身受鋪天蓋地的“漢奸”罵名。清朝的前途和自己的命運,都令馬相伯失望。正是這時期,他決定退回上海,息影徐家匯。他的弟弟馬建忠則卷入太深,簽訂《辛丑條約》的時候,又被李鴻章找去,和八國聯軍代表沒日沒夜地談判。陷在翻譯不完的英、法、德、俄、意、日文的談判文件堆中,累死在案桌前。甲午戰爭前,朝鮮危亡。李鴻章曾對馬相伯說:“大清國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壽命,何況高麗?”清朝從內里腐敗掉了,快要滅亡,李鴻章、馬建忠、馬相伯這樣參與機密的官員看得最清楚。六十歲以后,馬相伯決計離開官場,為中國的年輕人,為民族的新文化作一點貢獻。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于古代君主來說,祭祀(宗教)和軍事是根本大事,強大的軍隊,宏大的宗廟,是王朝強盛和繁榮的象征。但是,中國要走出專制制度,步入文明社會,需要王朝之外的公共領域。對于19、20世紀中國的孔急之事,開辟、繼承和傳播現代知識的學術機構——大學才是最為重要的。大學是民族之魂,國家之本。現代社會的基礎是文化和教育,而不是宗教和軍事。沒有大學的引導,中國走不出傳統的王朝社會。在傳統的私塾、書院和縣學里,背“四書”,查“五經”,不學外語,不讀數、理、化,國家沒有出路。更重要的是,沒有大學,不培養專業精神,不鼓勵獨立人格,青年人蒙昧,成年人顢頇,老年人固執,正在把這個傳統文化深厚的民族拖入深淵。大學之道,是使中國擺脫困境的正途。老馬識途的馬相伯,是最早認識這一點的中國人。
中國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起源于基督教傳教士舉辦的教會學校。1903年,馬相伯決心創辦自己的大學時,他的周圍已經有了幾所私立學校。1879年,美國圣公會從本國募來巨款,在上海創辦了圣約翰書院。1901年,美國循道會傳教士合并了幾所中等學校,在蘇州創辦東吳大學。此外,在北京、武漢、杭州、長沙等地都陸續出現了一些教會學校。另一方面,面臨崩盤的清朝政府為了挽救局勢,不得不在甲午戰敗后創辦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由李鴻章策劃,盛宣懷籌辦了天津北洋大學堂;1896年,盛宣懷又籌建了上海南洋公學;1898年,為了落實維新條例,朝廷創辦了京師大學堂。這些學校,雖只能傳習一些簡單的英、法、俄、日文和零星的聲光化電知識,程度不高,但已經算是最早的國立大學了。
舉辦新式高等教育是國家大事,理應由政府來推動。但是,從官場上退出來的馬相伯深知朝廷做事,十九不成功。歷次挫折,使他對清朝早已失望,便決心以一己之力創辦大學。馬相伯要辦一所以歐洲為樣板的私立大學。搞實業賺錢,辦學校燒錢,辦大學需要的大筆資金哪里來?中外人士目睹了一場令人驚詫的豪舉:1900年8月25日,即“光緒庚子又八月一日”,馬相伯立下了《捐獻家產興學字據》,把自己名下的財產全部獻了出來,作為辦學基金,“愿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獻于江南司教日后所開中西大學堂,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這筆財產不是小數目,它們是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良田,上海法租界的十幾畝地產,還有其他不少零星的工商業資產。用這些基金,辦一所私立大學綽綽有余。馬相伯是震旦學院的出資人,復旦公學的籌款人,也是兩校的首任校長,稱他為“震旦之父”、“復旦之父”恰如其分。馬相伯一本淡泊名利的教友性格,沒有留下多少與二校相關的材料作為自己的榮耀。除了捐獻字據之外,我們只搜集到1905年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分裂之際發表在報紙上的《前震旦學院全體干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和《復旦公學章程》兩份資料。此外,馬相伯在北京參與了輔仁大學的籌建,也有不少捐助,還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對這些他都寡淡視之,只在別人保留的書信中偶爾提及,自己并不炫耀。
馬相伯是一介書生,兩袖清風。當修士和神父的時候,穿圣袍,吃食堂,手不摸鈔票。“下海”后雖然給李鴻章當幕僚,參與洋務,卻從來不掌管經濟實權。馬相伯富家子、士大夫和出家人的灑脫性格,使其視金錢如糞土,無心為自己私蓄財富。他晚年得到了巨額財富,但全不是他自己賺來的。財富來自家族,來自他大哥和大姐繼承的另一種善賈家風。馬氏兄弟中,二哥馬建勛從太平天國動亂時期起就給李鴻章的淮軍采辦軍火、糧草,是淮軍的“糧臺”。戰亂期間,馬家在上海八仙橋地區開商號,財富不下于在杭州為左宗棠“糧臺”的胡雪巖。大姐嫁給了董家渡朱家,馬相伯的外甥朱志堯,是上海最大的民營機器業求新造船廠的老板,擔任過上海總商會會長。馬家、朱家為同光時期上海商界翹楚。二哥去世后,沒有子嗣,全部財產都分給了二位弟弟。馬氏兄弟是上海驕子,在官場,馬家兄弟是淮軍的智囊,深與朝廷機密;在商場,馬家是上海開埠后少有的成功者,富甲一方;在學界,馬相伯、馬建忠是公認的人才,在外語、西學方面罕有匹敵。馬相伯完全可以留在政界、商界,充分享受權力和金錢帶來的世俗快樂。但是,就在人人都為財富奔忙,個個都嫌收入太少的上海,馬相伯拿出巨額的財富,拋卻洋場的繁華,毀家興學,重歸教會。
馬相伯是“裸捐”,財產捐光后,他留下兒子馬君遠在法租界獨立生活,自己只身回到徐家匯,重過隱修生活。息影徐家匯的時候,馬相伯開始翻譯《圣經》。天主教會對《圣經》翻譯比較謹慎,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白日升(Jean Basset, 1645—1715)曾翻譯過一部《四史攸編》,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也曾有過一部《古新圣經》,但是都沒有公開出版,只供神父自己參考用。20世紀中,羅馬教廷對《圣經》的翻譯逐漸放松,馬相伯帶著為中斷教會生活二十多年的贖罪心理,決心以他的中西學識來完成這項事業。從1897年開始,歷時十數年,他翻譯的《新史合編直講》終于在1913年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無論如何,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而且出版了的中文《圣經》。馬相伯忠誠于天主教會,這是無疑的。1897年,他撰寫了《利瑪竇遺像題詞》、《徐光啟遺像題詞》、《湯若望遺像題詞》、《南懷仁遺像題詞》。1915年,土山灣孤兒工藝院用上述題詞,創作了中國天主教四大重要人物畫像,參加了舊金山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現今真跡仍存于舊金山大學圖書館閱覽室。
本想推卻塵緣,在郊外教堂的鐘聲中摩挲《圣經》,了此殘生。但是,馬相伯沒有料想他長壽,他還有相當長的四十年生命路程要走。1900年以后,中國發生了那么多的變故,把他這位老人又拉了出來,卷到沖突的中心。徐家匯的土山灣離市區有七八里路,上海不斷引進西式馬車、轎車,交通已不是問題。張謇辦江蘇教育會、中國圖書公司,蔡元培辦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都來請教馬相伯。《中國圖書有限公司招股緣起啟》(1906)透露出馬相伯和辛亥革命前的上海精英人物融合在一起。在中國圖書公司的股東中,除了發起人張謇(狀元、實業家、江蘇巨紳)之外,嚴信厚(中國通商銀行總董、上海總商會會長創始人)、周晉鑣(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上海總商會會長)、李平書(上海縣自治運動領袖)、席裕光、席裕成、席裕福(三人均為銀行家)等之外,馬相伯把富豪外甥朱志堯(號開甲,上海總商會會長、實業家)拉進來,可見他在地方自治和預備立憲運動中有實質性的參與。中國圖書公司的股東結構和1909年預備立憲后建立的江蘇諮議局高度重合,可以證明馬相伯在1905年興辦復旦公學以后,又回到了上海的維新運動中,而且越來越卷到運動的中心。
我們從上海《申報》等報刊報道中知道,馬相伯在張園、福州路、南市有很多演講。例如:1904年5月16日,在上海商學會演講,主題為“商戰”;1905年8月6日,在務本女塾演講,主題為“抵制美貨”;1905年秋,在南京兩江總督府演講,主題為“憲法精神”;1907年11月9日,在上海張園江蘇鐵路公會集會演講,主題為“路權”;1907年11月20日,在上海愚園預備立憲公會集會演講,主題仍為“路權”;1911年6月11日,在上海張園中國國民公會總會成立大會上演講,主題為“尚武”、“民治”,準備光復。非常可惜,馬相伯的個性太瀟灑,真的是述而不作,這些第一流演講,生前都沒有好好整理成文,乃至不傳。
1903年,用馬相伯捐獻的基金,法國耶穌會派出師資,借徐家匯天文臺舊址開辦了震旦學院。馬相伯自訂章程,自任校長,這是一所后來以Aurora聞名于世的精英大學。震旦學院的開辦,正逢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變。清朝廢科舉的議論,已經攪得天下讀書人一片惶恐。士大夫們一肚皮的“四書”功夫將要爛在腸子里,對就要開考的“新科”知識卻一竅不通。很多人急忙從各地趕來上海,到新式學堂進修數理化,惡補西學。馬相伯說,震旦招收的一年級新生中,居然有“八個少壯的翰林(進士),二十幾個孝廉公(舉人)”。馬相伯曾回家鄉參加過科舉考試,雖得過學額,但只是個秀才。四十年之后,科舉制崩潰,大批進士、舉人們,反而投在他的震旦門下。1903年的震旦,法國耶穌會還沒有介入,辦學方針由馬相伯自己決定。按馬相伯自訂的《震旦學院章程》,“分文學Literature、質學(日本名之曰科學)Science兩科”。兩科內容,就是外語和哲學,都由馬相伯審定,外語學拉丁文,哲學學笛卡爾。震旦初期的馬相伯,還在猶豫是按明末西學傳統,把Science翻譯成“質學”(方以智用“質測”),還是按日本近世“蘭學”傳統,翻譯成“科學”。無論如何,震旦的課程在上海學子中普及了科學精神。輾轉相傳,遂在十多年后衍為北京《新青年》的“賽先生”。
震旦學生中,還有南洋公學轉來的另一批精英學生。當時,正逢南洋公學的學生鬧學潮,一大批學生退學。退學學生們一部分跟隨辭職的蔡元培,加入了新成立的愛國學社,另一部分學生則來到震旦學院,其中就有后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留美博士的胡敦復,此外還有民國元老于右任、邵力子。1905年,震旦學院學生又鬧起了學潮,結果就是復旦公學的誕生。20世紀的頭幾年,上海學生們動輒鬧學潮,這是有原因的。科舉制廢除前后,江南的讀書人忽然明白,未來將是英文、法文和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主宰的時代。于是,棄“四書五經”如敝屣,一等有錢留“西洋”(歐美),二等有錢留“東洋”(日本),三等有錢就到上海去,挑一個公立、私立的新學堂,算是“小出國”、“窮留學”。于是,上海傳教士和洋務人士冷冷清清辦了幾十年的新學校,忽然遇見了黃金時代。學生們對新學堂缺乏認識,對舊學問又恨又愛,心理浮躁。入學、退學,出國、回國成為時髦,一遇不滿,就鬧學潮。大量年輕的秀才、舉人拋棄舊學,涌到上海補習新學、西學。他們其實是清朝一次次失敗改革的受害者,在內地積累了很多不滿,遇到上海的學校里鼓勵獨立自主,租界里保障言論自由,就天不怕地不怕地爆發出來。
1905年震旦學院學潮中,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等帶領學生向掌管教學的法國耶穌會士抗議。這一次,學生們不是要脫離學校,而是要占領學校。學生們帶走了部分實驗設備、動植物標本和書籍等,趕走法國老師,宣稱自己要獨立舉辦震旦。按馬相伯后來的解釋,爭端的起因是震旦的“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我意見不合,遂脫離關系而另組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復旦”。當初情況比馬相伯的回憶要復雜得多。上海學生不愿意學法語,因為法語在洋場不及英語那樣有用。震旦學潮,并不起因于中、法民族之爭,而是英、法文何為“一外”的問題。馬相伯選了畢業于耶魯大學的李登輝來掌校,而后來的復旦公學改為商科為主,就是這個道理。剛剛接手校務的法國巴黎省耶穌會士一時難以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于是,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帶領學生,再度造反,脫離震旦。
學潮不是馬相伯發動的,甚至是有點沖著他去的。學生要學實用的英語,不愿學法文,更不用說拉丁文、歐洲哲學等古典學科。從經典轉為實用,并不是不可以商議,但與當初的震旦章程相違背。胡敦復、于右任、邵力子和擔任教務長的法國耶穌會士南從周就法文教學鬧翻后,帶著學生們來見馬相伯,要求校長脫離法國人,自辦震旦。馬相伯捐款給教會的時候,立下了不得反悔的死約,學校基金不可能收回。在震旦和學生的僵持之中,學校難以為繼,學生將要失學,馬相伯急得哭起來。胡敦復、于右任和邵力子是馬相伯最好的學生,他們要走,馬相伯只好奉陪。最后,校長站在了學生“造反派”一邊,把震旦留給法國耶穌會管理,自己另起爐灶。花甲之年的馬相伯拼了老命,再創辦一所大學。復旦公學的創辦,基本上也是馬相伯一個人的功勞。馬相伯在震旦與復旦之間吃了三夾板,最終卻難能可貴地再創了一個后來愈顯重要的大學。可惜的是,這一時期的馬相伯也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文章、文獻、日記和回憶文章,只在晚年一番云淡風輕的談話中提到。
從戊戌到辛亥,這一時期全國變法、立憲和革命思想界唯馬相伯“馬首是瞻”,他發表的觀點、談話、演講和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南北議和的時候,一位暗探在和馬相伯談話后,密報惜陰堂主人趙鳳昌,作為代表南方共和派人物主張的《辛亥政見》。馬相伯的中西學識確實比他人高明,在非常復雜的宗教問題上尤其如此。戊戌變法以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以不同方式把宗教信仰與政治制度聯系起來。康有為提出要建立“孔教”,譚嗣同把佛學、儒學和神學融合為“仁學”,章太炎則提出了一種以佛學唯識論為根底的“建立宗教論”。1907年,在這方面比較沒有見解的梁啟超在東京籌建政聞社,采用了馬相伯的“神我憲政說”作為社綱。目前我們還未見到“神我憲政說”的完整文本,只是通過章太炎的《駁神我憲政說》了解到這一學說的基本看法。按馬相伯理解,人性有本于動物性的“形我”,有本于精神性的“神我”。人類基于“神我”的結合,是有信仰、有精神的結合,馬相伯宣布:“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政聞社。”馬相伯用“形我”、“神我”的概念表達宗教信徒的社會理想:以“神”的名義組織人間社群團體,而不是蠅營狗茍搞黨派。按現代政黨理論來判斷,這種帶有宗教理想主義的政黨主張,比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和孫中山的偏頗之論公允得當一些。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體制建設中出現了紛繁的宗教問題。例如:國體層面的政教關系問題,倫理層面的信仰自由問題,不同宗教之間的宗教寬容問題,很復雜地糾纏在一起。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搞了尊孔、讀經、祭天等國家宗教活動;康有為執拗地籌建著孔教會,企圖一面借著孔教組織的影響來參政,一面以孔教思想抵御基督教信仰;不少維新人士延續戊戌變法時期移風易俗、教產興學的主張,打擊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間;更多的一般民眾則感覺到時代更替中的道德淪喪,不斷呼吁宗教信仰的回歸,“大聲疾呼曰:提倡宗教!提倡宗教!”中國古代思想家,對現代國家制度中的政教分離、信仰自由、宗教寬容原則并沒有系統的理論,而徐家匯出來的馬相伯在這方面正好有著長期思考。比較起來,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談宗教,馬相伯既理解中國古代傳統,也懂得世界近代思潮,最站得住腳。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布尊崇孔圣令;冬至日,袁世凱到天壇親自祭天。馬相伯當然知道康有為、夏曾佑在此背后鼓搗的孔教,并且識別出這是一種政教合一和國家宗教的做法,有違中華民國設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憲法精神。馬相伯堅持現代國家原則,在《一國元首應兼主祭主事否》中明確堅持信教自由,認為中國歷代固然是天子祭天,但信教自由的民國,元首與主祭不得一人相兼,因為:“元首者,乃五族五教人唯一元首,非一族一教人所得而入主出奴之。”比一般人更加機智的是,馬相伯采用了儒家傳統的君師相分原理來說明政教分離,“不惟不兼主祭,而君與師之職亦不相兼焉”。按儒家原理,師者,儒也。君主接受儒教,君主不得為導師。既不得為導師,便不能為教主,更不能為偶像崇拜的對象,儒家確實是這樣堅守的。馬相伯懂得儒家精髓,向康有為、袁世凱怪誕扭曲的孔教予以有力一擊。
馬相伯同一時期的文章有《信教自由》(1914)、《〈憲法草案〉大、二毛子問答錄》(1916)、《書〈請定儒教為國教〉后》(1916)、《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1916)、《代擬〈反對孔道請愿書〉五篇》(1916)、《憲法向界》(1916)、《〈約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信教自由》(1916),都是他抗議袁世凱、康有為等人的孔教、國教行為,為政教合一方案辯護的文章。1916年的馬相伯似乎真是急了,寫了那么多的抗議文章。我們看到,身為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馬相伯卻堅決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的主張。他的抗議態度,肯定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天主教教會的利益。但是,細看馬相伯的分析,他主張中華民國的儒、道、佛、回、耶,無分本土還是外來,“五教”都要與政治生活分離。“五教”平等,相互之間則容易建立寬容、平等、對話和共融的關系。這些主張,無疑更符合當時中國的宗教格局。
中華民國肯定不能建立一個國家宗教,但是一般人群的生活是否還需要宗教?世俗社會的倫理建設是否還要用信仰來支撐?宗教信仰在中國人的民眾社會中應該起怎樣的作用?20世紀初年的大部分中國思想家,都是急急忙忙地臨時考慮這些問題。馬相伯畢竟當過神父,他是從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畢業出來的神學博士,因而對此問題有著比較長期的思考,回答起來也是比較從容。也是在北京從政期間,他在《宗教在良心》(1914)、《宗教之關系》(1914)、《青年會開會演說詞》(1916)、《〈圣經〉和人群之關系》(1916)一系列演講和論文中闡釋了自己的主張。馬相伯和大家一樣,也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風氣概括為“風俗澆漓,紀綱廢弛,世道人心,大壞大壞!”作為一個神學家,他也和大家一樣,認為:“思從而補救之,以為非有宗教不可。”但是,當時提倡宗教的大偉人、大名士、大政客、大官僚都認為,“宗教者,為下等社會而提倡”,言下之意是精英人士并不需要宗教。把宗教看做社會控制的工具,用以管理愚夫愚婦的下等人,這種陳腐見解為馬相伯所不屑。馬相伯的說法很簡單,無論貧富、貴賤、智愚,“宗教在良心”,人人都可以從宗教信仰中獲得道德資源。這種說法被幾年以后冒起來的“新青年”們忽視了,他們用科學打擊宗教,進而發展出一種徹底的無神論。終不能淹沒的是,一百年后,“馬相伯問題”又似曾相識地歸來了。馬相伯留下的作品,以1914年到1916年在北京和袁世凱、康有為、夏曾佑爭論時所發表的宗教論述最有思想價值。同時代的思想家中,包括章太炎、嚴復、梁啟超、蔡元培等人,也數馬相伯的觀點最能明心見性地切入信仰本身,最為全面地涉及了宗教與中國近代社會的關系,而且相對正確。
對國共兩黨的政治家而言,馬相伯的生命意義有所不同。按他們的看法,馬相伯的價值不在于從事洋務,主張立憲,也不在于創建震旦、復旦,參與辛亥革命,更不在于他反對國教,提倡宗教,豎立良心,而在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在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挺身而出,發表了眾多的抗戰言論。本來,馬相伯“八十后厭聞時事,宗教書外,間閱科學各月刊”,不打算過問政治。但是,1931年九一八后,各方為黨派利益爭執不下,仍然置日本入侵于不顧。馬相伯只得又一次走出徐家匯,在上海的會場、劇院、電臺、學校拼命演講,奮筆揮毫,主題都是“還我河山”!奇怪!一個民族,因為陷入內戰,無法協商政治、發展經濟,不能建立現代國防,坐視領土淪喪,民眾逃亡,居然還需要一位耄耋老人出來大聲疾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本身是件很不人道的事情!1937年八一三以后,馬相伯以九八之年,跟隨西遷的洪流,經廣西桂林,輾轉到越南諒山的一個山洞里躲避。顛沛流離,馬相伯于1939年11月4日遽然去世,良可嘆也!當年的4月5日,是馬相伯的百歲誕辰,國民黨中央發來了褒獎令,內稱“民族之英,國家之瑞”,中共中央的賀電則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馬相伯生命的最后意義,就是讓一些立場不同的黨派群體有一個擱置爭議,想到國家、民族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片段時刻。
馬相伯的抗戰言論,1933年有馬相伯秘書徐景賢編輯的《國難言論集》,由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刊行;1936年又有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記的《一日一談》,由上海復興書局刊行。前書輯錄了馬相伯在上海、香港、天津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其中有演講、訪談、報道、題詞、回憶錄等等,不能完全算是馬相伯的親筆作品。后書是年輕人對馬相伯往事回憶的記錄,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核實,存在誤差。這兩部作品,均存于朱維錚主編、李天綱等編校的《馬相伯集》中,讀者可以自行參看,本書因篇幅限制,不加收入。另外,這次在《申報》等處找到一些確定屬于馬相伯自己撰寫的抗戰通電、文章,如與他人聯名發表的《聯合宣言甲》(1933)、《聯合宣言乙》(1933)、《聯合宣言丙》(1933)、《〈申報〉發行港版感言》(1938)、《精誠團結一致對外》(1938),則加以收入。
這一時期的馬相伯,受到救國會等組織年輕人的推崇,更加的被人“唯馬首是瞻”。因為支持抗戰政治家的活動,馬相伯與宋慶齡、楊杏佛、沈鈞儒、史良、王造時、鄒韜奮、章乃器等人有交誼,他甚至還是魯迅治喪委員會的成員。然而,這一時期和馬相伯在國家、民族和國學方面最為投契的,確是過去與他很是暌違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抗戰言論和馬相伯非常一致,他們在國家、民族、政體、黨派、國學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共識。為反對獨裁,停止黨治,政治協商,組織國民政府,挽救中華民族,兩人聯署了很多文件。章太炎去世之前在蘇州國學傳習所講學,馬相伯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在《申報》專門發文《贊許章太炎講學》(1935),稱贊他:“樸學鴻儒,當今碩德。優游世外,卜筑吳中。……值風雨如晦之秋,究乾坤演進之道。體仁以長,嘉會為群。網羅百家,鉆研六藝。綱紀禮本,冠冕人倫。……”這樣的贊語,挑剔如章太炎,也是應該滿意的。
現代學者追求著作等身,古人卻更加推崇述而不作,馬相伯基本上是個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孔子、蘇格拉底、朱熹、王陽明,大都是靠聚眾講學和身體力行留下自己的思想和學問。從此情景來看,馬相伯沒有留下很多專著,或許是可以理解。馬相伯辦了震旦、復旦,稱他為老師的后來都成了大師:梁啟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黃炎培……馬相伯似乎應該就是大師的大師了。問題在于,這些晚輩大師們雖然都愛他,敬他,利用他,實際上卻都沒有傳承馬相伯的學問。然而,思想是可以口傳的。清末的上海,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誰都可以發表政見,表達思想。政客要人、文豪大家、熱血青年中,總是馬相伯的演講有理有據,還最具表現魅力。梁啟超聽過馬相伯的演講,佩服地說他是“中國第一演說家”。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報紙曾經把兩個“反串”角色評論為:“馬相伯演講象唱戲,潘月樵唱戲象演講。”那是海派名角潘月樵喜歡在唱京戲時高喊革命口號,馬相伯的政治演講則繪聲繪色,詼諧有趣。幸虧馬相伯還能演講,晚年尤其如此,現今才留下了一些作品。
馬相伯不是一個強人,三十五歲以前的耶穌會士訓練,使得他養成了豁達、服從的個性;六十歲以前給李鴻章做幕僚的生涯,更發展了他敏銳、謹慎的個性。馬相伯的詼諧幽默,超然豁達,是作為神父的基本功而訓練出來的。天主教徒的身份,還有他曾經是耶穌會神父的經歷,讓他能夠透視中國問題,成為超然于黨派政治之外,為中國社會的長遠利益考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馬相伯絕無那種爭勇好斗的強辯性格,也沒有明顯的黨派色彩。馬相伯固然是一個未能盡職的神父,其實也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或者說他根本就是一個不斷被政客們利用的學問家。
歷史學家總是把鴉片戰爭看做中國文化由盛轉衰的關節點。一百年間,大師輩出。以年齡論,生于1840年的馬相伯正可以說是這鴉片戰爭后涌現的幾代偉人中的第一位大師。馬相伯出生以前的儒者,可能飽讀經書,舊學精湛,但是對西方文化終究隔膜;馬相伯逝世以后的學者,留學歐美,新學熟練,但是與中國文化傳統漸行漸遠。馬相伯和他的學生們,夾在古今中外當中,既熟悉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又剛剛經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這是他們的時代特權。他們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傳統,馬相伯,真的是大師中的大師。
本書選編,若無特別說明,均出自朱維錚主編、李天綱等編校的《馬相伯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收文稿中凡屬明顯錯字的,以〔〕內之字改正之;明顯脫字,以〈〉內之字補充之。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