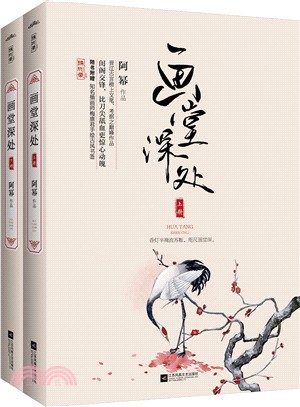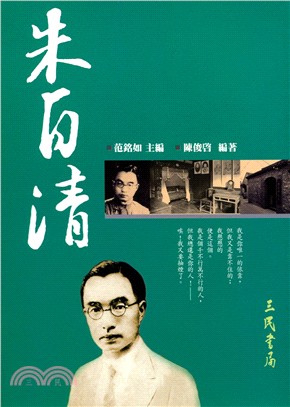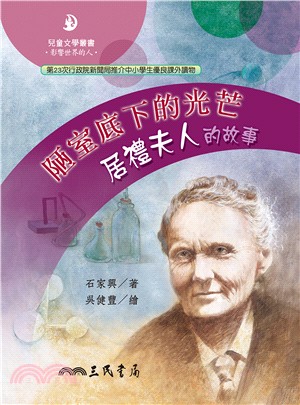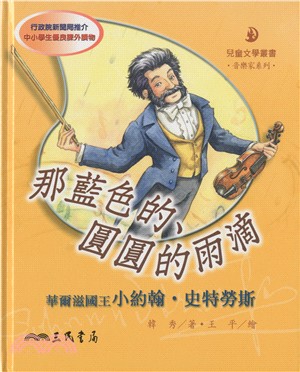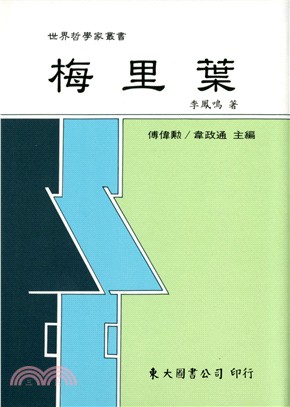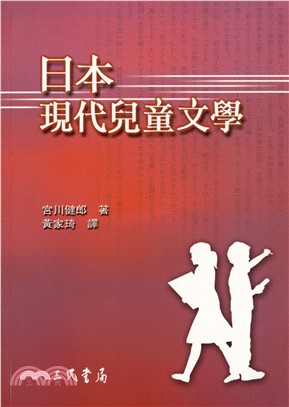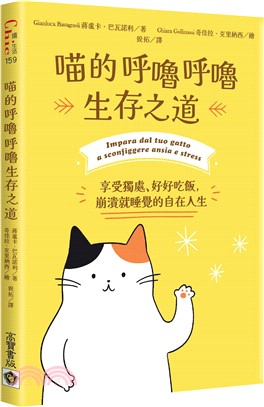商品簡介
★知名插畫師梅鹿君手繪書簽。
★始於深宅,不止於深宅。
丁家有女,小名團圓兒,生得如珠似玉,待字閨中。
城中首富蘇員外聞其美名,欲買作妾。丁氏夫婦愛其家財,欣然以應。
入得府中,錦繡繁華翩然而至。
象床珍簟,山障掩,玉琴橫。
正是天上神仙地,人間富貴場。
蘇員外喜其容貌,寵甚;正妻金氏素有賢名,於她亦頗多容讓,以致團圓兒無所畏憚,心生貪念,欲取金氏正室之位以代。
脂粉溫柔窟,暗流潮湧。日算千萬計,富貴險中求。
畫堂深處定風雲。
作者簡介
上海人士,商科畢業。生性散漫,愛看書、愛幻想,用心描摹一副副錦繡畫卷。
信奉格言:有夢想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要放棄。
名人/編輯推薦
脂粉溫柔窟,暗流潮湧。日算千萬計,富貴險中求。
目次
第二章 見嫡 爭風
第三章 舊情 滑胎
第四章 短見 蒙羞
第五章 訓妾 失寵
第六章 挑唆 入府
第七章 冷眼 搶子
第八章 傳言 動怒
第九章 遭辱 訓媳
第十章 軟禁 探子
第十一章 家訓 暗計
第十二章 遣婢 探主
第十三章 罵槐 暗算
第十四章 掌嘴 逐妾
第十五章 偏愛 斷離
第十六章 惡夫 諷嫗
第十七章 尋釁 生隙
第十八章 喪禮 離心
第十九章 反嘲 定計
第二十章 混戰 大牢
第二十一章 終章 團圓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口舌 逼婚
話說平安州富陽縣本是遠近聞名的魚米富貴鄉、脂粉溫柔窟,多有豪門大戶,城中有一條街,名為長安,乃是城中最為繁華的地段,中有一家喚作丁記油鋪的小鋪子。店主姓丁,大名一個瑞字,小名喚作大郎,四鄰八舍叫得慣了,這丁瑞的本名反倒無人提起了。這丁大郎十歲上父親亡故,寡母幼子倆守著一家油鋪過活,雖不敢稱富戶,倒也有些積蓄。到了二十歲上大郎便娶了城外一農戶的女兒王氏為妻,一連生了二子一女。長子叫作丁豐,今年剛交十八歲,已說定了東街上開米鋪的何家二女兒為妻,隔年就要成親的;幼子喚作丁富,才得十一二歲。這夫婦倆把那兩個兒子倒看得尋常,反把個十六歲的女兒當作掌上珍、心尖肉,這其中卻有個緣故。
卻是王氏懷著這女兒時,一夜夢見一輪圓月落入懷中,化作一面明鏡,照得人鬚髮皆明。王氏醒來自認為是個異端祥瑞,便叫醒丈夫,一五一十說了與他知道。那大郎也稱奇,也以為這孩子有些來歷,逢到有人來打油便誇耀一番,但凡有人奉承幾句,大郎夫婦一高興,油錢也少算幾文。倒是大郎的寡母朱大娘有些見識,因鏡子是易碎之物,心上便做個不祥之兆,只是見兒子媳婦格外高興,自己年老多病要在他們手上討飯吃的,故此不敢說,只忍在腹中,在媳婦王氏誇耀之時,還不免隨聲附和幾句。轉過數月,恰逢仲秋,王氏十月滿足,午時起便肚疼難忍,折騰了幾個時辰,生下一個女兒來。彼時恰是一輪皓月當空,便如一面大銀鏡一般,大郎為合了夢境,便不肯委屈女兒,特特提了兩斤肉,打了一壺酒請教私塾先生。那先生因著仲秋夜月色極好,月光照在地上如水銀瀉地一般,故起名叫作月華,又有個小名兒喚作團圓兒。
想大郎不過尋常相貌,王氏亦不過五官端正,偏這團圓兒也不知像了誰,生得面如桃花猶豔,眼似秋水還清,十分美貌。又有夢境為憑,大郎夫婦便將這女兒看得越發重了,雖是小戶之女,卻十分嬌慣,等閒不叫她出來,怕叫街上的潑皮瞧見了臊她;更不叫她做活,團圓兒長到一十六歲,自家雖開著油鋪子,連醬油同醋都分不清,女紅上也是有限,不過能繡幾塊手帕子罷了,便是自己的繡鞋都要依仗母親王氏。更有一樁,因王氏懷著團圓兒時得了那個夢,大郎便以為女兒非比尋常,又有時常走動的幾個媽媽見了,偏要湊趣,說團圓兒怕是月裡嫦娥來投胎的,奉承得大郎王氏格外得意,是以雖從團圓兒十二三歲起便有人來做媒,大郎同王氏夫婦兩個或是嫌人家底不厚,或是嫌家中妯娌多,或是嫌男方容貌尋常,挑挑揀揀總是不肯許人,一心只想往高枝上攀。可他們偏不想,自家不過開了個油鋪,略有幾個積蓄,上等人家哪裡肯要他們的女兒做媳婦。這一耽擱便到了十六歲。
朱大娘此時已年過六十,雖已發衰齒搖,見識倒是清楚,不免悄悄勸幾句說:“團圓兒,你又不是大家小姐,三奴六婢地使喚著,不會也使得。我們這種人家攀不得高門大戶的,和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娶媳婦不是供著瞧的,都要和你娘一般地操持,如今你這樣樁樁件件都不會,橫針不動、分隔號不拿的,將來到了婆家如何做人?”團圓兒還未說什麼,王氏恰巧進來取東西,聽見了這番話便惱了,把鼻子一哼,冷笑道:“娘如今也老糊塗了,你孫女兒這等容貌,便是給人家做少奶奶也是使得的,還怕沒人服侍?從來求親的人多了,不過是你兒子嫌門戶低,不肯罷了。若是肯,你老重外孫子都抱上了。”朱大娘見王氏聲口不好,也只得歎了口氣,自去做活。團圓兒因有娘撐腰,便也把祖母一番好意丟在了爪哇國中,依舊像個沒事人一般,每日裡只在自己房中玩那三十二張牙牌,端的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半點心也不操。
一轉眼便到了年關,眼瞅著過了年便要給丁豐娶妻,偏出了事。這一日,有個叫作張山的來打二兩麻油。這張山的母舅方青正做著這條街上的保正,張山自認為縣官不如現管,仗著方青的勢派,格外橫行些,結交了些混混,自己充作老大,到哪裡都是白吃白拿的。若有人不肯孝敬,輕則囂罵一場,重則砸東砸西。因此這一條街上無人不厭憎他,又不敢招惹他。
事有湊巧,恰好王氏的娘病了,大郎同王氏回娘家去,店裡只留丁豐一個人看店。丁豐素來厭他,又是少年人,做不來臉面功夫,灌好了油將瓶子往張山眼前一擱道:“五文錢。”那張山也不掏錢,只笑嘻嘻地道:“你妹子還沒許婆家吧?眼瞅著過年就十七了,也算老閨女了,一朵花再好,沒蜜蜂兒采也結不了果,倒不如就便宜了我,我情願給你們家做倒插門女婿。” 一面說著,一面將一雙賊眼往鋪面後面掛的布簾看去。原來這丁記油鋪乃是前店後家,這布簾子後就是住處。丁豐冷著臉道:“放你娘的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嘴臉,憑你也配!”張山也冷笑道:“都知道你爹媽吊著你妹子當寶賣呢,多少人來求親都不肯,只想著攀高枝。也得瞧人家高枝肯不肯。爺爺再告訴你一句話,女大不中留,保不齊哪天就白眉赤眼給你們弄個雜種出來。”說了往地上啐了口,拎起了油瓶就走,也不付油錢。若是大郎夫婦在,也就忍過這口氣去。偏生是丁豐守店,他是少年人,一時惱了就顧不得許多,打櫃檯後鑽出來,一手搭在張山肩上,又說:“你與我站住。”張山笑嘻嘻地說:“討油錢嗎?”說了從懷中摸出五文錢來作勢往丁豐手中放,手伸了一半,卻把銅錢往地上一扔,斜眼一笑道:“哎喲,掉了。”丁豐早就被他攪得惱火,見他這般無賴更動了真氣,握起拳頭就往張山臉上招呼。
張山猝不及防叫他打了一拳,手上一松,油瓶便掉了,碎了一地。那張山素來是打慣架的人,雖先吃了虧,倒是不慌,也還起手來,兩人就在店門前撕扯起來。丁豐雖有勇力,卻不敵張山久經戰陣的,不過數個回合就叫張山覷了個空,拉過膀子一扯,腳下一絆,摔在地上。張山縱身上去,照著丁豐劈頭蓋臉就打,直打了丁豐個頭臉紅腫、唇角帶血。雖有許多街坊來瞧,到底都怕這不講理的張山,不敢過來相勸。
張山還不肯放得丁豐過去,又在他臉上吐了幾口口水,口中罵罵咧咧:“什麼鳥人,也敢打你爺爺,爺爺不教訓教訓你,還當爺爺的拳頭是吃素的。今兒爺爺偏要瞧瞧你妹子是怎麼個樣兒。你那狗爹娘當寶似的收著,要真是個美人,爺爺委屈一下就受用了。”一行說一行又踢了他幾腳,說完了轉身就往櫃檯裡走。丁豐聽他的意思竟是要去臊皮團圓兒,慌了手腳,待他從地上爬起身來,那張山已伸手要去掀簾子。丁豐情急之下,顧不得許多,自櫃檯上抓起一物就朝張山頭上砸了下去。張山應聲倒地,面色慘白,頭上竟冒出血來。丁豐方才瞧見自己手上抓了一隻鐵秤砣。他到底才得十八歲,見自己打死了人,早嚇得慌了神,站在當場動彈不得。
街坊們眼見打死人了,一時都慌了,囉噪起來。卻說裡頭團圓兒同朱大娘也聽得明白,團圓兒是沒經過事的女孩兒,聽得那張山要進來先自慌了,跑去尋朱大娘討主意,祖孫倆還不曾說得幾句,就聽得丁豐打死了人。團圓兒險些暈過去,哭道:“都是我的緣故!”還是朱大娘穩得住,心上雖慌卻還不亂,先把丁富喊到跟前,叫他去喚大郎夫婦回來,自己壯起膽子挑起簾子走到外頭來。卻見張山在地上直挺挺厥著,頭上冒血,臉如白紙。她一個女流之輩,嚇得手腳都有些發軟,又瞧著孫兒唬得臉色發青,著實心疼,此時也顧不得他,先壯起膽子摸上前去,往張山鼻子下一探,還有些兒熱氣,心上一松,腿腳倒軟了,一下跌在地上,口中念了幾聲佛,勉強掙起身來,向著街坊求告:“列位街坊,那個人還不曾死,老婆子求各位行個善,請個郎中來,若是救活了這人,便是救了兩條人命,這也是積陰德的事。我老婆子在這裡給街坊磕頭了。”說了竟是跪下去磕了幾個頭。
因張山著實叫人厭,大郎夫婦平素為人又和善,便有人幫著去找郎中,也有人說:“丁婆子,你且放心,衙門倘是來了人,我們替你分述。是這潑皮尋事在先,也怪不得你孫兒許多。”這裡正鬧,張山的母舅方青得了耳報神的訊,他住得近,已然到了。
這方青年當四十來歲,生得面皮微黃、眉淡眼小,頜下幾縷細細鬍鬚。因他念過幾年書,腹內又奸猾,是以做了保正。卻說他分開人群走將進來,往地上一看,見那張山直挺挺躺著,頓時大哭,道:“我好苦命的姐姐,可憐你青春守寡只得這麼一個兒子,好容易要娶親了,偏教人打死了,你日後還去靠誰!”又罵:“好你個丁瑞,教唆你兒子打死我外甥,我若不教你父子償命,我白做了這個保正。”一邊罵一邊揪著丁豐就打。丁豐一是嚇得慌了,二是心虛理虧,一些兒不敢躲,也就挨了好多下。朱大娘見孫兒挨打,少不得過來勸說,只說張山未死,等郎中來了,只要能救人,多少銀子都肯。方青聽說,只朝著朱大娘臉上吐了口痰,罵道:“你個老虔婆,滿嘴屁話,頭都破了哪能不死?待我在你頭上敲了,看你不死。”又說:“我姐姐只得這麼一個兒子,全靠他養老送終。如今我也不同你說,只叫你兒子來說話,別跟個縮頭烏龜似的躲著。”丁豐見方青扯著朱大娘謾駡,他倒是個孝順孩子,過來拉開朱大娘道:“人是我打死的,我抵命便是,你休欺我祖母。”方青冷笑道:“哪有這許多廢話,你自然是要抵命的。”正說著,只聽地上傳來呻吟之聲,唬得眾人都住了嘴,往地上瞧去。
卻見張山慢慢坐了起來,捂著腦袋猶自罵道:“兀那賊兒子、鳥人、狗養的雜種,竟敢打你爺爺。爺爺不擰下你的賊頭來,爺爺就給你做兒子。”朱大娘喜不自勝,忙道:“保正老爺,令外甥可不還活著,真真老天保佑。”又念佛不迭。
方青心中暗罵張山該死不死,臉上卻做個關切寬厚模樣,轉了口風道:“既是未死,倒也好說,我也不是那等不講理之人。”又對丁豐說:“是你打的人,還不扶起來,要你祖母妹子去攙人嗎?”丁豐見張山未死也是不勝之喜,忙過去要扶張山。張山見是丁豐,自然惱怒,揮手便打。他是受傷之人,手上綿軟無力,打在丁豐身上也不覺什麼。丁豐將他扶在一邊椅上坐了,那張山口中依舊是囂罵不休。方青喝道:“你當我不知道嗎?平日裡你借著我的名兒生了多少事,我念著你年輕無知也不與你計較。如今鬧出大事來了,若不是這丁小哥手下留情,你死了不說,白連累人一條性命,你還不知道收斂嗎?”張山果然不敢再說。朱大娘同丁豐聽了,只認方青還是個好人,朱大娘忙上前笑道:“到底是保正老爺,說話就是公道。”
正說著,街坊請的郎中到了,替張山瞧了,雖是皮破血出,所幸不曾傷到骨頭,沒甚大事。上藥包紮了,又留下藥方來,這診金自是朱大娘拿了櫃上的錢付了。
方青一聲不吭,見郎中去了,方笑道:“公道不公道的,這都好說。只是我這外甥再不肖,你孫兒將他打成這般,若是告在官中,以我朝律法,凡鬥毆以物傷人,皮破血出者杖八十。我瞧你孫兒肉嫩骨軟,怕是挨不起八十下大杖。”朱大娘雖有些見識,聽了這番話,也慌了,忙道:“保正老爺高抬貴手,憑你要什麼,只要我們有的,都容易。”方青冷笑道:“休胡唚,莫非我還訛你不成!你既如此說,咱們還是見官的好。”說了拉起張山便走。
朱大娘自悔失言,正要上來攔,卻見門外跌跌撞撞奔進個人來,卻是丁大郎得了信,一路上先奔了回來,正聽得方青說話,先往丁豐臉上打了一掌,罵道:“我打死你這該殺頭的小畜生,你如何就打死了人,闖下這般禍事來,我看你如何收場!”朱大娘忙上來拉住,道:“人還沒死,有話好說。”丁大郎聽說,趁勢住手,偷眼覷見方青手上拉著的張山,滿臉血污,頭上包裹著白布,站在那裡,一雙眼賊溜溜轉著,瞧著也無大礙。來時一顆懸在嗓子眼的心頓時放下,忙堆砌起笑臉,拉著方青叫坐,又叫丁豐倒茶來。方青卻道:“你只叫我吃茶,在這裡坐也沒有坐,站也沒處站,也看得我太不堪了,莫非我當不得你賠罪嗎?”說了抬腳要走,大郎忙忙扯住,方青只是不依,張山也喊道:“你兒子險些把你爺爺打死,我只要見官。八十杖,管保將你兒子打死。”大郎知道自家兒子理虧,手腳都軟了,一時也沒了主意,只得往裡讓。方青半推半就,打發了張山先回去,自己跟著大郎走了進去。張山雖不情願,又怕方青,只得自去。
挑過布簾過去就是一極小的穿堂,不過數步便又是一門,門上擋著一塊打了補丁的藍布簾子。簾子雖舊,洗得甚是潔淨。大郎前頭挑起簾子來,便是天井了。他們幾人才一踏入院子,就見衣角閃動,一條纖影避入了房中。方青心知十有八九便是那團圓兒,故作不知,待在堂屋中坐了,又等大郎重新沏上茶來,方問道:“方才那小女子是誰?”大郎也知他明知故問,如今又有把柄在人手上,不敢再推託,只得過去叫團圓兒過來。
可憐團圓兒自幼被父母嬌寵,些兒事也未經,今兒出了這樣的大事,早哭得雙眼紅腫。此時見父親來叫,雖是害怕,也只得壯起膽子跟著大郎過來,見過了保正方青。方青久已聽說丁家油鋪的女兒美貌,今日一見,果然傳言非虛,又見團圓兒雲鬢微松、杏眼紅腫,分明是才哭過的模樣,格外可憐些,不由十分心動。見大郎要她跪下磕頭,忙起身攔道:“罷了,罷了。她一個女孩兒,今兒嚇得夠可憐了,莫要為難她。”大郎便叫團圓兒下去,又賠笑道:“保正老爺,今日全是我那不懂事的畜生不好,打傷了令甥,論理就該送官究辦,便是打死也是他活該。只是可憐他外祖母久病垂危,又最心疼他這個外孫,若是那小畜生有什麼,只怕我外母也活不成。還求保正老爺高抬貴手,饒他這次。憑他多少湯藥費都使得,就是賣了這鋪子,也不敢少分毫。”
方青道:“我那外甥也是個不曉事的,今日之事,我料定他也有不是,如今也休提這些,我是一方保正還訛你不成?”大郎聞聽,心中更是忐忑。因這方青平日那是黑眼珠子只瞧得見白銀子的人,今兒這般好說話,必有緣故。還未及盤算完,就聽方青說:“大郎,你也休看我是個保正,雖不入品,到底也算個官,只是我也命苦,今年三月裡,我那妻子一病竟沒了,連一兒半女也沒給我留下,我雖有些家底,我那甥兒張山又是個靠不住的,還不知我老來靠誰。”說著假惺惺歎息了幾聲。大郎不知他為何忽然訴苦,少不得相勸,方青方住了悲聲。大郎因見方青臉有淚痕,便親絞了手巾來請方青擦臉,方青站起身來接,口中稱謝,倒把大郎嚇一跳,連稱不敢。方青卻道:“你若依我一事,不獨今日你兒子傷人一事可揭過不提,往後這長安街上也無人敢為難與你。”大郎聽他這樣說,隱約猜到幾分,手腳都有些發軟,果然聽方青說:“請將令愛團圓兒許我為繼室,如此一來,你我是親戚,你是我岳父,張山還得喚你兒子一聲舅舅,舅舅打甥兒,豈不尋常?我也知道你一時難以決斷,我也不逼你,三日後我來聽信。你若是不應,我倒是沒什麼,你也知道我那外甥,從來都是沒轡頭的馬,他若是做出什麼來,我也攔不住。”說了抬腳便走。
卻說丁家屋子窄小,這番說話團圓兒聽得清楚明白,哪能不怕,如何不哭,捂著臉,過來忍羞含愧哭說:“爹爹,你真要把女兒許配那人,女兒只有一死。”大郎對女兒寵愛已慣,見她哭成這樣,不免心痛,又想起方青臨去的話,分明是說不答應這門親事,便有禍事,不由又氣又恨又怕又惱又急,心中只恨丁豐生事,氣衝衝奔到外頭,照著丁豐劈頭蓋臉打去。方才進門打他是做戲給方青瞧的,現在卻是真打。拿手打疼了,便四處找棍子。丁豐哪敢還手,被打得抱著頭四處竄,又叫救命。朱大娘見孫子挨打,要來攔,大郎怒道:“娘,你閃開,我今日定要打死這個畜生!他不是我兒子,竟是來尋仇要命的,今兒不是他死就是我死。”說了又扔了棍子去抓門閂。
卻在此時,王氏也趕了回來。他夫婦二人原是同時得信,哪得不歸心似箭。只是一來,王氏她娘病重,不敢驚嚇到她,怕出個好歹,只得推說店裡有事,讓大郎騎著騾子先回來;二來,王氏是纏足的,哪裡走得動遠路,騎著去的騾子叫大郎騎回來了,王氏只得另雇騾子,是以晚來了這許多時候。才到門前,就見丈夫舉了門閂要打兒子,眼見要出人命,也慌了,急叫:“大郎,你敢打死他,我便把這條命同你拼了。”大郎素來有些懼內,聽妻子厲聲大叫,不免手軟,心下還氣,將門閂杵在地上做個拐棍靠著,罵道:“你養的好兒子,要斷送我們全家。”
王氏冷笑道:“什麼是我養的兒子?兒子不是你的還能是誰的,難不成是我偷奸養漢生下的雜種?你要說他是雜種,你就一棍子打死他,再打死我,也算你是條好漢。”丁豐叫大郎打得又氣又愧,更聽王氏這般說,直恨不得方才被大郎打死才好,跪在地上大哭。朱大娘著實心疼,說:“你們說話也避著些人,難道真要逼死他你們才安樂。”說了,賭氣過來強拉了丁豐到外頭去。大郎早被王氏罵得沒了骨氣,扔了門閂蹲在一邊抹淚。王氏見他這樣,少不得過來勸幾句,又問詳細情形,大郎方一五一十說了。王氏聽了,急得罵道:“我說你是個糊塗蟲、沒主意的,白做個男人。被人幾句話就嚇成這樣,倒有臉打兒子。別說沒打死人,就是真打死了人,該抵命的也只有打死人的那個,哪有拉妹子去抵的道理!如今女孩子嚇成那樣你不知道勸,只知道逞威風。”說了扔下大郎不理,自己進去團圓兒房中。團圓兒果然早哭得聲哽氣噎,兩隻眼腫得核桃一般。王氏心疼得不得了,從大郎起,連同朱大娘、丁豐,並那張山、方青,統統罵過一遍,對著團圓兒又好言相勸,只說絕不把她許給方青等語。哄了半日,團圓兒方才慢慢止住哭聲,又說哭得久了心口疼,王氏忙不迭取了天王保心丸來,又燙了半盞黃酒,給團圓兒送藥,哄她睡下了方才回到自己房中。
此時天色已近黃昏,大郎早把店關了,也無心做飯,只在院子裡悶坐。王氏此時氣也略平,過來在大郎身邊坐了。她口頭說得雖硬,心上卻也沒甚大主意,如今看丈夫歎氣連連,也無話相勸。夫婦倆不過相對而坐、相顧無言罷了。大郎忽罵道:“都是你這婆娘不曉事!不過是得了個勞什子的夢,真當你女兒是要做皇后的嗎?這家求親不許,那家求親不好,若是早許了人,哪有今天的話!”說了氣呼呼站起身來,扔下王氏,自己摔門往街上去了。王氏待要追上去,只聽得團圓兒房中又傳來嚶嚶哭聲,想是沒睡著,把大郎的話聽了去。王氏此時也無心再勸,只是坐在院子裡歎息。
卻說大郎這賭氣一去竟是一夜未歸。王氏同大郎成親以來,從未分離過,他這賭氣一走,王氏不曾好睡。到了清早,雖是精神倦怠,因是靠著那油鋪入息吃飯的,少不得掙紮起來。也沒心思燒水,只用冷水洗了面,馬虎收拾了,就去開門。卻見丁豐已起來了,門早開了,自己愣愣坐在門前,兩眼鰥鰥地望著地。王氏不免心疼兒子,過來撫慰幾句。丁豐只是不作聲,王氏又問他早飯吃了沒有,丁豐也像聽不見一般。王氏心道:都是你惹的事,如今還來裝委屈。心火上來,便在丁豐身上掐了幾把。丁豐依舊垂著頭,王氏見他這樣,到底是做娘的,便再下不了手。又想起方青提親一事不知怎麼收場,大郎這一夜也不知道歇在哪裡,別是叫混帳老婆勾引去了,心中十分委屈擔憂,自己倒掉下淚來。
王氏這裡正抹淚,就聽得有個婦人笑道:“喲,丁家姐姐怎的哭了,莫不是昨兒做生意做賠了?”王氏忙收了淚,抬眼看去。店門口立著個三十來歲的婦人,面若銀盆、眼似彎月,未語先含笑,卻是這富陽縣有名的媒婆崔氏。
這崔氏為著團圓兒的親事也曾來過兩遭,親事雖沒說成,偏她生了一張巧嘴,善能吹捧誇耀,說出的話,字字都如真心,句句仿如體貼,同王氏倒是熟稔了。因王氏只有哥哥沒有姐妹,便把崔氏引為閨中知音。
王氏忙擦了淚,站起來道:“崔家妹子,今兒好早,要往哪裡去?”崔氏搖搖擺擺走將進來,笑道:“都是你妹子我貪財,應了蘇員外家金大奶奶的托,替蘇員外尋個美貌的女孩子做妾,已尋了四五個了,不是大奶奶不中意,便是蘇員外不喜歡,十分囉唆。若不是瞧在謝媒銀的分兒上,我早不耐煩了。”王氏讓座,又去倒茶。崔氏起身接了,又笑說:“前些日子,我替前門開綢緞莊的王員外的兒子說了門親,王員外甚是感激,除了謝媒銀子,額外送了我匹翠綠雲紋底水蓮花緞子,說是杭州那邊最時興的料子,我想著我們團圓兒穿肯定好看。只是今兒出來得匆忙,忘了帶,回去就打發我那小子給姐姐送來。不值什麼,給團圓兒做件衣裳穿。”王氏忙說:“妹子自己留著穿,她一個孩子哪用得著穿那麼好,上回你給的衣裳也才穿了沒幾次。”崔氏笑道:“那樣花俏的顏色,我穿著怕不成了老妖精,還是給團圓兒的好。說起來多日沒見,團圓兒想來出落得更好了。”王氏本是勉強撐著,聽了崔氏這話,再忍不住,眼圈兒一紅,道:“現如今,我倒只想她生得尋常些。”
這崔氏卻是為蘇員外家要買妾的事特意來的。原是蘇員外也聽聞了團圓兒美貌,私下同崔氏透了口風,要買團圓兒做妾,許下了二十兩銀子的重謝。這崔氏是個貪財的,便在蘇員外跟前誇下了口,拍著心口賭咒必將親事說成。前面那番說辭半真半假,不過是為著引出團圓兒來,此時見王氏這樣說,說不得便借著梯兒登上去,湊過身來細問。王氏本不欲說,禁不住崔氏巧舌,便一五一十把昨天的事說了,又哭道:“我那沒用的當家的,不敢和那方青辯駁,反怨我不肯早把團圓兒許人。我也是一點癡心,想著我就那麼一個女孩子,自幼捧珍珠一樣捧著,想她去個好人家,也不枉我心疼她一場。”崔氏聽了,也做個咬牙切齒的模樣說:“那方青論年紀,怕比王大哥都大,竟這般不要臉,打團圓兒的主意,也不怕遭雷劈。”王氏聽了這話,更是說到心裡去,哭得更甚。崔氏忙道:“好姐姐,你在店裡這樣哭,叫人瞧去了,還不知道說什麼呢。”說了反身吩咐丁豐好生看店,自己拉著王氏進去了。
到了裡頭,崔氏便道:“好姐姐,有句胡話,我若是說了,你可別惱。”王氏道:“你說吧,我也知道你心善,疼我們團圓兒。”崔氏道:“姐姐,你也知道蘇家的體面,雖不是侯門官宦,卻是個頂有錢的。富陽縣中一半兒鋪子是他家的,叫他聲蘇半城都不為過,便是他家的下人,吃穿用度都比我們這樣的人家強。”說了,斜眼去偷看王氏臉色。王氏正低了頭拭淚,並沒有不耐之色,崔氏心上便有了二三分把握,又說:“蘇員外今年才交三十歲,正當壯年,論相貌,瞧著不過二十多歲,十年前娶了清河縣金舉人家的三小姐做正房奶奶。姐姐,不是我誇這個大奶奶,到底是讀書人家的小姐,最是有教養,我幾次去蘇家,冷眼裡瞧著,她同犯錯的下人說話都是一臉和善,從不高聲,可不難得?更難得的是她為著自己不能生育,一力要替蘇員外討個姨娘,以備生養,真真賢良淑德。”王氏聽到這裡,抬頭看著崔氏,臉色頗有幾分活動。
崔氏又笑道:“好姐姐,你且想,大奶奶不能生養,這個新討的姨娘現如今聽著是給人做小,但凡她日後生個一兒半女的,也就能和大奶奶比肩了。等孩子大了,這偌大的家財還能跑到別人手裡不成?依我這個淺短見識,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長長遠遠的才是道理。”王氏只道:“你這話倒也有理。”
崔氏故意歎息道:“只是那大奶奶說了,蘇家雖不是詩書傳家,也是清白門第,新姨娘生的孩子將來是要繼承家業的,所以要找個美貌溫柔、家世清白的女孩子才好。只要女孩子好,多少彩禮都使得。我找了四五個女孩子,金氏都不甚中意,不是嫌長得不夠好,就是說舉止不溫柔沉靜。我心裡倒是想,若是我們團圓兒,這樣一個比大家閨秀還要秀氣的人品,金氏必定喜歡。姐姐,你別惱我,我不過那麼一想,一般人家的正頭夫婦都嫌委屈了我們團圓兒,何況是給人做小。”
王氏也不是蠢人,聽了崔氏這番話,知道崔氏想做這個媒,低頭想了許久,才道:“好妹子,往日我叫你空走了幾回,難得你不見惱,還真心疼我家團圓兒。我不是那不知好歹的人,你說的這番話,意思我也明白,若是給蘇員外做姨娘,果然是強過嫁給那方青。”
朱大娘見王氏心思活動,像是有答應的意思,急道:“崔娘子,你這話不通。”崔氏忙道:“朱大娘,我哪裡說得不通,您老指點。”朱大娘道:“崔娘子,你也是有見識的人,怎麼不知道小妾難做的道理?這奶奶不是奶奶,奴婢不是奴婢的,不是個身份,白受委屈。”
崔氏怕王氏聽了心裡活動,忙道:“朱大娘,論理這話不該我這小輩的說,只是您老才真糊塗了。若說小妾難做,也看什麼人家。蘇府這樣寬厚傳家的,哪裡會委屈人?不瞞您老說,那金氏雖是金舉人家的小姐,論出身也是庶出,生怕別人瞧低了,所以才格外地賢慧穩重,絲毫不肯動氣的。更何況,這回做姨娘可是正正當當花轎子抬去的,比之正室也差不了多少,更強過給那些撒野耍橫的粗人做填房。”說了又轉向王氏道:“我心裡只把姐姐當作親姐姐一般,所以才說這實話。那大奶奶人雖好,身子卻不牢靠,看這十來年都沒懷上孩子就知道了。如今日日吃藥呢,說句遭雷劈的話,若是團圓兒真嫁過去了,待她生下一兒半女的,將來扶正也是有的。”
王氏此時已經是千肯萬肯了,只顧慮著團圓兒被嬌縱慣了,自己主意又大,她若不肯也是枉然,因此略有猶疑。崔氏笑道:“姐姐也太心軟了,這婚姻大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別人插口的道理?待我們好言勸她,團圓兒若是個明理的,自然該遵從父母之命。”朱大娘原要再勸,聽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別人插口的道理”這句,又見王氏答應了,氣個仰倒,心道:反正是你們的女兒,你們愛往火坑裡推,我還死攔著不許不成?賭氣摔簾子出去了。
王氏見朱大娘出去了,便同崔氏一起到了團圓兒房中。團圓兒原也聽到了一句半句,她自幼為父母嬌寵,又有夢境做憑據,自以為來歷不小,將來非富則貴,如何甘願給人做小。又嫌蘇員外年紀大了些,先是咬了牙不許,怎奈崔氏鼓動如蓮巧舌,先將蘇府的富庶誇耀一遍,說得是天上有,人間少;又說蘇員外如何風流溫柔,大奶奶又是最賢德的,嫁過去了不怕沒一場大富貴可享;又說若是不應了蘇府,落在方青手上,才真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一番話軟硬兼施,直說得團圓兒低了頭。王氏又在一邊附和,竟將團圓兒說動了,點頭答應了。
兩人滿心歡喜地出來,坐一起又商議了會兒,定了崔氏去覆命,這裡王氏同大郎商議。兩人都有些怕蘇府知道了方青這一節,他們有錢人自然不想同無賴爭,倒不要了。一個為了女兒終身,一個為了謝媒銀子,索性商議定,先把方青一節瞞住不說,等蘇府那邊下了定,方青要鬧,蘇府這般有頭有臉的,自然不肯白叫人欺負了。
且不提王氏等到大郎回來如何商議,那大郎素來面活心軟,凡事都聽王氏的,又有愧在心,更架不住團圓兒自己應了,自是一口答應。朱大娘聽了,氣得啞口無言。卻說崔氏得了這裡的答覆,歡歡喜喜往蘇府去。
卻說蘇府上的大奶奶金氏正在房中看著小丫鬟們逗貓兒玩。她跟前的大丫鬟叫作春梅的進來回話,說是二門上的婆子來回,媒婆崔氏來了,正在西角門外等著呢。金氏按了按額角,似笑非笑地道:“這個崔娘子,腳頭倒是勤快,叫她進來吧。”春梅應了,回去吩咐了小丫鬟,小丫鬟又去說給婆子知道,那婆子便回來傳了崔氏進去。崔氏謝了,跟在婆子身後到了二門裡頭,就有小丫鬟來接,也只送到金氏的房前,自有金氏跟前的大丫鬟接了進去。雖則這崔氏來過兩次,少不得再叮囑些“回話仔細,不叫開口別說話”之類的,崔氏自是滿口答應。
崔氏見了金氏,先道了萬福。金氏笑道:“勞動崔娘子了,快給崔娘子看座。”小丫鬟搬了錦凳來,崔氏告了坐,方斜簽著身子坐了,又問金氏近日身子可好等語,金氏笑答了。崔氏方笑道:“奶奶,府上要買的姨娘,奴已尋了一個,論相貌是極好的,今年不過十六歲,家世也清白,是城中丁家油鋪的女孩子。”她話音才落,春梅先喲了一聲,道:“是她呀。”
金氏笑道:“把你伶俐的,偏你又知道。只是不該打斷崔娘子說話。崔娘子虧得來慣的,換了別人還當我們家沒規矩。”崔氏賠笑道:“大奶奶說哪裡話,不是奴奉承,別說是富陽縣,便是平安州,貴府也是數得著有體面有規矩的人家。”金氏笑道:“崔娘子休說這樣的話,我們不過借祖宗餘蔭,略有點子家底罷了,就這般妄自尊大起來,傳出去,可不叫人笑話。”又問:“你說的那個女孩子,家世倒清白,只不知人品如何,若是那等拈酸吃醋之人,我倒是沒什麼,只怕傳出去叫人恥笑。”
崔氏忙道:“大奶奶放心,借奴一個膽,奴也不敢哄奶奶。若是哄了奶奶,奶奶只管叫人把奴的腿打折了。”春梅聽她這樣說,便道:“奶奶,那女孩子有個小名兒,滿富陽縣可是沒人不知道的,叫作團圓兒,聽人說樣貌倒是很好的。”金氏把眉頭皺了下道:“怎麼一個女孩子的小名兒弄得人人知道,不太像話。”崔氏暗惱春梅多嘴,卻不敢惹她,只笑說:“大奶奶,這其中有個緣故。”說了便把團圓兒來歷說了遍,又道:“大奶奶,奴有個淺薄的見識,這團圓兒既有些來歷,保不定天意便是要她為奶奶您生一個了不得的兒子,將來金榜題名,皇帝要封誥父母,自然是先封生父嫡母,那副鳳冠霞帔還不是奶奶您的。”
金氏點頭歎道:“既是有些來歷的,倒還罷了。我也不指望做什麼誥命夫人,只求蘇家早有後代,便是我的造化了。不然,我也無顏見祖先于地下。”說了拿著綠羅帕子拭淚。跟前服侍的大丫鬟們少不得過來安慰幾句,崔氏也跟著相勸。金氏方收了淚,道:“夏荷,你領著崔娘子往前頭去見員外,員外說好,我這裡自然是喜歡的。”又對崔氏說:“我們員外要是答應了,少不得煩你回來,商議下定。”崔氏一聽這話,喜心翻倒,忙答應了聲就跟著夏荷去了。
蘇員外那邊本就有意,聽得崔氏來說,心花怒放,本欲一口答應,礙著大奶奶跟前得意的大丫鬟夏荷在,少不得推託幾句,只說“既有來歷,只怕不肯屈身做妾”等語,崔氏何等機靈,便一力擔保,又以子嗣來勸,蘇員外方才答應,又向夏荷道:“回去告訴你們奶奶,委屈她了。等晚間我再親自賠罪罷。”
金氏既知道蘇員外那邊答應了,便也歡歡喜喜叫丫鬟冬竹拿皇曆出來,要翻個好日子下定,又說要備幾色彩禮,要盤算給丁瑞夫婦多少銀子。崔氏只怕夜長夢多,便道:“大奶奶心善,這原是好,也是那團圓兒的福氣。只是如今不過是員外納個妾室以備生養,這樣隆重,一來也違了例;二來,也怕那團圓兒折福;三則,只怕人不說奶奶賢德,怕要說員外得新忘舊。”金氏聽了,卻說:“你說得也有理,只是我想著她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來做妾已經是委屈了,若是再鴉鵲不聞地過了門,我都不忍心,何況她父母。少不得張揚些,我也心安。”
崔氏心上怕橫生枝節,把到手的謝媒銀飛了,只求速速下定,笑道:“果然是團圓兒有福氣,奶奶這番話,奴倒有個見識,只是不敢說。”金氏道:“你只管說。”崔氏便道:“奶奶請想,貴府如今只是納妾,雖承奶奶好意,要下重禮,偏丁家是個沒錢的,傳揚開去,只怕叫人說丁氏夫婦是賣女兒。傷了丁氏夫婦臉面沒什麼,就是貴府臉上也不好看。”金氏聽了,笑道:“都說崔娘子會說話,果然不差,來來去去都是你的理,依你該當如何?”
崔氏笑道:“若依著妾,奶奶這就取幾色緞子,並一百兩銀子來。少了不是貴府的體面做派,多了也有不便。煩請管家同奴一起走一遭,取了八字來算一算,若是同員外、奶奶並無干犯,就算把這事定了。奶奶若是覺著委屈團圓兒,日後團圓兒在府上,奶奶多看承些也就是了。”
金氏聽了,沉吟片刻道:“這倒也罷了,我只是有些不忍。”說了令喚管家蘇貴進來,如此這般吩咐了,叫開庫房取緞子,又讓帳房支了一百兩銀子,便著管家隨著崔氏去即時排八字,若是沒甚干犯,便可下定。
蘇貴才要出門,金氏道:“回來!”蘇貴忙轉了回來:“奶奶還有什麼吩咐?”金氏端著茶盞,用蓋子撇了撇浮沫方說:“你開庫的時候,順手拿幾匹青緞來。眼瞅著要過年了,給丫鬟們一人做身衣裳。”蘇貴答應了,崔氏叫這一聲回來嚇得不輕,只當大奶奶要反悔,聽了這話方放了心。
到了晚間,蘇員外回房,見金氏已然卸了冶妝,只梳著一個慵妝髻,插著支點翠鑲紅玉的鳳頭簪子,穿著湘妃色竹葉紋底綢襖,領口微開,露著大紅抹胸,燭光下愈發豐腴豔麗,正依在床頭看書,看見丈夫進來也不起身相接。蘇員外因心中有愧,便自家過來,在大奶奶身邊坐了,摸了一摸她的手,說:“手這樣冷,想是穿得少了,我替你暖暖。”金氏由他握著手,依舊看書,蘇員外湊過身去,笑問:“瞧什麼好書呢?連我也不理。”金氏方笑道:“原來是相公來了,妾看入迷了,竟不知道。”又怪丫鬟們不早說,“都是我平日慣得她們連規矩也沒了。”
蘇員外笑道:“你這話說得好,論理你這幾個丫鬟是該管管,見我來了,連茶也不知道倒來。”金氏啐道:“你是客嗎,要喝茶自家不會說?”說了,扔開書下床去替蘇員外倒了茶來,道:“妾替那幾個蠢丫鬟賠罪罷,員外勿惱。”蘇員外一把抓住金氏的手,道:“好奶奶,我知道今兒你委屈了,為夫的這裡賠情,奶奶恕罪。”金氏似笑非笑,從鼻子裡輕哼了聲,道:“妾不敢說委屈。”
蘇員外見金氏這半含酸的模樣,被勾得心癢,雙手一用力,將金氏扯入懷中,兩人溫存一回。春梅、夏荷、秋月、冬竹等人見了,都悄悄退了出去,將門帶上。金氏便將同崔氏商定的計較一一說了,又說:“妾明日就讓人把東院收拾了,再指派幾個老成的媽媽丫鬟過去,日後就給團圓兒使喚。何時接人來,全憑相公的主意。”蘇員外又喜又愧,道:“我的好奶奶,辛苦你費心。”金氏嘴唇兒微微一彎,道:“這原也是妾的本分。只求相公日後不要得新忘舊的,妾也就心滿意足了。”蘇員外趕緊道:“哪裡來的話,我們夫婦十年,你也該知道我不是這種人。”說了,攬著金氏上床。丫鬟們早濃熏了繡被,展開了錦褥,兩人安寢。這一夜,蘇員外一面是心中有愧,一面是愛金氏婉轉嫵媚,自是努力報效,極盡恩愛纏綿。
不提蘇府這裡。卻說丁家那邊收了蘇府的定,自以為大事底定,把心都放下了,只等蘇府挑好了日子來抬人。王氏同大郎得了一夜好睡,到了清晨兩人起來開門,因團圓兒是就要出門子的,王氏心上不捨得,便到了團圓兒房裡,給女兒梳頭,陪著說話。
王氏按著團圓兒的手道:“我同你爹商議了。雖是做妾去,嫁妝倒也不能不準備齊整了。那府裡的下人們見慣了場面,都是些勢利的人,不能叫她們太小瞧了你。”團圓兒倒也有些主張的,告訴王氏:“娘,你那話很是,再有蘇家高門大戶的,雖然丫鬟婆子有許多,到底是他家的人,女兒是半路去的,自然同女兒不是一條心,明裡暗裡算計了女兒,女兒怕還不知道。所以女兒想著,他們家不是給了一百兩銀子嘛,請娘拿些出來,給女兒買個小丫鬟,叫女兒帶進去,女兒也算有個知心人。”說了,掉下淚來。
王氏自是滿口答應不迭,又教女兒,只要討得蘇員外歡心,占住他的寵愛便不怕了,若是再能生下一兒半女的,更不用愁了,怕是現在的正室大奶奶也要讓你個二三分。團圓兒聽了,羞紅了臉道:“娘,你說這些,好不羞人。”朱大娘聽了這些道理,卻是憂心忡忡,到了這個時候,也是一點法子也沒有,只得暗求菩薩保佑罷了。
不說大郎、王氏各自忙碌,卻說方青那邊也請了個媒婆,走過來要答覆。那媒婆也姓丁,論年紀比朱大娘還老,仗著資歷深,又是給保正老爺做媒,連眼角也不瞅大郎,開出口來便要商定過門的日子。大郎見方青狂妄成這樣,也自有氣,也因為女兒已經許了人了,蘇府又是有名的富戶,自然不怕他一個小小保正,便冷笑著對那媒婆說:“你回去告訴方青,他來說得晚了,我女兒已經許給蘇員外做二房奶奶了,叫他死了那條心罷。”
丁媒婆聽了,依言回去告訴了方青,其間不免添油加醋。方青見到口的天鵝肉飛了,又氣又恨,既羞且愧,又因連縣官何大人都羡慕蘇府富貴,折節下交,他也不敢招惹,一口氣便出在了丁豐身上,令張山出首去告丁豐,只說他鬥毆傷人。自己又在衙門的衙役身上撒下錢去,務必要叫丁豐多吃苦頭。
衙役們得了方青的銀子,便到丁家來捉人,偏巧大郎同王氏去人牙子那裡看小丫鬟了,店中只留朱大娘同丁豐守著。衙役們過來,二話不說,拿鐵鍊子往丁豐頸子上一套,說:“丁豐!你前兒打人的事犯了,跟爺走一遭吧。”說了,扯住就走,一路跌跌撞撞,又打又罵地將他拉到縣衙。待得大郎、王氏得了朱大娘求人捎的消息趕了來,丁豐已然認了打傷張山之事。到了此時,大郎夫婦也只能跪在地上求縣老爺法外開恩,念丁豐年幼,又情願多賠湯藥銀子。
何大人雖有些昏聵,倒是好說話,見王氏求得可憐,丁豐瞧著也是瘦弱的樣兒,便言道只要原告撤狀子,他也不追究。王氏無奈,又去央求原告張山。張山因得了方青的教唆,只咬了牙不許,又捏造出許多傷痛來。何大人只得依律判了下來:丁豐持械傷人,傷者皮破血出,著杖八十。丁豐立時叫衙役們拉了出去,按倒在地重打了八十板子。衙役得了方青的銀子,下手格外狠,可憐丁豐臀部以下並雙腿都被打得鮮血淋漓,連骨頭都露了出來,趴在地上昏死過去。大郎夫婦見了,心如刀絞,見兒子被打得不能走道,只得雇人用春凳抬了回去,又請郎中來瞧。
郎中過來瞧了,洗了傷口上了藥,招了大郎出去,在無人處告訴他,這一頓板子怕是傷到了一根極要緊的筋,縱是好了,以後怕也不能做丈夫了,說了留下藥方歎息著去了。大郎聽了如同五雷轟頂一般,半日回不過神來,到了夜裡,悄悄同王氏說了。王氏聽著這番話,一下沒轉過氣來,暈了過去,待得救醒,又痛又急,不敢大哭,怕叫丁豐知道,咬著被子哭了半宿,深恨方青張山,立定了心要報復,便同大郎商議要去蘇府,求他們個主意。
王氏自以為同蘇氏結了親,以蘇氏的體面,便是縣老爺也要給幾分面子,只要去求了蘇氏,必能出了這口惡氣。大郎卻勸道:“依我的意思倒是不要去,團圓兒人還沒過去,誰知道我們是誰,只怕門都進不去!更別說還有事去煩人,別讓團圓兒沒臉。”王氏冷笑道:“你若是個男人,能頂門立戶的,誰敢這樣欺負我們母子?如今你兒子都叫人打殘了,你依舊縮個王八脖子不出聲,我做娘的卻是要為他出這口氣。”說了賭氣要去,大郎素來面軟心活,也無可奈何。
王氏自己盤算了半夜,雖說女兒給了蘇員外做偏房,到底沒過門,自己一個女流去見蘇員外就多有不便。崔氏既說金氏是個慈善和軟的人,不如就去求她,女人家見面也好說話。計較定了,待天一明,王氏便起來梳洗,到底知道蘇府上下都是一雙富貴眼,便把年前做的一身出客的新衣裳從箱子裡拿了出來換上,買了幾色禮物,就往蘇府去。
到了蘇府前,就見門前有個皂衣家丁正掃地,忙上前道:“這位管家,勞煩通報聲,妾是府上新定的姨娘的娘,求見你們當家大奶奶。”那家丁手上不停,只用眼角掃了王氏一眼,見她身上一件簇新的青底富貴花樣布襖子,折痕猶在,下系著半新皂色裙,知道不過是尋常人家,便道:“什麼新姨娘,不曾聽過。我們大奶奶也是你要見就見的?”
王氏叫他這一句話堵得一時說不出話來,紅著臉道:“那就請蘇管家來見一見。”那家丁停了手,拄著掃帚冷笑道:“你老屬蛤蟆的吧,好大的口氣。一會子要見大奶奶,一會子要見管家,你倒不求著要見我們老爺。實話說給你知道,別說不知道你是誰,就算你真是新姨娘的娘,這大門也不是你配走的,一點子規矩也不懂。”說了,依舊掃地。王氏直氣得話也說不出來,手腳都有些抖,只得拎著東西回去。
到家的時候,油鋪子才開門,大郎正在收拾櫃檯,一抬頭見王氏回來了,臉色不甚好看,眼圈都紅了,便道:“蘇家大奶奶不肯嗎?”王氏一聽這話,把東西往櫃檯上一扔,哭道:“都是你個狗東西,一點子用也沒有,凡事都要我們娘們出頭。如今我叫人把臉皮都臊光了,你就有臉了!”說了賭氣回房,越想越氣,一會子罵方青、張山是殺千刀的畜生,做鬼也要找他們報仇;一會子罵大郎是沒種的王八,看著老婆兒子叫人欺負了也不敢作聲;一會子又說蘇家不過是仗著爺老子有錢,就來充大尾巴狼等語。
朱大娘實在聽不過去,便過來勸她,說團圓兒早晚都是蘇家的人,萬一這些話傳進蘇家人耳中,對團圓兒不好等語。王氏不聽還罷了,一聽朱大娘這話,便跳了起來,啐道:“憑我們團圓兒這樣的人才,什麼樣的人家配不上?將來只怕還能封誥命夫人,有八抬大轎給她坐,就非給他們蘇家做小?不過有幾個臭錢,也沒什麼了不起。”這話出了口,便想著要退親,只管打開箱子,取出給團圓兒做的衣裳並剩下的幾匹緞子。前次蘇家送來的一百兩銀子,因給團圓兒置辦嫁妝,又買了個小丫鬟子、給丁豐瞧了病,所剩無幾,她也不管,一併拿了,抱著便出了門。
朱大娘見媳婦這樣,急著追出去,又叫兒子:“大郎,攔著她!”大郎素來有些懼內,此時見王氏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哪裡敢上前,眼瞅著王氏一路出門。
王氏出了門,一路到了崔氏家。崔氏才梳洗畢,開了窗倒殘水,一眼瞅見王氏來了,陰沉著臉,懷裡抱了許多東西,不敢大意,忙開了門迎了出來,只當作沒瞧見她臉色,笑道:“姐姐怎麼來了?”王氏也不理她,自顧自進了門,將衣裳、緞子並散碎銀子都往桌上一放,道:“你去說給蘇家知道,我們寒門小戶,高攀不起他們高門大戶,請別處去娶姨娘罷。”崔氏聽了,心頭火起,眼先往桌上一掃,把鼻子哼了一聲道:“我說丁家姐姐,這是什麼?”說了伸出手來拎著衣裳抖一抖,又劃拉了一下散碎銀子,“這裡還剩多少銀子?你把人家送來的定都做成衣裳穿舊了,銀子也花完了,你老倒要退親?天下哪有這樣的理。”
王氏臉漲得通紅,“崔娘子,你也不要太仗勢了。這衣裳都是全新的,並沒有穿過;用去的銀子,我便是盤了店、賣了房也還你。”崔氏指著王氏道:“你倒是說說,我仗了誰的勢?當初定下親,你家也是千情萬願的,我拿刀子逼你們的不成!如今蘇府上新房都收拾好了,只等過兩天挑個黃道吉日要抬你女兒過門子的,你倒要退親。我問你,我在你店裡打了油,過兩天來還你,你收還是不收?”王氏雖然潑辣,口頭上不如崔氏,叫崔氏說得啞口無言,跌坐在凳子上道:“人是人,油是油,你別渾說。”
崔氏冷笑道:“我勸丁家姐姐你安分些。蘇府再慈善,也是有臉面的人家,你這般渾鬧,撕人的臉,他們一生氣,硬抬了團圓兒過去。他們心中有氣,說不得拿著團圓兒做規矩,你還不能說什麼;再則,你大兒子都傷成那樣了,能不能好都不知道呢,小兒子還小,有多少饑荒要打呢,你就要盤店賣房子爭臉面地胡鬧。依我說,團圓兒嫁過去,蘇家就是不給,團圓兒多少也還能幫襯著家裡些,你自己想清楚罷,別一顆心都叫糊塗油脂蒙了。”說了,將桌上東西胡亂一卷,往王氏懷裡一塞,把她推到門外,將門一閂,不再理她。
王氏來時的一團盛氣被崔氏這一番連唬帶嚇,早丟到了爪哇國,只得抱著東西回家。大郎同朱大娘正急,見王氏回來,方放了心,又問她去哪了,王氏不理,只管到了團圓兒房中,關了門同女兒說了許久話。中間只有團圓兒開門出來,叫新買的小丫鬟鈴兒去燒水來給奶奶洗臉。
朱大娘深知自己這個媳婦,眼皮子淺、心眼兒窄,不知會和團圓兒渾說些什麼,怕教壞了,本欲和團圓兒說下規矩,又知道自己這個孫女,自認為是有來歷的,自高自大慣了,很聽不進好話,只得暗自憂心。
卻說過了幾日,金氏便著管家蘇貴喊了崔氏去,商議抬人的日子。崔氏叫王氏那天一鬧,心裡也是懷恨。她只為把團圓兒說給蘇員外做妾,那是抬舉了團圓兒,若團圓兒得寵,丁家一門都有好處,便認作王氏恩將仇報。為著自己的謝媒銀,倒不至於攪黃了這門親,卻也不想叫王氏好過,見了金氏,問了好,又翻了皇曆,擇定了五日後抬人。商議既定,崔氏便道:“奶奶,妾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金氏便道:“崔娘子請說。”崔氏便道:“團圓兒那個大哥,同府上做了親之後,就以為自己是舅老爺了,為了幾文油錢,就將人的頭也打破了。”金氏聽了這話,歎道:“怎麼這樣強橫,那人傷得如何?”崔氏道:“回奶奶話,那人的舅舅是做保正的,也是知禮守法的人,將他告在了衙門裡,叫縣官老爺打了八十板子,如今趴著不能動,也怪可憐的。”
金氏歎道:“我們如今也算半個親戚了,竟不知道這事,倒是失禮。”說了吩咐喊管家進來,叫送一斤參苓補藥,並麝香虎骨等活血化瘀的恩物到丁家去,又說:“你說與丁家奶奶知道,是我知道晚了,並不是我眼中無人。郎中開出的藥,若是家中難以支持,只管到家裡的藥鋪上取,不要見外,都是親戚。”
崔氏點頭歎道:“奶奶果然是最聖明賢德的,只是團圓兒她娘是個不知道規矩沒進退的人,這會子同府上做了親,便自以為了不得了,逢人誇耀,說是蘇員外也得稱她一聲岳母。奶奶再這樣客氣,她更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說了,便偷眼覷看金氏臉色。
金氏只是略略皺眉,笑道:“崔娘子你且放心,丁家奶奶不過上了年紀,有些糊塗罷了。我也不是那等小肚雞腸的人。”說話間瞅了眼身旁的丫鬟,一個喚作秋月的因笑道:“若是崔娘子沒旁的事,就請回吧。我們奶奶這幾日身上不好,大夫吩咐要多歇歇,別勞累著。”崔氏只得應了,退了出去。
秋月見她走了,便笑道:“這崔娘子倒是刁猾,想是那丁家奶奶得罪她了,跑到這裡下眼藥呢,也太小瞧我們奶奶了。”金氏笑道:“叫她這一鬧,我倒真乏了。”秋月同冬竹忙過來扶著金氏往後頭去了。
卻說蘇貴依著金氏吩咐,將參苓、麝香、虎骨等物送到了丁家,並轉述了金氏的話。丁氏一門幾時見過這樣貴重的藥材,王氏本來一肚子的委屈,叫這一堆好東西並那番話說得煙消雲散,不住口地稱頌金氏賢德,又說要上門拜謝等語,又留蘇貴吃茶。蘇貴推道:“我們奶奶說了,親戚們互為照料是應該的,不敢當一個謝字。再過五日就是吉日,要迎姨娘過門的,府上必定事多,我家奶奶也等著我回話,不敢久留。”王氏同大郎千恩萬謝地將他送出了門,連團圓兒同朱大娘知道了也感欣慰,自此一家子歡歡喜喜數著日子等蘇府來接團圓兒過門。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