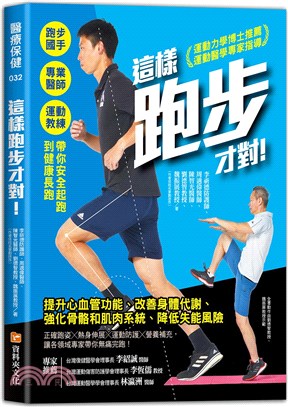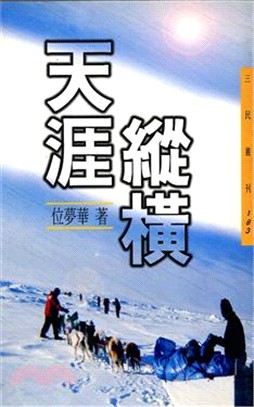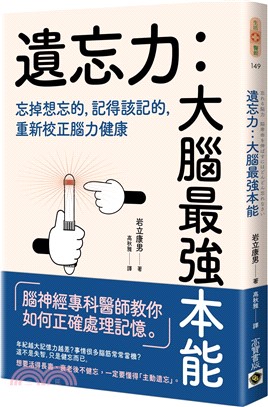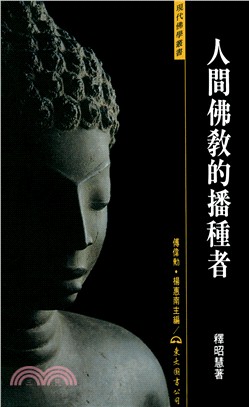蘭嶼之歌 清泉故事(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三毛譯作,大陸首度出版,三毛與心靈知己共同譜寫永恆的生活熱力、永遠自由的心。《蘭嶼之歌 清泉故事》收錄兩篇三毛推薦文,五十幅作者珍貴攝影作品。《蘭嶼之歌 清泉故事》是“一本有生命,有愛心,有無奈,有幽默,又寫得至情至性的好文”。
丁松青,天主教耶穌會神父,1945年生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1969年以修士身份來到臺灣蘭嶼,1976年被委派到清泉,從此與當地人結下不解之緣,也由此結識了畢生的摯友三毛。
本書即為他用文字、攝影記錄下的當地生活,分為“蘭嶼之歌”“清泉故事”兩個部分,精選50張珍貴照片,貫穿作者自蘭嶼至清泉的生活故事與心靈成長,記述了生活的點滴趣事,展現了洋溢著愛與自由的心靈,有歡樂有悲傷有溫暖有孤獨。三毛是作者的心靈知己,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擁有20年的深厚友誼,三毛以一貫的感性輕靈的文字將作者的故事譯出,字裡行間流露出生活的熱力以及對愛的體悟,能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
作者簡介
丁松青,一九四五年生於美國聖地牙哥,九歲時便立志做神父,十八歲進入耶穌會修道院修習。
一九六九年來到臺灣,兩年後在東南海岸的小島蘭嶼做見習修士,與雅美族人度過了難忘的一年。一九七六年夏,自菲律賓修習兩年神學後,再次回到臺灣,在新竹山區的清泉天主堂任職神父,融入泰雅族人的生活,至今仍生活在那裡。
一九七二年,與三毛在蘭嶼島上偶然相識,由此開始了兩人長達二十年的友誼。在三毛眼中,丁松青不僅是畢生的摯友,更“是詩人,是藝術家,是神父,是可愛之人,是天父的孩子”。
因著對愛與生命相似的心靈感悟,三毛以感性輕靈的文字翻譯了他所寫下的系列作品《蘭嶼之歌》《清泉故事》《刹那時光》,將愛與希望傳達給更多的人。
目次
【蘭嶼之歌】
有這麼一個人 三毛
和海一起
蘭嶼
伊莉莎白
禮物
海底世界
自由之歌
岩石
龍眼
拜拜
約瑪姑媽
卡吐西
颱風
金項鍊
海夜
裡帕沙的心願
晨光中的兒童
小雅由
田螺與小米
學校
遠足
被鬼抓到了
生活點滴
依凡瑞奴之夜
獵豬記
第一艘船
道多陀的世界
肥皂
巴陽
煩惱
打工
黑糖
木屋
迷人的村落
飛魚
捕魚
生命之歌
最後的戰爭
老顏
歲月人生
耕耘與收穫
船的日子
後記
【清泉故事】
清泉之旅 三毛
和山一起
前言
山地世界
風雨故人
半個婚禮
河裡的孩子
十隻小雞
運動會
中興之歌
大丁神父訪清泉
耶誕節的淚水
一場大火
演出問題
兩個山地人
根
給庫諾西的十字架
到更高的山上去
山青會
四種人生
木材工廠
動物的故事
山地舞
安全之旅
鴨毛
施與受
吃飛鼠肉
阿秋的世界
我的姑丈
蛇的故事
山修士
耶誕馬槽
書摘/試閱
有這麼一個人
——記丁松青神父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架小飛機在著陸的時候是順風落地的。當然我關在機艙裡並不可能曉得。
我們好似要吹到海水裡去了,飛機才悠然止住。
地面上的人迎了過來,笑著對機師說:“今天怎麼如此降落呢?”機師說:“天氣好得那個樣子,沒有危險的!”
一群人上來幫忙下行李,我提出了簡單的小背包,對著機場檢查官員笑了笑。這兒的人與本島臺灣的,在態度上便是不同,那份從容謙和給人的感覺便是舒坦。
機場邊的辦公室是水泥的長方房子,立在海邊全綠的草坪上,乍見這片景色和人,那份除了安寧之外的寂靜,夾著海水、青草地還有機油的味道,絲絲刻骨,這份巨大的震撼卻是面對一個全綠的島嶼時所帶給我的。
那是十一年前蘭嶼的一個夏日。
在赴蘭嶼之前,我已跑過了大半個地球,可是這兒不同,這兒的荒美尚是一片處女地,大地的本身沒有太多的人去踐踏它,它的風貌也就寂然。
女友子卿與我搭上一輛鐵牛車跑到預定的蘭嶼別館去,在那個島上唯一的旅社裡安置了簡單的行李。
放下了衣物,急著跑出門去,滿腔的歡喜和青春,經過花蓮、台東一路的旅行,在初抵這片土地時已到了頂峰,恨不能將自己潑了出去,化做大洪水,浸透這個陌生地,將它溶進生命還是覺得不夠。那時候的我,是怎麼樣地年輕啊!
景色的美麗事實上是拿它無可奈何的,即使全身所有的心懷意念全都張開了迎接它,而不長期生活在它裡面,不做些日常的瑣事,不跟天地在個人的起居作息上融合一體,那麼所謂遊客似的看山看景,於我還是空洞。
看了一會兒蘭嶼的山海,我便覺得有些無聊,禁不住想去跟當地的居民做做朋友了。
遠遠的山坡上立著一些涼亭,山坡與地面接近的地方有著本地人低矮的住宅,沿著上坡一條小徑的最頂端一座天主教堂在一片綠色中十分優美地站著。
子卿和我不約而同地指著那個教堂,說走便走,沿著在當時尚有小紫花開滿的斜坡爬上去。
那時候去島上的陌生人有限,我們走路的時候,身邊很快引來了一大群小孩子,我隨身的布包裡放滿了台東買去的糖果和吉祥牌香煙。本是不懷好意,預備拿來交換蘭嶼手刻小木船用的。結果要糖的孩子太熱烈,我又是個不忍拒絕孩子的軟手人,一路上教堂,一路努力分辨孩子的小臉,給過的絕不再給重複,這麼爬到半路,糖果光了,孩子們也散了。
教堂的面前一個泥巴地的小廣場,淙淙的山泉用管子引了下來,不間斷地流著。一個婦人蹲在那兒洗兩個赤身露體的小孩。四周寂靜無聲,也看不到其他的人。
女友子卿是世上最合適的遊伴,她很少跟我黏在一起,是個不多話又自有主張的好朋友。當我低頭去喝泉水,跟那婦人說話時,子卿已經自去四處行走了。
我試著抱起那個小女孩,親親她美麗的面頰,她的母親便說:“給你好不好,你給我帶去臺灣,要不要?”
我聽了嚇了一跳,微笑著趕快放下孩子,跑到教堂的大門邊去。
教堂的大門沒有完全關嚴,主人不在,不敢貿然,趴在門縫裡偷看內部的情形,這一張望喜得愣了過去。
內部的聖堂牆上大幅的壁畫,畫著蘭嶼服裝的同胞,戴著他們狀如鍋蓋似的大帽子,手中捧著土地裡生長的收穫,活活潑潑地在向神獻上感恩。這麼一座神民交融的美圖,竟然藏在如此一個小島上,又是誰的手筆呢?
可惜門縫裡張望所見的角度總覺不夠,我又是個酷愛美術的人,在這種理由下,便想扭開教堂松松拴著的鎖,私自跑進去看個夠。
便在動手的時候突然覺得身後有人,我尚喊了一聲:“阿卿,我們想法子進去看畫!”猛一回頭發覺身後站著的是一個陌生的棕發青年。我因自己正在闖教堂,巧被捉個正著,立即飛紅了臉,一句想也沒有想的話脫口而出:“您是義大利神父嗎?”
這完全是大窘之下掩飾自己不良行為的話語。
眼前的青年不算太高的個子,頭髮剪得規規矩矩,牙齒極整齊,眼神溫柔友善,算得上英俊,一身舒適清潔的舊衣,腳上一雙涼鞋,很羞澀,極純淨,脖上一條粗鏈子掛著一個十字架,沒有言語,只是站在我面前。
他不說什麼,可是透露的身體語言便明白告訴了我,這個青年,是有光輝,有信仰的,並且不是個義大利人。剛才那句問話真是莫名其妙。
這一回,是他開了門,謙卑和氣又安詳地將子卿與我引進了聖堂。
教堂在廣場的正面,左廂另有一個小房子,裡面放著一個醫藥櫃,另外擠著一架老風琴,我試按了幾個音,有些琴鍵下去了便不肯再跳起來,半啞的。
房間裡堆著一遝一遝的兒童畫,用色取景鮮明活潑,想來是島上的孩子們塗來送給這位神父的禮物。
神父愛畫,不必說也看得明白,他自己也畫。
教堂的右側也是一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桌子,好似尚有木板床。再進去的一小間,一個如同爐灶的黑洞,旁邊一堆柴火,食櫃裡幾隻鍋碗,顯眼的兩隻蛋孤零零地靠著,想來便是廚房了。
那位青年說他姓丁,是天主教耶穌會的修士,在島上生活已經一年了,美國人。
我不會稱呼一位修士,隨他怎麼說,仍是喚他丁神父。
我們交談的時候,四周湧進來一大群好奇而友善的本地青年和孩子,說話的時候,修士的手便撫著身邊小孩子的頭,自自然然地流露出那份家族式的親情。
參觀完畢,覺得不能再打擾這位陌生人,便告辭下山去了。
蘭嶼之旅的第一位交談者,便是後來結緣的丁松青神父。
我以為那種美麗的木刻小舟是有希望不花錢,只用香煙便可與當地同胞交換來的。這是傳聞的失據,也是自己的如意算盤打得太不忠厚。
一路上蘭嶼同胞的確要去了我的吉祥牌香煙,而小船卻不肯換給我。那時候在別館的旁邊有一家商店,店內的雜貨自然是臺灣運去的,可是他們也兼賣泥塑的小人,還有那一艘艘美麗的小木船。我一口氣買下了六條。
第一日到蘭嶼,沒有去遊山玩水,心思就在那批小木船上,放在旅社床鋪上左看右看,細數划船的小人兒一共有幾個,當我發覺子卿船中刻的人居然有側面孔的,而我的並沒有,便吵著要跟她交換,兩人忙來忙去,旅社裡已叫我們下樓吃飯去了。
那時候的蘭嶼遊客稀少,食堂中為我們開出來的居然是大盤的四菜一湯。
面對如此豐盛的食物,子卿與我卻很不安,覺得菜蔬得來不易,吃不完浪費了不好。
一時裡我有了主張,請子卿管桌子趕蒼蠅,自己一口氣奔上山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進了教堂便喊:“丁神父,山下的菜吃不完,請您一同去吃飯呀!”
所謂晚飯,不過是下午四點半,實在太早了。
丁神父聽了我的話,淡淡地回絕了,他的神態很親切也很自然,並沒有傷害到我。
當時的我,凡事積極,做人也太直率,已經被人婉謝了,居然不肯甘休,又說:“那麼將菜搬上來幫忙吃好嗎?”
這真是強人所難,丁神父慌忙道謝再拒,我已掉頭往山下又跑了去。回想起來,那時的體力好似再也用不盡的。
子卿真是好女孩,她的菜飯也不肯吃了,自己撥出一點點菜來,其他的全都要給神父。
這一回再上山,我找到了近路,崎嶇難走,可是快捷,左手中端的一條紅燒魚在盤子裡滑來滑去,很不安分。
送菜去的那個黃昏,神父的房內又擠滿了小孩子,盤子剛剛放下來,那些孩子沉默的大眼睛便牢牢盯住了菜。
神父很安靜地謝了我,用手拿起那條魚,將魚頭一折,很自然地交給了他身邊的孩子,然後一段一塊的魚肉都公平地分散了,眼看盤子內只有了湯汁。
“你也吃一些嘛!”我有些著急,對神父輕輕地說。
他只是微笑著,摸摸孩子的頭,叫他們去廣場外面玩。
那時候我們由台東上飛機赴蘭嶼,父親的朋友,當時在台東任職土地銀行的王毓麟伯伯,給我們備了好多水果餅乾帶了上路。那些水果,到了蘭嶼,子卿與我又捨不得獨吃,覺得神父必定許久沒有葡萄吃了,因此也跟菜一同搬了去教堂。
吃好了菜的孩子們,看見葡萄,又湧到神父身邊來。
“神父,請你自己留下一些,你也要吃的!”我又急了。
葡萄又被一顆一顆放進了孩子的口裡去。那只溫柔的手怎麼不知還有自己呢。
那一個夜晚,我坐在別館面前的大海邊,別館的發電機是那兒唯一亮出燈火的地方,身邊不時有大人和小孩跑上來伸手討糖果,我的口袋裡裝滿了在島上雜貨店中新買的水果糖,有人來討,便交換條件,他們教我一句當地話,便給一顆糖,不是白送的。
一直坐到燈火全熄,我卻無法欣賞海濤雄壯的聲音,在夏日拂面的夜風裡,心裡想的只是教堂內那個食櫃,空空的架子上,除了兩個蛋之外,什麼也沒有的食櫃。
這些同胞伸手不斷地向人討東西,那修士孩子似純潔的靈魂,又怎麼弄得過他們。
聽說蘭嶼的山裡有蘭花和烏木,子卿與我起了個早,東南西北地亂走,看見了島上的居民,便跑上去鍋蓋鍋蓋地打招呼微笑,不然就是跟著人家後面走,看看別人要到哪裡去,因為我們事實上也沒有目的。
人說蘭花早已被採光了,山中去玩玩倒是好的。
於是我們又沿著小徑往上爬,島上的居民和氣,低矮的房舍歡迎我們進去坐坐,我當真不客氣,一家一家給爬進去坐坐,大家對著含笑,略略接受居民送上來的食物。還一同聽了收音機,我漸漸地開始喜歡這些雅美族的同胞。
經過那座教堂的時候,又見第一日的那位修士在家,子卿與我上去道日安,說了一些蘭嶼的話題,那時已近正午了,不時有些居民來找修士,是來擦皮膚病藥膏的。
修士忙完了,突然問子卿和我,是否願意在教堂內同吃一頓中飯,那時候他的兩位雅美族朋友也在場,其中一位元青年如果記憶沒有錯誤,應該叫王棉羊。
其實我們在蘭嶼別館中所付的費用是包括伙食的,不吃也是付了,可是聽見這位修士要請我們吃飯,居然一口便答應下來,也不知道客氣,更忘了不如先去旅館中搬了菜上來吃,不是省了別人張羅。
我們對修士說,他請客可以,由子卿和我來煮飯,說著便跑進了廚房。子卿和我進了那個灶間,修士卻失蹤了,再也不見人跡。
柴火煮飯不很容易,子卿和我被煙熏得眼睛赤紅的,那些米卻是不肯熟,火怎麼扇也燒不旺,弄得狼狽又緊張。
食櫃中找來翻去還是兩隻蛋,我急了,拿水摻進去用力打泡泡,希望做出來的炒蛋能夠看上去多一點。
做飯的過程裡我一直跑出去張望,不知請人吃飯的那個主人為什麼不再出現了。
等了很久很久,才見修士由山下跑著回來,他一看見我,臉也紅了,將雙手一直放在背後跟我說話,他的手裡藏著罐頭。
看見他為了我們去添菜,我亦大窘,深悔自己的不懂事,弄得別人簡單的生活秩序大亂,又令人無端破費,這都是我所不願的。
煮了三個人量的米飯,進來的人卻很多,修士與雅美族的同胞看得出情同手足,也不必留飯,那些態度極為友善而略略羞澀的青年們便與我們同桌,大家都吃得很少,修士自己可以說沒有吃什麼。這份特別的飯菜和殷勤,使我至今感謝在心,對於這位異國青年默默的愛心,對雅美族人及對子卿和我個人的付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住在蘭嶼的第三日,又結識了同住一個旅社的兩位外國青年,他們帶了衝浪板,說是要坐車去島另一端的海灘,問我要不要同去。
我當日的計畫是在島上慢慢地看民舍和別村的百姓,因為喜歡走長遠的路,便謝絕了他們。
子卿和我早晨出門的時候,在雜貨店的門外碰到了三個穿著灰色制服,頭髮剃光的青年,他們問我們哪裡去,我們說沿著島上唯一的路走,想走一整天呢!
經過教堂山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抬頭看,看見那位修士和雅美青年王棉羊遠遠地站著,便揮著雙手,神父再見神父早安地亂喊,喊完了發覺三個灰衣的光頭青年還在等著我們,於是自然而然地與這些碰到的人一起上路去了。
路邊的芒草在有些地方長得比人還高,天氣卻已忘了是不是炎熱,在荒野裡走著談著,發覺那三個新朋友對臺北相當熟,圓環那兒的情形說來頭頭是道,談吐卻是有禮而活潑的。
“你們猜我們是誰?”其中一個突然問子卿和我。
我看著他們的制服,便說:“我猜——你們是工兵。”
他們聽了大笑起來,好似我說了一個笑話,神情非常愉快,彼此看來看去,有一個笑得彎了腰,還故意跌到草堆上去。
“工兵?是兵的工哦!”說完又笑起來。
這時我突然知道他們是誰了,一時裡天地突然變成好大,四周的笑聲也聽不清楚了。
“你們是管訓來的,對不對?”我喊了起來,又加了一句,“活該!”
“你們現在怕了吧?”其中的一個說,他的態度卻是很好的,虛張聲勢之外又有些說不出的什麼東西隱在口氣裡。
子卿與我很快地交換了一下眼神,不由得笑起來了。
“怎麼會怕呢!你們來受訓,期滿了重新做人,大家都是有缺點的,我們也不算什麼好人。”
說完這話他們沉默了,一個突然說:“當初,我們是沒有人瞭解,才因為恨,做下了許多明知不對的事情——”
“算囉!你們流氓做到甲級,總算聰明人,不被瞭解也不能惡到去欺侮善良的人呀!還要找理由嗎?”我說。
“小姐,你說話有學問,我想請問你在臺北做什麼的?”
“我教書。”
“你知道,我這一生就只有一個小學老師真心愛過我,所以我過去什麼人都給他打,只有做老師的人,絕對不打,老師好嘢!”
子卿是個廣告設計專家,她的才能在那一方面的確突出,可是我們在那種時候,那個環境裡,只有兩個女子對著三個管訓的人,因此將她的職業也改成了老師。他們便稱呼我們老師。
那時候我才回想起來,為什麼我們出發的時候,山上的丁神父一直不斷地張望,距離那麼遠,他的不放心,在這時方才明白過來了。
四周荒寂無人,我沒有絲毫抗拒管訓人的懼怕心理,因為自己慢慢與他們做了朋友。當然我心裡仍是防著一點的,至於如何防,也不曉得。
走著走著,那些雅美族的村落零零落落地來了,我想買把漂亮的小刀,進入政府給當地居民蓋的水泥房舍中去問,那三個人也熱心地替我選,雅美族同胞好耐性地拿出三把來給我挑了又挑。
一回頭,修士的好朋友王棉羊就站在不遠的地方,我看他來了,非常歡喜,跑上去問他:“你怎麼來了?上哪裡去?”
他只是微笑,也不說什麼。我們買了一把小刀,又往前走,那個王棉羊總也在五十公尺之外,我們停他也停,我們開步走,他也走。前面五個人說得起勁,後面的王棉羊也不上來,固執而沉默地追隨著。
那一日一直走到黃昏,子卿在路上碰到另一個放羊的管訓人,他手裡好幾個烏木圖章要賣出來,子卿想要一對同樣大小的送給她父親,慢慢走細細挑,那個人有生意做,羊群也不管了,跟到太陽快西沉了,才賺到我們幾塊錢,拿了錢,這才哇哇大叫,說他的羊群還丟在老遠,飛也似的跑了。
窄窄的路上突然來了牛群,就對著我們沒處可躲的正面,帶著飛揚的沙塵奔騰而來。牛群的後面叱喝著趕牛的是一個阿兵哥,他也管不住狂奔的牛。
眼看長角大牛要踩死我們了,子卿和我叫著便逃,那個跟了我們一整天的雅美青年王棉羊匆匆趕上來,我們擠得跌到茅草叢中去,他拿身體去擋我們兩個嚇得臉都黃了的人。
王棉羊沉默而固執地保護了我們長長的路,本是不放心其他的人和事,結果卻在牛群的驚嚇裡救了我們一次。
他和那位修士是親愛的朋友。
我們抵達的不數日之後,一個大學的暑期醫療服務隊也乘船來了蘭嶼,這對平日寂靜慣了的島嶼來說是一件大事,接待的軍方舉行晚會招待這些遠客,表演的自然是他們要來醫療的雅美同胞。
那個中午,據說颱風已快來了,可是正午的晴空和海洋完全看不出風雨欲來的絲毫跡象。
教堂的廣場前有修士集合起來的雅美同胞為著晚會在預習表演,蘭嶼的年輕人唱“國語”流行曲,女人們,大半高年的了,說是將跳頭髮舞。
我不喜歡看預習,要看正場,修士說到了晚會時間他們經過蘭嶼別館赴軍營大禮堂的路上,順便來接子卿與我。
夜間的風勢突然大了,島上的小路完全沒有燈光,漆黑風高的夜裡,一串串雅美族同胞,跟著修士高舉帶路的手電筒嘻嘻哈哈地走著,那是島上的大日子。
那一束在完全無星無月之下的黑暗裡舉著照亮人群的微光,就有上百的雅美族人追隨著——他們愛他,那個叫做丁松青的人。
晚會是給醫療服務隊的人預備的,我們不能進去,站在禮堂外面的窗戶外向裡張望,當然,表演的人就進去了。
我趁著大家進場時,一擠跑了進去,一直走到一個靠椅子坐著的軍官旁邊,蹲在他膝下,坦承自己不是來賓,請求給我進去看。
那位長官非常客氣,立刻站起來給子卿與我安排了座位,又捧來了香煙、瓜子和糖果。我的要求並沒有那麼多,堅持盤膝坐在水泥地上,那時表演前的歡迎詞開始,窗外大雨傾盆而下,風雨的聲音被擴音機所掩蓋。
窗外爬滿了進不來的人,丁修士沒有要求進來。
我無法安然看表演,又半彎著身子去對那位長官說,裡面的場地尚空,外面淋雨走遠路來的同胞可否放進來。
這位長官實在好耐性,忙說:“請丁神父進來!快請!快請!”
人們讓出了路,擠在雅美族朋友間的修士,卻是笑著不肯進來——他不能丟下他的人,情願一起淋著大雨。
我瞭解這位修士,在他親密的友伴裡,不願做一個特殊的人。於是我又去對長官請求,結果晚會場地開放,大家都進來了,每一個人都歡喜,我想我是最歡喜的一個。對於那位好長官至今感激。
颱風來了,預定離開島嶼的小飛機停開,子卿和我回不了臺灣,心中也不著急。
那時候,我們已在島上七日了,最感興趣的是跟雅美族的青年和小孩子學講當地話,每日傍晚的海邊,吹著颱風,一句一句地學,雙方的情感漸漸地因此建立起來。
島上七日,世間千年,對於大海之外的世界,覺得十分遙遠而不重要,沒有什麼理由急著要回去。
颱風過去了,確定第二日的飛機便要載著我們離去,那三個受管訓的人跑來旅社告別,其中的一個給了我臺北電話號碼,說是他母親的,托我千萬轉告他的家人他在島上的生活情形,又說請姐姐寄兩百元給他。
我猶豫了幾秒鐘,還是答應了。
那是蘭嶼的最後一個夜晚,修士破例下山來,與我們同坐在海邊。
“去了要不要寄英文《中國郵報》來給你,看看你自己的文字?”我問他。
“不必了,我在這兒很好。”他說。
旅社透出來的燈光十分幽暗,修士的側面襯著一波一波湧來的海浪,他自己也不自覺的寂寞在一瞬間閃了出來,就那麼一下,也就隱沒了。
那時的他,實在是一個大孩子,千山萬水遠離故鄉的靈魂,在這寂靜的島上,默默地對雅美族的居民付出了他的愛。
“這裡需要人來,其實你會是合適的人選,這兒的人歡喜你,才一星期多的時間,你有了多少朋友。”
聽見他說出這句在我心裡縈繞了已經好多回的念頭,我默然不語,膝上抱著的一個小孩子伸出髒髒的小胖手在撫我的臉。
“我能做什麼?能對他們做什麼?這兒的小學也不再需要人了。”我說。
“你有愛他們的能力,這比什麼都珍貴。”
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我腦中掠過的卻不是雅美族人,而是那幾個管訓中的青年,他們必是無惡不作才送到這兒來的,可是那一個深深記得他老師的青年,在內心的深處,必然仍有一絲善良的東西在喚醒他,至於方式的問題,便見仁見智了。
“你想,有一日你會回來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決定,人的路,走了出去,要回頭便費力了,我得再想。”我說。
那時我方知,這位修士因為還得去輔仁大學念神學院,不久的將來也要離開蘭嶼了。
提到離開,他顯得異乎尋常地悲傷,那份不舍,使得這位青年一時裡哽然無語,好似他的根,他的生命,已經深植在這片荒寂的海島上,要離去,於他是極大的茫然。
“其實,你跟雅美族的人,在文化上的差異仍是有的,這無關情感,可是另一部分的你,事實上是封閉了,起碼我的看法是如此的。”我說。
講這些時,我一直對他說著英語,不為什麼,只是想他也許偶爾也歡喜聽聽他自己生長地方的語言。
“我不喜歡離開,臺北對我陌生而遙遠,這兒的人,已是我的鄉親,可是——”
我舉目看見那在深暗藍天下山的黑影,看見永不止息澎湃的海洋和那一片朦朧光影中來去的雅美族人,我的心,竟也浮起了離去的悵然。美麗寂靜的島嶼和居民啊,我也開始愛你們了。
我們交換了地址,便如此告別了。
過了不久,那位修士到了輔仁大學進神學院。再過了一陣,我再度離開臺灣,又去了西班牙,在那兒教了一年小學生的英文,便去北非定居,從此很少回到臺灣來。
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我的情況十分不好,喪失了生的意志,也喪失了信仰的能力,我回到故鄉來養息。那時,耕莘文教院的一位陸達誠神父一再地給我開導與鼓勵,接著西班牙籍的沈起元神父也用極大的愛心來幫助我度過今生今世在人間最最艱難的功課。
便在陸神父那兒,才知蘭嶼時的那位丁松青修士原是光啟社丁松筠神父的弟弟,而今他已是神父了。
這位在我腦海中一直十分鮮明的神父,在去年我再回來的時候給我寄來了他的手稿和許多當時的照片,那便是今日譯成中文的《蘭嶼之歌》。
我深愛這一本有生命,有愛心,有無奈,有幽默,又寫得至情至性的好文。丁松青那誠實而細膩的筆調,和對當地雅美族同胞真摯的愛,使得蘭嶼,在他的筆下,在他的心裡,成了永恆之島。
這是一部真真實實的生活紀錄,再沒有什麼書籍比真實的故事更令我感動。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才情,第一本書,如果沒有一個如此美麗而敏感的詩人之心,是不容易寫得如此傳神的。
預祝《蘭嶼之歌》這本新書得到所有愛世界、愛人類、有信仰、有盼望的人一同的共鳴和讚賞。
丁松青神父,深愛我們中國的一位朋友,至今仍在臺灣某地的深山裡為著山胞服務,他的信仰,只有一個字便包容了全部,那便是將對天主的愛,經過他的心靈,交付給了人類。我由他的行為而得到的啟示和榜樣,是當一生感念的。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