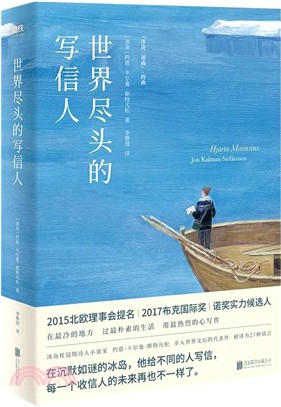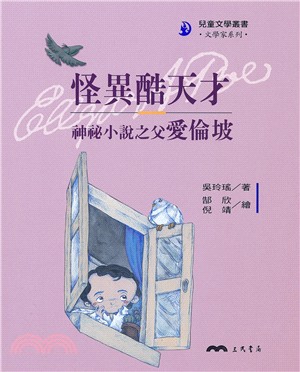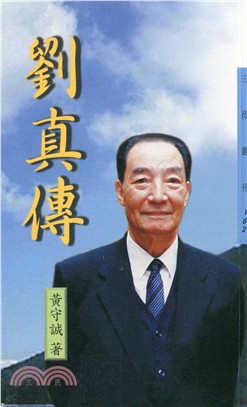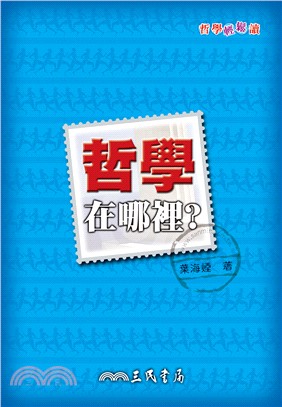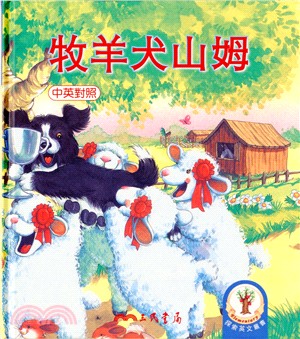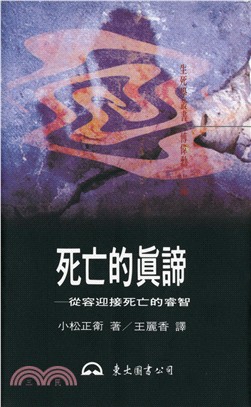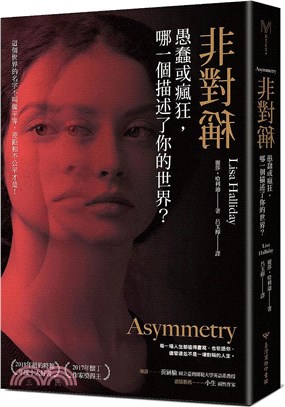世界盡頭的寫信人(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一百年前的冰島,世界的盡頭,一個年輕無名的男孩在不斷的失去中重新尋得生活意義的故事。
他出海捕魚,卻見證好友因一句彌爾頓的詩句而喪生北極海。藝術和美,這世界上Z讓人傾心的東西卻Z容易讓人陷入險境。
他幫好友把書還給原主人,卻在那裡生平第一次遇見令他倍感迷亂的自由:一個人的房間,看不完的書本以及撩人心弦的紅發姑娘。
他讀書人字,代人寫信,象和表達別人的愛情和甜蜜。收信人在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想起男孩寫下這些句子的樣子,總多一分羞澀和快樂。男孩懂得了詞語的秘密,語言的力量。
一封封給人帶來希望與遐想的信,緩慢而不可逆轉地改變著人們對生活的另一種想象……
信和文字,是過去時代裡對濃烈情感的Z樸素表達。我們在字裡行間糾纏著愛,所以才有了歷史。
作者簡介
約恩.卡爾曼.斯特凡松
冰島作家,詩人。
1963年出生於雷克雅未克。斯特凡松做過屠宰工、捕撈工、磚瓦工,還在機場做過一個夏天的警察。他曾在冰島大學研習文學,肄業後又做過教師、地板清潔工、圖書管理員,陸陸續續地出版詩集。一個普通而樸素的文字創作者。
2000年始,他專職寫作。2005年,“冰島三部曲”讓他真正地走入國際文壇並立即獲得廣泛聲譽。十餘年來,他的一系列作品被譯成27種語言,數次斬獲及提名國內外重要的文學大獎,如布克國際文學獎(2次)、都柏林文學獎(2次)、法國費米娜小說獎以及有“小諾貝爾文學獎”之稱的北歐理事會文學獎(4次)。
斯特凡松的文字幹凈清雅,並且充滿了北歐特有的冰涼的想象力。他形容山之高遠時,寫“像尖叫一樣尖銳的山尖”;他形容山之低矮時,寫“山坳短得像一個猶豫”。他的寫作不僅深深根植於人心之間冷暖交替的現實機制,更與冰島無可替代的自然環境緊密聯系。只有冰島的雪、山和海能孕育出斯特凡松對語言的這般想象。
名人/編輯推薦
◎這是一部關於生活與存在的深度探索之作。以男孩為圓心,斯特凡松用令人難以忘懷的詩性語言刻畫了孤獨又溫暖的心靈群像。在“世界盡頭”,我們幾乎看到了世界上每一種絕望、脆弱和對美的衝動、對生的向往。——本書編輯 面面
◎在冰島的夏日裡,斯特凡松令人沉浸的句子隨海浪的變化應和著雷鳴,閃著光亮。僅僅是語言,就能提供給我們對抗時間、死亡、健忘和不快樂的武器。斯特凡松是擁有這般武器的高手。如故事中校長向男孩講述他心愛的經典時所說,“就像所有重要的著作一樣,它也關乎人如何成為人”。這令人振奮的三部曲也如此。
——《獨立報》記者、英國作家Boyd Tonkin
◎這就像牡蠣一樣,在粗糙的外殼中閃閃發光。
——《明鏡周刊》
◎生死、快樂、選擇、運氣、性,所有這些東西的意義都在這裡被詩意而憂鬱地討論了一遍。能讓我感到如此強烈、樸素又莊嚴的小說很少,更不用說三部曲了。閱讀它們!在斯特凡松哲學性的延伸裡放松吧,這豐盛的語言,將帶給你幽靈般敘事的寧靜。
——Goodreads讀者Leif
◎這個沒有名字的寫信的男孩,他為我們見證了死亡的意義,見證了“擁抱大於生命”。這擁抱是如此近在咫尺,讓人似乎能感覺到它的熱氣。
——亞馬遜讀者Marcia Letaw
目次
1這是我們要講述的故事
2一份古老的阿拉伯醫學文獻中寫道:人的心臟分成兩個心房,一個叫幸福,另一個叫絕望。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
3通往天國之弦?
4生命,那偉大的樂器,既不圓潤動聽,也沒被上帝調好音
5那寓於存在中的開放性傷口
6我們最懷念的就是存在
7除了親吻,死亡還會在何處止步
書摘/試閱
I
夢境終於何處?現實始於何處?夢來自內心,它們從人人皆有的內心世界汩汩流出,它們可能是扭曲變形的,然而什麼不是扭曲變形的呢?什麼不帶凹痕呢?我今天愛你,明天恨你——聲稱永不改變的人,是在對世界撒謊。
男孩閉著眼睛,在地上躺了很久。不確定現在是白天還是夜晚,不確定他是清醒的還是在熟睡。他和詹斯摔在硬東西上。他們先是沒找到哈加提,那個跟他們一起從內斯出發的農場雇工;他們仨拖著奧斯塔的棺材走過山地和荒野,然後男孩和詹斯摔到硬東西上。過去多長時間了?他在哪裡?男孩猶豫地睜開眼睛。睡眠之後,等待你的東西並非總是確切無疑的,世界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生命消亡,星星間的距離增大,黑暗加深。男孩猶豫而不安地睜開眼睛。他躺在月光下的房間裡,躺在慘白的月光下,哈加提坐在椅子上,死死地盯著男孩,臉蒼白得讓人難受。奧斯塔站在床邊,散發著寒意。你總能逃脫。哈加提緩緩地說。是的,總是有人準備著把他拉起來。詹斯說著在他旁邊的床上坐起來。月光為他織就了死亡的罩衣。但是現在沒人能幫你了。奧斯塔說。不,他不值得。詹斯說。不管怎麼說,他能有什麼可獻出的呢?他有什麼權利活下去?哈加提說。男孩張開嘴想回答,想說些什麼,但他感到胸口沉重,幾乎沒辦法說話。而後他們的影子慢慢退去,慢慢消失,月光變成了無盡的雪,房間變成了充斥世界的冰冷荒地。天空是覆蓋一切的厚厚冰層。
II
我睜開眼睛安不安全?或許男孩沒有睡著,或許只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死去。男孩聽不到風聲,聽不到雪被風吹起的沙沙聲,也感覺不到寒冷。我一定是在雪地裡睡著了,這樣的睡眠會變成柔軟舒適的死亡。我再也無法抗爭下去了,男孩想,現在沒有人能幫我,奧斯塔是對的,如果最好的一切都已終結,為什麼還要抗爭呢?但我要接受教育,吉斯利校長本人應該會教導我。死亡是不是一種背叛,我是不是不必戰斗?難道他不是正躺在床上嗎?他感覺自己好像在一張柔軟的床上,真奇怪。也許他只是躺在蓋爾普特的房子中,躺在他自己的房間裡,夢到了這一切,夢到了和詹斯一同穿過暴風雪的旅程。難道有可能夢見這麼多的雪、這麼大的風、這麼多的生命和死亡嗎?夢境大得足夠容納這一切嗎?他無法睜開眼睛,可這是多麼簡單的事。他的眼皮如同沉重的石板。他試著去感受周圍的事物,派出他的手去完成調查之旅。但他的手和眼睛一樣無用,他甚至感覺不到雙手,也許它們死掉了,冰霜已經啃掉了他的雙手。它們像雪地上的舊木塊一樣躺在那裡。詹斯,你在哪兒?男孩想,或許嘟囔出了聲,而後又沉入睡眠——如果這真的是睡眠,而不是死亡。他沉入了睡眠,陷入了噩夢。
III
你確定好了嗎?你是想活下去還是想死去?這個女人或女孩問。她長著紅頭發,死者長著紅頭發。我不知道,男孩說,我不確定自己知不知道這兩者的區別,也不確定這是不是如此重要。我會吻你,她說,你會感受到區別,如果你感覺不到親吻,那你無疑就是死人。她一下子站起來,彎下腰,頭發紅得不像是真的,她的嘴唇溫暖而柔軟。生命若不在一個吻中,又在何處?
IV
男孩醒來時,周圍半明半暗,實際上是曙色朦朧。他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身上蓋著溫暖的毯子,毯子散發出新鮮的春日氣息。他的手還在,懷著信任耐心地等待著他,冰霜沒有咬掉他的手。他可以舉起雙手,活動手指,盡管手指的動作僵硬,就像糊塗的老人,但它們仍在原處。真棒。他喃喃自語。他辨認出窗簾後面兩扇窗戶的輪廓,聽到了近旁深深的呼吸聲,於是鼓起勇氣和力量,用胳膊肘撐起身體,環顧四周。他在一個相當寬敞的房間裡,房間裡還有張床,有人躺在床上呼吸。那是詹斯。所以,他們還活著。你怎麼知道自己還活著,而不是死了呢?這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男孩想了想,然後舉起右手的食指,用力咬了一口。他感到疼痛。所以,他的食指應該是活著的。不管怎樣,這都是件大事。另外,起床需要做出相當大的努力,他感到頭暈目眩,他應該繼續躺在那兒。把身體的重量壓到小腿上或許是個錯誤,天堂與地獄之間的這場拔河賽剛剛開始。地板很冷,男孩蹣跚著走到詹斯床邊,站在他身旁,看著他呼吸,然後坐到床邊,松了口氣。很好,這個難相處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應該還活著,那他妹妹海拉就不會被陌生人捆起來,也不會被人踢打。
男孩聽到有動靜,一位矮個子女人走了進來,表情看起來有點尖刻,仿佛認為這個世界上沒什麼好東西。哦,你醒了。她說。這會是他夢中的那個女人嗎?那個親吻過他的女人?她如此尖刻,至少有二十歲了。我怎麼了?男孩問。我怎麼會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在哪裡。在斯雷圖埃利的醫生家裡,不然你還能在哪裡?
這不是他夢中的那個聲音。這個女人不是夢,她更像是一段繩子,堅韌而堅定。在斯雷圖埃利。他慢慢說,就像要品味這個名字。這是他們在兩天兩夜裡的目標,是風暴背後的休息和安寧。所以,他達到了目標。他和詹斯已經達到了目標。可是哈加提呢?她把手放在臀部,兩眼之間的距離不太大,神情有些不耐煩。也許她知道人的生命短暫,天空變了顏色,於是你就死了。所以說我們做到了。男孩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看起來是這樣。女人說。
但我們怎麼到了這裡?……到了床上,我是說,詹斯和我。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你什麼都不記得。可你真的已經說得夠多了。
我說話了嗎?
你一暖和過來就開始說話,一半的話讓人聽不懂。最重要的是,你想赤裸裸地衝回到暴風雪中。大家不得不按住你。沒錯,赤裸裸,你的衣服當然一定要脫掉,它們都凍在了你身上。人們摩擦你們的身體,讓生命重回到你們兩人身上。
她走到窗前,唰的一下拉開窗簾,日光流瀉而入。哈加提在哪裡?男孩在眼睛適應了光線後問。哈加提,她走出房間時站在門口重復了一遍,我不知道。你胡言亂語的結果是,十個人被連夜派了出去,他們差點兒沒逃過雪崩。等一等。男孩在她轉身離開時幾乎是喊了出來。就好像我有時間談這些似的。說完,她就走開了。
她沒關門,迅疾的腳步聲遠去了,短促的、快速的步伐。不久後,男孩聽到了說話的聲音。詹斯的呼吸如此緩慢,簡直稱得上平和,就仿佛這大個子終於對生活感到滿意了。睡眠可以這樣欺騙我們。他們睡了多久呢?他們撞上這棟房子時是夜晚嗎?男孩又一次小心地從床上起身,雙腿支撐著身體,但是雙腿的狀態很差,它們已經衰老了很多,右腿可能老了幾十年。外面相當明亮,也許快到中午了。所以說,他睡了至少十二個小時,難怪他感覺頭昏昏沉沉的。多云,沒有即將降雪的跡象,大風和寒冷確定無疑。風隨處卷起白雪,就像是出於無聊,不過不論哪個方向的景象都沒有受到風雪的遮擋。還有大海,鉛灰色的、波濤洶涌的大海,在兩山之間翻騰打旋。男孩朝右看去,看到向遠方延伸的海洋,在無邊無際的遠處變得更加平靜。群山是白色的,太遙遠了,不會有什麼威脅。群山完全是白色的,除了黑色的懸崖峭壁,那裡如同地獄之門。男孩伸出一個指尖慵懶地滑過嘴唇,好像在尋找一個吻。親吻、聲音、紅頭發、溫暖,那是夢嗎?
站在窗邊很冷,冰霜和雪的氣息穿過了薄薄的玻璃。男孩窺見幾座積雪覆蓋著的房屋,那包含著生命的冰冷外殼。他向前傾身,辨認出了教堂的輪廓。奧斯塔是不是在裡面,等著入土?哈加提在哪裡?男孩向外張望,似乎希望能看到哈加提從一座白雪覆蓋著的房子裡衝進另一座房子,那樣他大概就是在尋找受祝福的波迪爾杜爾。一本著名的書上說,人生就是要尋找一個可以共度一生的人,並在找到後幸存下來。能夠這樣也很好,因為孤獨地生存肯定總比有人陪伴更難。我們孤獨地降生、孤獨地死去,如果也在孤獨中生活,那會是件令人心碎的事。男孩試著想起萊恩海澤——特裡格維商業貿易公司代理人福裡特裡克的女兒。她就要在陽光下遠行了。可是接著就有人走上樓梯,沉重地跺著腳。男孩正要回到床上,躲到被子下面,卻停了下來,決定重新回到窗前。但他又改了主意,因此當一個中年男人進來時,他正好在床和窗戶中間,或者說,正好無處可去。地板在那個男人沉重的身體下咯吱作響。他身材健碩,個子高大,幾乎禿頂了,卻留著濃密的長鬢角,穿著一件羊毛背心和外套,鼻子明顯發紅,灰藍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窩裡,讓鼻子看起來顯得更大。所以這是真的,你醒了。男人說。他嗓音深沉,但聽起來有點疲憊或嘶啞。他嘆了口氣。不錯,你能休息一下。一個出現在男人身邊的女人說。她比他矮一頭,更年輕,或許要年輕二十歲。她身材瘦削,有著一頭濃密的金發。她那明媚的表情讓男孩再次想到陽光、夏天、六月藍色的夜晚,它們還會回來嗎?那更像是一段繩子的女人靠在門框上,雙臂交疊在脹鼓鼓的胸前,她的表情似乎在說:你休息過了,現在呢?
有一會兒,男孩站在房間中央,穿著手紡羊毛編織的別人的衣服。衣服太大了,生活似乎在煞費苦心地貶低他。那男人把拇指插進褲子說:那好。那個表情明媚的女人說:你應該休息一下。然後男孩上床躺了下來。來幫我拿湯。她說道,目光並沒有從男孩身上移開,另一個女人放下交疊的手臂,走了。腳步遠去。你真的應該躺下。女人對男孩說。她坐在床邊,向他靠近時,她顯得比遠看時要衰老一些,臉上有微小的細紋,深深的皺紋——時間之爪留下的痕跡。歐拉弗爾想見見你,之後我們真的很想聽聽你的旅行故事,還有可憐的奧斯塔的故事。可以肯定地說,自從你們,你和這個大個子,砰的一聲摔到村裡以後,村裡的人幾乎就沒再談起或想到過其他事情。她邊說邊看了看詹斯。見我?男孩問,心裡不太確定在床上該怎樣躺著。
不好意思,你還不認識我們。這是歐拉弗爾,這個地區的醫生,我丈夫。女人說著,朝那個男人揮了揮手,有點像揮舞著一只翅膀。他快速鞠了一躬,微笑著,眼睛看穿了男孩。我是斯泰努恩。她說完,便站起來給丈夫讓出地方。他重重地坐到床邊,輕輕嘆息,仿佛在這場令人疲倦的永恒拉鋸戰中筆直站著讓他感到不舒服。他開始開男孩的玩笑,問他簡潔而尖銳的問題。是的,我的腿能移動。不,我的手臂不麻木。是的,我脖子酸痛,疲憊,是的,虛弱。好啦。斯泰努恩說。她丈夫站起來,她重新坐下。他這麼年輕,因此他幾乎什麼都能承受。醫生說,休息,吃像樣的食物,喝水,保暖,差不多再過一個星期或再過十天,他的身體就會棒得如獲新生。你真年輕啊。斯泰努恩贊同地說。年輕真好,歐拉弗爾說,總是在變化。今天你是這樣,明天就是完全不同的你。我們都該年輕,永遠不變老,永遠不讓時間趕上我們。你不想改變,你討厭改變。他妻子輕輕晃了晃那一頭金發,說道。
詹斯好嗎?男孩輕聲問。他突然覺得有氣無力。詹斯,這麼說他的名字是詹斯,那個大個子。歐拉弗爾說,嗯,唉,他比你糟糕,無法否認,他受了凍傷。
更糟?男孩遲疑地說,就是說他沒脫離危險?
脫離危險?一個人什麼時候能脫離危險?歐拉弗爾說,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但他可能最終要瘸著腿走路。也許更糟。
他們都陷入了沉默,就好像在思索最後幾個字。也許更糟,那是什麼意思呢?更糟是糟到什麼程度,生命離死亡有多遠?
男孩猶豫了一下,然後問道:所以說,你們沒找到哈加提?他終於鼓起勇氣問了出來,因為只要不發問,人們就還活著,他們在沉默中安然無恙,然後我們開口說話,於是有人死去了。哈加提。歐拉弗爾邊說邊看了妻子一眼,然後望向窗外。你講了很多關於這個哈加提的事,因此我們把小伙子們送進了風暴。一共十個人。奧弗海德爾立刻就把他們召集到了一起。夜晚,暴風雪,一場雪崩,情況就是這樣。說完,他回頭看著男孩,重復道:情況就是這樣,我告訴你!你說得就好像他不知道似的,把他們趕到這裡的是同樣的夜晚和同樣的暴風雪。他妻子看著男孩溫柔地說。她那美麗的眼睛就像古老、溫暖的星星。歐拉弗爾走到墻邊,拉過一把木頭椅子坐下來,點了點頭。當然,非常正確,把他們趕過來,實際上是把他們扔過來拋到房子上,嚇了我一大跳,弄灑了這個冬天的最後一杯雪利酒。那滴滴美酒、那濃郁的酒香就這樣浪費了。他短短的手指敲著膝蓋,吹起口哨,吹出了悠揚的旋律。歐拉弗爾和我那天睡得晚,斯泰努恩說,仿佛是要解釋,我們正在寫信,結果你們來了……喧囂迅猛,歐拉弗爾打斷了她的話。對,喧囂迅猛。她表示贊同。砰的一聲。歐拉弗爾說,同時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嚇了男孩一跳。但是按你所說的,斯泰努恩說,你們還有同伴,所以我們派人上山。出門闖入那瘋狂的暴風雪中,歐拉弗爾說,他們找到了內斯的奧斯塔、一個雪橇、一個棺材的碎片,但沒找到別的。
男孩閉上眼睛,突然感到一陣暈眩,內斯農場外的哈加提的形象飄然而至,占據了他的全部意識。那個男人在他前面滾著一個不斷膨脹的雪球,把最小的男孩像麻袋一樣夾在胳膊下面,其他孩子在他身邊歡呼雀躍。難道這個身材高大卻略帶悲傷的人已經死在曠野裡了嗎?詹斯說過,他有辦法,而詹斯知道這些。他肯定知道。也許哈加提只是回到了孩子們身旁,回到了他所屬的地方,那世界背後的海灣。孩子們需要他,世界不可能可怕到這種地步,竟會把那個大個子從他們身旁帶走。你現在該吃點東西了。斯泰努恩說。她的聲音令人平靜,如同溫暖的擁抱。有些人就應該坐在你身邊說話,他們的聲音可以紓解痛苦和疲憊。男孩睜開眼睛。那個女人,一段繩子一樣的矮個子女人,已經回來了,舉著個熱氣騰騰的托盤。她肯定就是奧弗海德爾,她就是把人們召集起來尋找哈加提的人。還有奧斯塔。可是她已經死了,搜尋死者沒有意義,你不會尋找到已然逝去的東西。男孩聽到樓下傳來孩子的笑聲,聲音縹緲。盡管有死亡,但生命仍在歡笑中繼續,如此無法忍受,如此無味,如此重要,那是我們的主要依靠。斯泰努恩讓男孩坐起來,把一個枕頭墊到他腰上,奧弗海德爾把托盤放在他的膝蓋上,托盤上是冒著熱氣的湯,她彎下腰調整托盤,領口散發出微甜的濃郁氣味。男孩低頭盯著盤子,看了良久。吃吧,親愛的。斯泰努恩說。哈加提,男孩對著湯說,他是比亞德尼和奧斯塔的農場幫手,他是,或者曾經是。男孩對於時間的指示感到困惑,他究竟該說過去還是說現在呢,如果說的是過去,那哈加提會死嗎?我不記得哈加提這個人,斯泰努恩說,但我總是忘記名字,也會忘記人。而且,有些人就是很難讓人長時間記住,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歐拉弗爾說。
奧弗海德爾:我認識一個叫哈加提的人,但他很多年前就淹死了。
歐拉弗爾:大海,該死的一切,真艱難。他有家嗎?
奧弗海德爾:四個孩子,一個妻子。
歐拉弗爾輕輕嘆了口氣,說:的確,這真不該發生。
奧弗海德爾:這世上確實存在正義,這話是他妻子得知他溺水時說的。
歐拉弗爾:什麼?
男孩對著他的湯斷然說:哈加提沒淹死,他是……他是比亞德尼和奧斯塔的農場幫手……或者曾經是……我的意思是,她死了,當然。
湯又濃又熱又豐盛,可男孩喝湯時什麼都沒意識到,仿佛在發呆。
奧弗海德爾拿起托盤。又是那溫暖發膩的氣味。我也要給他帶點咖啡嗎?
歐拉弗爾:多拿點咖啡來,親愛的波爾蒂斯。
男孩抬起頭,想著名字一會兒一變,這真是太奇怪了。被稱為波爾蒂斯的人含混地咕噥了句什麼,聲音幾不可聞。男孩則閉上眼睛,哈加提的樣子清晰地浮現在眼前,清晰得叫人難以忍受。他看到哈加提的眼睛,其中刻著失望,或許是憂傷。他聽到哈加提在雪橇帶著棺材滑跑前說的最後的話:該死的!伙計們,難道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死去嗎?在那之後三人就彼此失散了。然後男孩睜開眼睛問道:他們能再去找一次哈加提嗎?
歐拉弗爾:什麼,再去找一次?第三次?
第三次?男孩問。
醫生回答,他們昨天已經進行過更仔細的搜索了,這是第二次了,天氣不是很糟糕,風不算太猛,不至於把人吹倒,但他們還是什麼都沒找到。我們估計還有別人和你們一起運送尸體,把一個棺材運過一座山,兩個人是不夠的。
男孩:我們到了山谷那裡。
斯泰努恩看著丈夫,說:現在他有可能站直身體好好看看周圍了。醫生緩緩起身,走出去大聲呼喊:奧弗海德爾!召集一些小伙子,告訴他們去尋找這個哈加提!告訴他們沿著山谷找!如果他們抱怨,就讓他們來聽我解釋!他們會不開心的,可憐的小伙子們。醫生回來時說。人不可能一輩子都開心。斯泰努恩說。不,從長遠來看終究是沮喪的。歐拉弗爾說。你願不願意給我們講講你的旅行故事?斯泰努恩問男孩。對,有故事不是壞事。歐拉弗爾說。嗯,咖啡來了。波爾蒂斯端著給他們三個人喝的咖啡回來時,他又加了一句。男孩意識到那個故事可能非講不可了,他們或多或少都期望聽到他的講述。這邊有沒有一位女子,名叫波迪爾杜爾?男孩緩緩地說。波迪爾杜爾,這對夫婦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人。你為什麼這麼問?她顯然是三年前來到這裡的。歐拉弗爾說:我們已經在這裡待了二十年,從來沒見過叫這個名字的人,你為什麼這麼問呢?沒有特別的緣由,男孩喃喃道,感覺胃揪在了一起。他看了看郵差,看著他身上的被子隨著他的呼吸起伏。呼吸的人是活著的,不論這意味著什麼。然後他開始講述他的故事。代理郵差古特曼杜爾生病了,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
V
詹斯在晚上醒了過來。
男孩講完他們的旅行故事後疲憊不堪,小睡了一陣,回憶過去可能總要費力氣,我們由此發現生活從來不是連續不斷的線,除了偶然的巧合,這既殘酷又美麗。一些事件偶然路過我們的生活,而後消逝,什麼都沒留下。然而,有些事件我們會不斷重溫,因為過去就居於我們心中,為我們的日子增色,改變我們的夢想。我們的過去與現在交錯纏綿,兩者有時可能難分難解,你今天所說的話會在五年後回來找你,回到你身邊,像一束鮮花,像一絲慰藉,像一把染血的刀。你明天所聽到的話,會把久遠而珍貴的吻變為蛇咬的記憶。
男孩講述了他們的旅行故事,重溫了發生的事件,卻沒有說出一切,沒有背叛詹斯。他既沒有提郵差詹斯在劃艇上的失敗表現,也沒有提詹斯說過的海拉和家中父親的情況。男孩沒有離題去表述詹斯的心聲,但他說起了住在維特拉斯特倫的那個小女孩,她咳嗽得太厲害了,生命幾乎懸於一線。他還說起了維克的牧師。可憐的老基亞爾坦。歐拉弗爾喃喃自語。更不用說安娜了。斯泰努恩說。失去視力很慘,失去對生活的欲望更糟。歐拉弗爾說。你確定嗎?斯泰努恩接著說,讓安娜周圍一片黑暗的不是愛的匱乏,而是受損的視力?別那麼荒唐,人們不會因為無愛而失去視力,這根本不可能,失明是生物學現象,是科學現象。我們對此知道什麼呢?斯泰努恩說:我們對人了解多少呢?就這個問題本身而言,或許不太多。歐拉弗爾承認道。而後男孩講起了雪、風暴、荒野、荒野上的農場主和少年,講起他和詹斯走散了,但後來他感到奧斯塔出現在他的身邊,在黑暗的暴風雪中,把他帶到郵差那裡。說到這裡,男孩注意到這對夫婦的神情,於是又說:可能這只是我的想象,她什麼時候下葬呢?明天或後天,斯泰努恩回答,要看吉斯利牧師的健康狀況以及挖掘墳墓需要多久,挖開冰凍的地面非常困難。他們要挖多深?男孩擔憂地問。他模糊地覺得,她躺得越深,就越有可能找到安寧。最深挖一米半或兩米,歐拉弗爾說,這裡死者安眠的地方都不深。不過希望我們在夏天能更好地埋葬她。希望?年輕人,在夏天,有鳥鳴、飛蠅和所有的魚,很多東西都會被遺忘。陽光正燦爛時難以記住死者,可能也沒有記住的必要。
男孩快講完時,波爾蒂斯走了進來,給詹斯拿了一個新的熱水袋。可你是誰呢?波爾蒂斯換完熱水袋後,歐拉弗爾問道。兩個女人下意識地看著男孩,男孩什麼也沒說。他究竟該說什麼呢?一個人該如何解釋自己的存在呢?我是誰?是我們的所作所為塑造了我們,還是我們所夢想的塑造了我們?斯泰努恩沒有得到男孩的回答,於是說:你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猜測。你穿著制作精良、價格昂貴的雪地靴,我猜是挪威靴子。你穿著暖和的衣服,說話時引用詩句,你說的我們無法聽懂,幾乎什麼都聽不懂,真的,但我覺得我聽出了莎士比亞,他可不是你所說的一般人。但你的手表明你做過體力活。波爾蒂斯說,人們要麼辛苦勞作,要麼不用勞作。我現在和蓋爾普特在一起。男孩說,好像這能解釋一切。蓋爾普特?歐拉弗爾重復道,你說的是古特楊的妻子蓋爾普特?男孩點點頭。那好吧。斯泰努恩說。她留下你是不是為了留下後代?波爾蒂斯問。不是,男孩說,而後又唐突地冒出一句幾乎沒經過大腦的話,無論如何我都喜歡你這樣敏感的女人。如果你不是躺在床上,我肯定會揍你。波爾蒂斯說。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