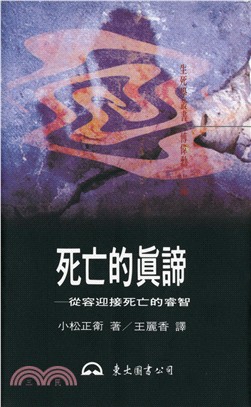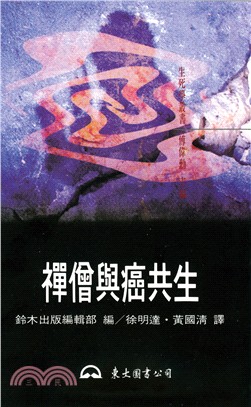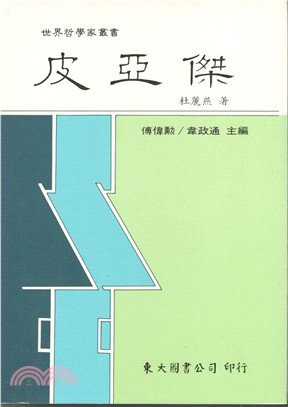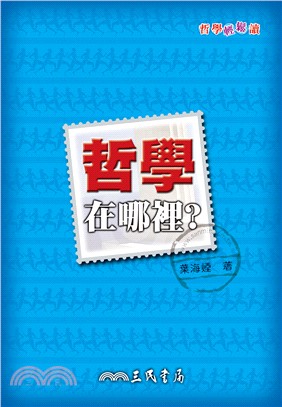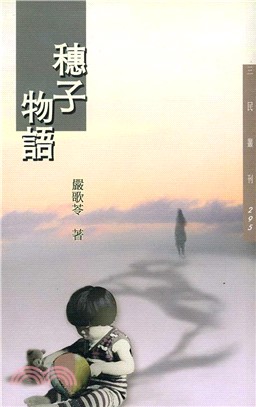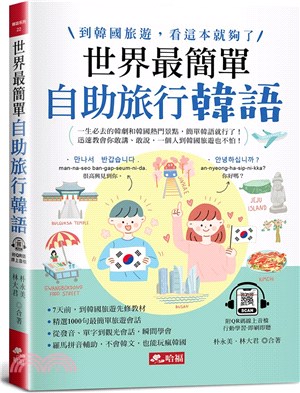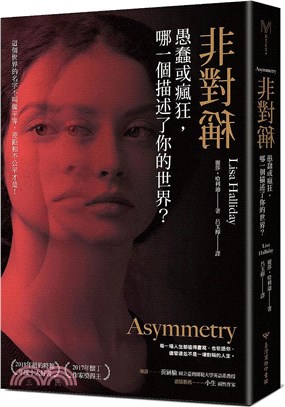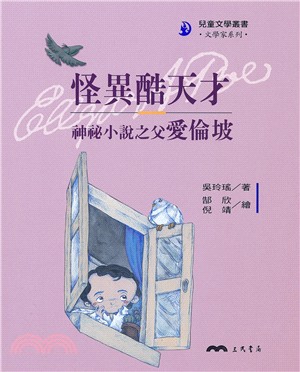商品簡介
曾經,我們都以熱血高舉著青春,
追尋人生中不知是否存在的出口;
卻總在事過境遷後,才明白
在生命與自由的追逐裡,無論如何,必定有所犧牲。
——朱天心專文導讀
——陳淑瑤 黃亞歷 謝金魚 朱和之 一致推薦
來自北港殷實富戶的李綉治,在兄長李良文及其好友莊修之影響下,心底逐漸萌生出文學之夢。由於不願接受家族擺布,兄妹各自思索著從既定人生逸走的可能。綉治拋下一切前往橫濱追尋自己的創作道路,將命運押在一段自由卻無愛的婚姻裡,良文與修之則被時代的旋風捲向未知的蠻野戰場。
身為平凡商家之女的莊美幸,從小仰望兄長修之與李氏兄妹,在自己怎麼也無可觸及的世界裡,彼此閃耀著光芒。美幸懷抱被遺留下來的心情守護家鄉的父母,戰後世事裂變的潮湧卻將她推往神戶,在異地勉力扎根生存的同時,頻頻顧盼故鄉島嶼的稜線。而終戰後的綉治,在家族破敗四散之際,竟決意定居台灣……
兩個來自台灣的少女,跨越近半世紀的牽絆,崩解的時代席捲了她們的一切,最終將她們帶往不曾想望過的彼方。曾經有過的青春,一如完熟落土的果實,被世事歲月剝蝕殆盡。而生命的核根早已纏結在那壘疊風霜的人生厚土裡。
與唐成功做到了小說才能做的事,……將政治正確關在她書房外,擺脫其保障和限制,使得書中人物得其血肉。——朱天心
細緻優雅的文筆,描繪出日治時期知識人的日常與掙扎。——謝金魚
作者簡介
1993年生,台北人,曾獲台積電文學賞等文學獎,以及文化部青年、國藝會創作補助獎。
寫小說之餘,嗜好探勘有趣的台灣歷史,希望分享給更多人認識。
經營 FB 與 IG「Ben & Don」以及 Youtube 頻道「熬夜的便當」。
名人/編輯推薦
唯有小說才能說清楚的事
——讀《食肉的土丘》
朱天心
班與唐這部獲得第五屆台積電文學大賞副賞的《食肉的土丘》,我以該獎決審評審、讀者、此文的寫作者身分曾三讀此作品,確實深有所感、所獲、所被鼓舞激勵。
這部作品,好寫、也難寫。
先說好寫的部分。這些年,在大量的口述歷史、回憶錄面世出土,以及主政者全面修補國族史的背景環境下,《食肉的土丘》的取材,不僅不難,甚至是容易的,一張家族相簿祖輩著異國衣裝的老照片、一段曾經隱晦的街坊傳言、一張圖書館裡的新聞紙、一本回憶錄、一份文獻……,乃至前輩文學作品如陳映真、郭松棻、林俊頴、楊照、賴香吟……的豐富文本(還包括我極喜愛的林芙美子的《浮雲》嗎?),如同在氣候宜當的一片沃土上撒種,怎麼不會順利長出幼苗、並開花結實。
這正或許是某一二位評審的「多慮」,如此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作品,不那麼難吧?更重要的,這缺乏遠古的批評殖民歷史的「史觀」,那麼的符合當下的政治正確,總令人不安。
符合政治正確的寫作,之於創作者,既是吸引(好寫、怎麼寫都對、都好、都易獲獎),也是禁錮甚至毀滅(如同那被賽蓮女妖之歌聲迷惑的希臘水手們)
不得不說,這正是我初始讀《食肉的土丘》時,始終提心吊膽的,是之前我說及的難寫之處,對班與唐這樣一位相對是新手的創作者,能抵抗(或曰不鳥)當下所處的政治正確很重要嗎?很難嗎?我們且看看這段小說老手米蘭昆德拉在《簾幕》(翁德明譯,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五)一書中論及大江健三郎二十三歲新手時所寫的短篇小說〈聲音顫抖的族群〉:
在一輛夜間公車裡坐滿了日本乘客,中途上來了一群醉醺醺的外國士兵。他們開始粗暴的欺負一位大學生乘客,他們強迫這名大學生脫掉褲子露出臀部。軍人覺得只欺負一個人不過癮,接著強迫車裡一半的乘客做出同樣的動作。後來公車停下來,士兵下車一哄而散,而那些受辱的人重新穿上褲子,另外那些乘客好像從束手無策的狀態中甦活過來,並且催促那些遭受羞辱的同車旅客趕快去報警。有位擔任小學教師的乘客陪那名大學生下車並走回家,無論如何要探知他的姓名以便公諸社會,讓輿論譴責那群外國士兵,但故事只在這兩個一陣爆發的恨意後落幕。
這是一篇引人深思的了不起作品,裡面的主題包括怯懦、害羞以及表面上是愛好正義但私底下卻是虐待狂的心態⋯⋯我提起這則短篇小說為的是想探討:那些外國士兵是誰?當然,作者指的應該是二戰後占領日本的美國士兵。為什麼作者只提到「日本」旅客,卻不指出士兵們的國籍?是政治上的考量?是作者個人風格?不是。我們不妨想像,要是這篇作品裡從頭到尾時時提著「日本」旅客和「美國」士兵發生衝突還得了!如果明文寫出「美國」,那麼這個力道萬鈞的詞便會使這篇作品淪為政治文章,變成指控占領者的文章。只要去掉「美國」二字,那麼文章的政治意味便大大淡化,而重點便集中在引發小說家興趣的主要謎面,「人類存在的謎」。
是的,我願意說,班與唐的《食肉的土丘》只情願做了「唯有小說能說清楚的事情」,小說拒絕做某個時代的見證,不願再描寫某個社會,不願再為某種意識形態辯護,小說家可不是歷史學者的跟班(以上字詞引用米蘭昆德拉語)。
沒錯,班與唐成功做到了小說才能做的事,她小說中的人物出邊出沿、毫不典型刻板,但他她們都非作者用來「作為歷史見證、描寫某個社會、辯護某種意識形態」的工具或棋子,班與唐將政治正確關在她書房外,擺脫其保障和限制,使得書中人物得其血肉、體露金風、趔趄前行……,好叫人懸念。
這容易嗎?重要嗎?我得提醒讀者,身在其中數十年,深深知道能夠不被概念帶著走、不被政治正確所召喚、不被讀者(市場?)所干擾⋯⋯這在開始創作時可能是人人皆懷抱的理想初衷,但時間拉長後是並不容易護持住的。
班與唐做為行車行船的駕駛,方向輪舵握得極穩,是很好的習慣、能力、和選擇(一些成名的作家都未必能做得到做得好)。
都說現下小說難寫的這些年(有大環境的影響如網路分掉了大半原來小說在做著的事,也有「低處的果子摘完了」的荒年期,小說難寫到索性作家不寫了……),早有作家用「廢墟」二字描述文學書寫當前所呈的面貌(無論寫的那方或讀的那方),我要說,還「廢墟」咧,廢墟尚有一些列柱、殘壁可供想像那神廟的曾經壯麗,我用的是「瓦礫」,得讓後來的作者咬緊牙關、嗚咽著在其中尋摸撿拾端詳碎石,分辨著,鑑賞著……,以之為磚石,建起自己的小說房子。
或該說,這些瓦礫的揀拾、擦拭、拼圖……才是班與唐的樂趣所在吧,她將之牢牢攢握於手,不叫風中的強大神話襲捲而去,如此,我們應該不吃驚在此時此際的台灣面對這題材時,它未被那「神話殖民」或相反另一側給挾持而去,再次,展現了(常為勢奪常為利誘)政治做不到而文學才做得到的事。
這段我曾在決審觀點寫過的話,願與班與唐共勉。
目次
推薦序 唯有小說才能說清楚的事 朱天心
桃
蟬殼I
時差
火燒
思念藍色的海
燃菸的一生
櫻瓣的一生
看海
巧克力
雕像
女給小說
蟬殼II
家庭訪談
書摘/試閱
桃
身著素白套裝頭戴圓帽的山口幸子,頂著台南的豔陽走到教堂的門廊前,街道發亮得連影子都沒有。
七月的島嶼充滿壓人的盛氣,像是巨大的蒸鍋,街上的人車身影搖曳,彷彿隨時會逸散煙消。然而人是隨和的,躲在屋內不出門,吸食飽餐後令人昏厥的空氣,猶如天然的鴉片菸,專屬於熱帶島嶼。
這天是星期六,修女們備完晚飯要用的食材,棲坐在教堂鐘樓外的階梯。聽見樓下的腳步聲,她們探出頭,議論門外女士的身分。
敢是台灣人——修女手中的塑膠紅扇搧得懶散,熱風徐徐送來。
教堂長在一堆老舊的民房之間,明明教堂早於其他房子,卻顯得教堂連同門口的大王椰子占據了民房該蓋用的位置,使得教堂氣派的巴洛克式圓柱失去莊嚴,就像在說,在這熱帶的土地,沒必要過於拘謹,一切隨安吧。
黑髮牧師為幸子打開旁門,引領她穿越長形的禮堂,走到末端上階梯到二樓。牧師帶她走到最後一間,在門扉上敲兩下,裡面的人應門了。
牧師對幸子微笑便離開,留下她一人面對那扇門。幸子深吸一口氣,脫下帽子入內。
床鋪坐著一名女人,灰白長髮束在脖間,窗戶透入的光線照得頭髮銀亮。女人雙手整齊擺在被單邊緣,幸子牽起那雙手,試圖在女人衰老的皮囊找回記憶中的模樣。
李綉治,那名穿著筆挺制服的女孩,水亮的眼神非淑女的婉約,而是帶刺的光芒。
現在的李綉治,眼神像是快要熄滅的火燭,雙手冰冷。
「美幸。」綉治積蓄的氣絲,叫出山口幸子的舊名。
「綉治。」幸子輕聲說。
「我都認不出妳了,完全就是個日本人的樣子。」
美幸脫下套裝的外套,「唉,我都忘了這裡有多熱。」
——神聖的青春,有著平靜及坦率的神情。
四十五年前,昭和十八年,綉治離開前兩人其實沒有真的見到面。綉治站在莊家的雜貨店舖前仰望著二樓窗戶,一頭剛褪去學生味的捲髮懸在頸肩宣告新身分,穿上父親從內地帶回的純白洋裝、洋皮鞋、絲襪,一身洋派的布料頂撞南國的溽暑。
綉治不知道美幸當天也在場,躲在巷子裡的美幸,制服裙下黝黑的雙腳踩著木屐。
蟬聒噪得惱人,經過的老人歪頭。
什麼事會值得一個千金小姐傻傻地等呀,他們的聲音被太陽烤得乾裂。
綉治只在意二樓的人影,她需要他的一個眼神,告訴她離開是正確的。
汗水不斷滑落到鎖骨,再順著身體滑落到腰部的裙頭,濕了的衣服吸走體內的高溫,熱得有股寒意。
身後的司機不停探頭催促時間:林夫人,要來不及了。
最後,人影還是沒動。
綉治一發不語,將自己扭頭塞進車裡,透過車窗看莊家倒退遠去,接著在火車上看北港離去、在船上看著高雄港在海平線消失。從此她再也回不了家,離開東京後第一個地方便是去北港,發現故鄉的樣子她簡直無法辨別出來,堪比戰後重建的神戶。
二樓的那個人,多年來綉治不斷在腦中重複播演窗簾後的人影。
人影說了什麼,現在都已經不重要,他已經死了。
「美幸,我找妳來是有事情要拜託妳。」
綉治拉開床旁矮櫃的抽屜,內有數本筆記本、剪報、信紙以及幾張相片,其中一張是兩名穿學生制服的青年在照相館的合照,他們搭著彼此的肩膀。
「請務必代替我好好保留。」
「別這麼說,我一定會將東西好好交到妳家人的手中—」
綉治打斷美幸,「東西我想要留給妳。我沒有其他人可以給。」
美幸頓一下,點頭答應。綉治的手再也無法維持在被緣,整個人鬆開後陷在床鋪,毫無痕跡地與床融為一體。
「人回想過往,總會感嘆為了得到某樣東西自己犧牲掉什麼,但怎麼就沒有人想過,無論如何都會有犧牲發生。」綉治眼睛定視美幸,「如果讓我再選擇一次,我還是會回來這裡。」
美幸別開頭,「妳又在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了。」
綉治禮貌性地笑,「對不起。」
美幸起身,心臟仍跳得劇烈,責備自己沒注意在綉治面前提到「家人」兩字。
老舊的木框窗蛀蝕嚴重,教堂佇立在台南的年歲比兩人還長。美幸使力推開窗戶,外頭煦暖的空氣注入房內,綉治覺得整個人徜徉在暖陽之中。南方的島嶼,午後總是有催眠的魔力,綉治閉上雙眼,她聽見走廊外修女走動時,腳步摩挲裙襬的聲因,以及街上人們的聊天聲。突然,遠方傳來鞭炮炸裂的聲音,破壞午後昏睡的張力。
小時候的她,討厭逢年過節的鞭炮,大串紅辣,點上火,炸得臟腑劇烈地跳動她將手掌塞住耳朵,努力不留一點縫隙,事後母親責備她把自己的耳朵弄到破皮。
「好熟悉的聲音啊。」美幸輕聲說。
「看來今天是新人的好日子。」綉治回答。「妳有找到米街嗎?」
「不需要找,房子早就拆掉了吧。」
「這裡真的變很多,對吧?」
「嗯,我們也是。」
那時的婚禮禁止使用鞭炮,勉強嗩吶樂隊湊合吵鬧的氣氛。然而在北港,大家仍照樣放鞭炮,大剌剌嚇飛鳥群,村民湧到住家前張望,綉治不知該笑還是佩服那些人,遵循傳統的意志力比誰都強,怎麼不害怕遠處的郡役所或派出所會聽見,就像母親,堅持要為婚禮找來術士,給綉治看了好幾輪才擇定日子。農曆七月二十日,親友聽了都勸不要在七月辦喜事,尤其是出遠行。母親堅定地說,術士看過宜嫁娶,宜遠行,沒問題的。
不管是嗩吶還是鞭炮,以前的綉治聽見了便使力把手指塞進耳道,弄得耳朵發紅,被母親責罵。
回想起來,婚禮的鞭炮、戰爭的燒夷彈,耳膜感受起來都是等同的難受。聲音不會放過任何聽得見聲音的人。
綉治記得以前在高女教室,外面偶爾傳來鑼鼓、嗩吶樂隊,聽見聲音的女學生擠到窗台,遠方看來像是準備伸展的柳枝,等不及春天的降臨,臆測是哪家學姊學妹的嫁娶。
是她呀,真是太幸福了,恭喜。大家如此讚賞出嫁的少婦。
純白、無垢,女性應有的模樣。老師一再強調。
綉治的座位就在窗戶旁,下課鐘響,立馬收拾書包,直衝出校門口,髮辮隨雀躍的心掃著頸肩,背起書包直奔銀座通。
街道上的男女穿著洋式的西米羅、洋裝配高跟鞋,女人細尖的臉蛋畫上細長的眉毛,如資生堂廣告嬌豔,男女成雙地出入各場所。街道穿梭的公共汽車及人力車,和著百貨播送的華爾滋音樂舞動。對於當時的綉治來說,這個就叫做「自由」。
純白杜絕了沾染色彩的可能,她拒絕老師所說的女性模樣。
不同於北港家鄉。市區沒有傳統禮教的拘束,綉治大口吸著新時代的空氣,巴不得不要回北港。卒業後在家的日子,她都在期待哥哥放假回來的日子。等那天終於來了,她趁透早母親忙安頓家事的時候,從側門出去,往環繞裊煙的朝天宮直奔,趕上開往嘉義車站的自動車。一坐上車,她便頭靠著窗戶,埋進小說度過通勤的時光。
一般人到銀座通,通常是去林百貨,或是去同學們喜愛逛的小出商行,販售各式各樣的信箋及文具,但是綉治獨愛一間不起眼的小書局「三一堂」。老闆是一位戴著圓眼鏡的和藹男士,總是穿著整齊的白襯衫,白皙的身影穿梭在疊滿書冊的書架間,他說書局的名字是取自英國劍橋的三一街。
「李小姐,請進吧。」老闆靠邊讓出後方通往二樓的階梯,愈往上走,泡煮珈琲的味道愈來愈濃。
二樓的房間,一盞搖晃的電燈,在大家的頭頂上晃啊晃,湊合幾張簡陋的木桌椅,這裡成為他們的聚會地。他們不喜愛「沙龍」一詞,寧願被稱作「俱樂部」,民主進步的象徵,切割布爾喬亞的臭名。
綉治習慣先杵在門外,踮腳探看房內的哥哥良文還有莊修之,他們兩人總是搭肩,笑著只有他們才了解的事情。良文遺傳到母親的濃密雙眼,但是粗黑的眉毛卻像父親,陰陽在他身上達成美好的平衡。站在良文身旁的修之哥,一臉和煦如夏夜清冷的月光,不過度搶走良文的風采,同時不失自己最自然的光芒。
她喜歡欣賞他們的快樂,猜想他們在笑什麼,尤其是修之,笑起來的時候眼角瞇成迷人的彎月。
修之看見綉治走進來,伸手輕摸她的頭,這是兩人的打招呼方式,從小沒變過。
俱樂部的人討論得正熱烈,突然有人喊良文:「嘿李君,身為理農學部的高材生,你怎麼看糞便跟現實主義?」
房間裡的人憋笑等待良文回答。哥哥總是很能迎合大眾的要求,給出眾人的期待。
「還要問我嗎?你們每個人消化出的東西叫什麼?糞嘛。所以說,任何人寫出來的任何東西不也是糞嗎?這是事實,管你現不現實主義。」
眾人叫好,說李君應該去投稿,一戰成名。
「現在大家都不討論作品了,只關注筆戰像看笑話一樣,好沒意義啊。」回去的路上,綉治將憋了好久的話說出來。
「妳應該來台北看看,太平町樓館都有文壇重要人物穿梭,他們肯定都有共同的危機感,島內文壇像是陷進泥沼,進退不得。即使是那些欺瞞良心,為國家宣揚戰爭的那群人,也是掉進同樣的困局,戰況膠著還能寫什麼。筆戰只是反映了大家不安的心情。」
「我去得了台北嗎?」綉治喃喃地說。
「綉治小姐想來隨時都可以來找我們。」修之瞇眼,「就算是偷偷跑來,妳的車資我們也能負擔喔。」
「少把我也算進去。」
良文追著修之跑,三人就像平常一樣吵鬧,在米街如腸的巷弄內用流暢的國語討論詩句,在本島人聚集的屋瓦中,磚牆探出的眼光都不值得他們回首注意。但願三人能永遠並肩走在一起,即便那是不可能的。她撐起微笑的嘴角,不想破壞現在的氣氛。
窄巷突然湧出一群人,其中一名男子撞到她,用小到僅綉治能聽見的聲音說,失禮。
人群馬上轉彎,如老鼠般鑽入其他巷子的深處,消失不見。隨後一群警察追趕上來,良文拉住綉治及修之手臂往路邊靠,整條街都是腳步錯落的聲音。
剩下黑皮書攤在路中央,風吹動,密麻如蟻的文字躺在紙張,仰面朝天。她好奇那些人惹到什麼麻煩。
——別撿吶。
良文回頭看她,幾乎是用唇語在對她說。
修之輕攬她的肩膀帶她繼續往前走,「既然被發現了,他們應該不會再回來。放心吧,基督教累積了好幾千年,不可能輕易被破壞的。」
「難說,你看日本帝國拿下多少領土,戰爭不只是軍火跟砲彈,你們不覺得宗教戰爭開始了嗎。」
「哥哥怎麼什麼都能想到戰爭。」
「一定是因為良文看太多奇奇怪怪的書,上次他看的那本,我記得書名好像跟基督教死亡有關,叫什麼呢。」
「才不是那樣!」
他們愈走愈遠,綉治回頭看,已經分不清道路及黑皮書的輪廓。
在快到修之家前,街上的攤販大多已在收拾店面,除了一名水果販坐在米糧店前大聲叫賣,前面擺一竹簍的水蜜桃。水果販看見修之,笑吟吟地望著他們。
——少爺轉來啦!
水果販連忙為竹籃內粉嫩的水蜜桃灑上水滴,每粒的細毛散發著香甜的光輝。
「喂,等等。」兩人還沒來得及阻止之前,修之已經掏錢買了一大袋。
「沒關係,反正以前稿費賺了不少。」修之開心地捧著。
兄妹兩人互看,走在修之身後。
修之家是長排兩層樓街屋中的一間雜貨店,與其他店舖比鄰,兄妹倆成長經驗鮮少會到這樣子的店,當他們得知有這樣的店販賣各種零食,心裡感到很雀躍。長大後,他們兩人才看出雜貨店與他們生活的差異,家中有許多雜貨店內買不到的食品。
出來迎接的莊夫人見到修之懷中抱著水蜜桃,嘴巴收不起來。
「傻孩子,買那麼多怎麼可能吃得完,給李少爺李千金裝一袋帶回去才行。」
莊夫人說完匆忙鑽入屋內,綉治總覺得穿著和服的莊夫人像是繃緊的蜜蜂,得奮力振動翅膀工作才能生活。他們在店門口可以聽見莊夫人在屋內翻櫃子的聲音。
美幸同學從二樓走下來,瞥一眼水蜜桃。「哥哥,做決定之前先考慮一下別人,好不好。」說完後跟綉治及良文隨便打個招呼便上樓。
「再不買,等秋天來就沒有了,到時候豈不剩下哀愁。」修之故作正經地說,講完自己笑起來。
「傻孩子,又在說傻話了。」莊夫人走出來,她揀選最好看的水蜜桃給他們,給的比留下來的還多。「我們家修之平常受您照顧了。」莊夫人直接將水蜜桃塞入良文懷裡,良文還來不及回應,僵硬地捧著水蜜桃站在原地。
良文瞥一眼身後的綉治,兩人一齊彎腰道謝,向莊夫人告辭。
修之揮揮手後轉身。進屋前,他突然停下腳步。「或許,我純粹被水蜜桃粉嫩的外表給迷惑了。」說完又自己開始笑起來。
只有綉治發現,趁大家沒注意從修之手中接過字條。
火車上,綉治攤開筆記本放在圓滾的水蜜桃上面,飛快記下腦中的想法。「在夏季想像秋季的哀愁」。俯身時可以聞到水蜜桃香甜的氣味。等回到家,綉治咬了一口,但是水蜜桃味道苦澀,果核甚至已經褐腐。哥哥馬上吐掉,「水蜜桃果然還是內地的好吃。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回來。」
「外表明明看起來一樣的鮮美。」綉治覺得可惜。「哥哥,現在不是放暑假嗎?你們為什麼還要去台北?」
「修之的醫學部還有事要忙。我呢,只是找藉口離開沉悶的北港而已。」良文調皮地眨眼,綉治生氣地捶他的肚子。
「妳有機會一定要來台北看看,妳來了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哥哥要下女在後庭挖個洞把水蜜桃全埋進去,螞蟻卻有著肉食動物的敏銳度,馬上湧上土丘,彷彿泥團在蠕動。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