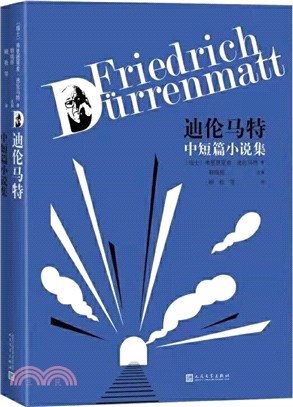迪倫馬特中短篇小說集(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狄倫馬特在喜劇創作上享譽世界,在小說創作上也很有建樹,特別是其獨闢蹊徑的偵探小說可以說在世界文壇上一枝獨秀。《隧道》(1952)、《嫌疑》(1953)、《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拋錨》(1955)、《承諾》(1958)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讀者的喜愛。
在同代德語作家中,狄倫馬特是很幸運的,由於他的國家的特殊地位,他的家鄉沒有遭受過納粹鐵蹄的蹂躪,他的精神沒有受過法西斯奴役的創傷。他幾乎一直生活在伯恩州比勒湖畔的諾伊堡。從這個靜謐的田園裡冷靜而批判地觀察著這個世界的“喜劇”,又以犀利的喜劇、小說、廣播劇、雜文等藝術形式將他那富有想像力的,但卻始終尖銳刻薄的詛咒拋投到讀者之中,就是要以驚世駭俗的方式將他們從那可笑可悲的日常現實中喚醒。他的作品不是自我的表現,而更多是力圖呈現給這個令人沮喪的世界一面鏡子,一面怪誕扭曲的鏡子,要以此來認識它。他的全部作品都圍繞著這個主題。與他同代作家不同,他的文學表現自始至終都滲透著一種歷史悲觀主義色彩,正如他所說的,“我認為,人們不可能完全認同一個曾經存在的、現在存在的和將來會存在的社會,而始終必然會以某種方式採取反對的態度。反對是文學藝術的事,而反對需要人,因為只有在
與別人的對話中,才會有事物、思想的繼續發展。”
作者簡介
狄倫馬特(1921-1990), 瑞士戲劇家、小說家。代表作有戲劇《老婦還鄉》《羅慕路斯大帝》《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小說《隧道》《法官和他的劊子手》《諾言》等。
選編者:
韓瑞祥 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德語文學翻譯家,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譯介有卡夫卡、施尼茨勒、伯恩哈德、巴赫曼、彼得·漢德克等奧地利作家的作品。
譯者:
顧牧 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譯有巴赫曼的《曼哈頓的好上帝》、彼得·漢德克的《無欲的悲歌》、施尼茨勒的《貝恩哈迪教授》等。
葉廷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德語文學翻譯家,原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會長。在卡夫卡、狄倫馬特等譯介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
名人/編輯推薦
弗裡德裡希·狄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是瑞士現代文學的偉大旗手,是戰後德語文學*優秀的經典作家之一,被譽為繼布萊希特之後“*傑出的德語戲劇家”。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戲劇和小說創作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為德語當代文學贏得了令人敬仰的世界聲譽。
序
前言
弗裡德裡希·狄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是瑞士現代文學的偉大旗手,是戰後德語文學最優秀的經典作家之一,被譽為繼布萊希特之後“最傑出的德語戲劇家”。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戲劇和小說創作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為德語當代文學贏得了令人敬仰的世界聲譽。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和學者瓦爾特·因斯曾經這樣讚譽說:狄倫馬特的喜劇“是在虛構,需要的是能夠表現對環境那無可挽回的東西的想像和出人意料的睿智,……是在創造風格”;他的喜劇“不是為現存的世界加磚添瓦,而是展現著那基石上的千瘡百孔;它所追求的不是對存在的證明,而是要採用誇張性的模仿去諷刺,去嘲弄,去重新創造;它表現著變化的東西,而自身同樣處於變化之中”。因斯的這段話不僅一針見血地勾畫出狄倫馬特喜劇創作的特點,也十分貼切地揭示出其小說創作的風格。狄倫馬特的文學創作是虛構、想像和睿智的藝術結合,而不是對生存環境現實主義的直接反映;他的文學藝術不是對現實的褒揚,而是立足於我行我素毫不掩飾的揭示,即“良心”的寫照;他借助怪誕而創新的多樣化藝術手段來表現變化的、引起痛苦和不安的現實生存與社會主題。他的藝術風格別開生面,
獨樹一幟,堪稱典範。
狄倫馬特於1921年1月5日生於伯恩市附近一個叫柯諾芬根的村莊。父親是新教神父。像他的祖輩一樣,他幾乎在伯恩家鄉度過了他的一生。對他來說,童年的家鄉既是一個祥和之地,又是一個幽靈似的田園。中學時期,他就開始閱讀表現主義作家凱澤和卡夫卡的作品,同時也對叔本華和尼采情有獨鍾。1941年,他進入蘇黎世大學學習哲學、自然科學和日爾曼語言文學,主攻克爾凱郭爾和柏拉圖哲學。與此同時,他
也開始研究阿裡斯托芬與古希臘的悲劇詩人。
狄倫馬特是在卡夫卡和凱澤的影響下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短篇小說《老人》是他發表的第一部作品。1946年冬,他的第一本劇作《聖經如是說》問世。創作初期,狄倫馬特為卡巴萊劇場寫了許多卡巴萊小品劇,因此也度過了初期作為自由作家生存的
困境。這些成功的卡巴萊小品劇可以被看作是後來喜劇的雛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伴隨著瑞士經濟奇跡的出現,狄倫馬特的文學創作也開始脫穎而出。作為戲劇作家的實驗場地,他首先發表了一系列廣播劇,先後獲得了德國戰爭盲人廣播劇獎(1955)和義大利國家獎(1956)。與此同時,他開始創作偵探小說。狄倫馬特獨具一格的偵探小說也是其在德語文壇上獨領風騷的創舉,與其戲劇創作競相爭豔,相得益彰。膾炙人口的《法官和他的劊子手》(1951)和《嫌疑》(1953)就是這個時期的傑作。從這個時期開始,狄倫馬特在創作實踐的基礎上也著手探討戲劇理論問題。1954年發表的《戲劇問題》奠定了這位劇作家一生所遵循的立足於社會觀察的戲劇創作思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是狄倫馬特喜劇創作的高潮。如果說《羅慕路斯大帝》(1948)克服了初期的表現主義傾向而預先實踐了他後來的喜劇理論,那麼《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0)、《天使來到巴比倫》(1953)等則是其開始探討和認識布萊希特戲劇創作的結晶。前者以極其誇張的漫畫形式展現出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死亡之舞,也奠定了他在聯邦德國戲劇舞臺上的成功。可以說,他日臻成熟的喜
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戰後德國重建時期德語戲劇的空白。
1955年,狄倫馬特發表了為他帶來世界聲譽的“悲喜劇”《老婦還鄉》,從而使他的喜劇“模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與傳統的喜劇不同,突如其來的轉折和怪誕的風格和表現手段構成了狄倫馬特喜劇表現的核心和與眾不同的特色。《老婦還鄉》很快就成為世界戲劇舞臺上的經典之作,深受東西方觀眾的喜愛。狄倫馬特因此先後獲得曼海姆席勒獎和瑞士席勒基金會大獎。《老婦還鄉》把狄倫馬特迄今在作品中所表現的社會批判昇華到對西方社會制度在道德上的控訴。喜劇《物理學家》(1962)是狄倫馬特喜劇創作的又一個高潮,是這個時期德語舞臺上上演最多的劇碼之一。它與後來的《流星》(1965)和處女作《聖經如是說》的新版《再洗禮派教徒》(1966)等徹底確立了
狄倫馬特在世界戲劇舞臺上的重要地位。
從六十年代末以後,狄倫馬特趨向於散雜文的創作,越來越關注社會政治問題,文化批評越發尖銳。雜文集《關於以色列的雜文》(1976)收錄了作者這個時期許多很有認識價值的政論和文化批評檄文。與此同時,狄倫馬特更多地投身於喜劇舞臺實踐中,他先後擔任巴塞爾和蘇黎世劇院藝術顧問,改編和導演了自己早期的喜劇以及莎士比
亞、斯特林堡、歌德等的劇作。
狄倫馬特在喜劇創作上享譽世界,在小說創作上也很有建樹,特別是其獨闢蹊徑的偵探小說可以說在世界文壇上一枝獨秀。《隧道》(1952)、《嫌疑》(1953)、《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拋錨》(1955)、《承諾》(1958)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讀者的喜愛。
在同代德語作家中,狄倫馬特是很幸運的,由於他的國家的特殊地位,他的家鄉沒有遭受過納粹鐵蹄的蹂躪,他的精神沒有受過法西斯奴役的創傷。他幾乎一直生活在伯恩州比勒湖畔的諾伊堡。從這個靜謐的田園裡冷靜而批判地觀察著這個世界的“喜劇”,又以犀利的喜劇、小說、廣播劇、雜文等藝術形式將他那富有想像力的,但卻始終尖銳刻薄的詛咒拋投到讀者之中,就是要以驚世駭俗的方式將他們從那可笑可悲的日常現實中喚醒。他的作品不是自我的表現,而更多是力圖呈現給這個令人沮喪的世界一面鏡子,一面怪誕扭曲的鏡子,要以此來認識它。他的全部作品都圍繞著這個主題。與他同代作家不同,他的文學表現自始至終都滲透著一種歷史悲觀主義色彩,正如他所說的,“我認為,人們不可能完全認同一個曾經存在的、現在存在的和將來會存在的社會,而始終必然會以某種方式採取反對的態度。反對是文學藝術的事,而反對需要人,因為只有在
與別人的對話中,才會有事物、思想的繼續發展。”
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推出狄倫馬特的作品,意在比較系統地向我國讀者介紹這位
獨具風格的瑞士德語作家。本書選編了狄倫馬特創作的十二篇作品。
在狄倫馬特的文學創作中,中短篇小說同樣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其喜劇和偵探小說共同體現了作者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和審美意識,一直深受世界各地讀者喜愛。他的許多中短篇小說,無論從主題還是表現手法上都與其喜劇和偵探小說相互輝映,相
得益彰,形成了作者渾然一體的藝術追求。
狄倫馬特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被他奉為大師的卡夫卡的影響,尤其是收集在短篇小說集《城》(1952)中的早期作品如同一個個卡夫卡式的寓言,其中包括膾炙人口的《陷阱》(1946)、《城》(1947)和《隧道》(1952)等。這些帶有悲觀主義色彩的小說以怪誕的想像、真實的細節描寫、冷漠而簡潔的語言表述、灰色的幽默,寓言式地表現出一個“成為巨大問號的世界”。狄倫馬特稱這樣的表現是對其喜劇創作的
“鋪墊”和“前哨”。
《陷阱》是狄倫馬特的短篇成名作,它講述的是一個交織於現實和夢境中的神奇故事。可以說,狄倫馬特在這裡採用了一種近乎融表現主義與超現實主義於一體的藝術手法,描寫了一個虛無主義者怪誕離奇的心路歷程。在“野獸”與“獵人”的角色遊戲中,小說敘述者“我”與這位虛無主義者邂逅。他們一見如故,情投意合,於是,敘述者“我”就成了“他”傾吐心聲的知己,“他”的命運的見證者,一個“雙贏人”的故事的講述者。這個被敘述的“他”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冷酷無情,讓人捉摸不透,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處不佈滿陷阱,生存如同一個無法逃脫的天羅地網,他覺得自己就像是被“追捕和獵殺的野獸”。他恐懼,他絕望,他感到自己“像只昆蟲一樣陌生”,在離奇古怪的黑暗中不斷地穿過令人恐懼的“空蕩蕩的時間和空間”。於是他不由自主地沉浸於自殺的渴望中;他玩各種死亡遊戲,“研究各種死亡方式”。他把自己的墮落和對虛無與死亡的渴望看成是與“陷入地獄的全人類共命運”。對他來說,時間就像是惡魔,空間就像是地獄。他墜入了“世界的深淵”。最後在虛無的絕望中,他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說《陷阱》是狄倫馬特所奉行的“怪誕化表現手法”最初的嘗試,或多或少帶有存在主義影響的蛛絲馬跡。主人
公撲朔迷離的命運成為一切現存價值體系無望和崩潰的鏡像。
194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城》無疑是卡夫卡創作風格影響的一個結晶,與小說《城堡》頗有同工異曲之妙。像《城堡》一樣,狄倫馬特筆下的“城”既不是具體的城市,也不是具體的國家,而只是一個抽象的象徵物。它象徵著一個虛幻混亂的世界,象徵著一種給人們帶來災難不可捉摸的現實;“城”是一個迷宮式的生存隱喻。如果說《城堡》中的主人公K面對近在咫尺的城堡可望而不可即,至死也進不去的話,那麼《城》中的敘事者“我”則身臨其境,親身感受著一個離奇的迷宮世界。在這裡,“城”成為一個不可動搖難以捉摸的權力的堡壘,“十分完美”。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動不動地坐在黑暗裡,面面相覷,瞪大眼睛,一聲不吭”。敘述者只有通過感知“城”那無比強大的權力和魔力,才會認識到自己的無所適從和“城”的“完美”。他在這裡所經歷的“完美”無非是個體無望的孤獨和生存的困惑。他在其中接受了一個看守囚犯的差事,卻弄不明白自己是看守還是囚犯,因為在這監獄裡,囚犯與看守在表面上毫無區別,周圍的一切都似真似幻,陰森恐怖。在小說《城》裡,狄倫馬特著力描寫的,不是“城”這個象徵物本身,而是“我”對它的切身體驗。“我”進入這“城”裡,好像進入了一個魔幻世界,出現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突如其來的、不合邏輯的、稀奇古怪的、驚心動魄的。而“我”身陷其中,只有迷茫和困惑。像《城堡》裡的K一樣,“我”在“城”製造的迷
宮裡一籌莫展,始終感受著地獄般的生存,忍受著荒誕的煎熬。
寓言小說《隧道》是狄倫馬特早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一篇承上啟下的傑作,在狄倫馬特的整個藝術創作中佔有特殊地位,亦是世界短篇小說經典之作。可以說,伴隨著《隧道》的問世,作者開始克服了早期小說表現的悲觀主義色彩,從而轉向採用反諷的喜劇手法表現那令人可怕,甚至怪誕離奇的東西。小說講述的是一列平平常常行駛的火車非同尋常地進入一個看不到盡頭的隧洞裡,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發現了人們面臨的可怕危險。他越來越焦慮不安,然而,這不祥的徵兆似乎沒有引起一個乘客的注意。當失去控制的火車越來越快地衝向那黑暗的深淵時,列車長絕望地問這年輕人該怎麼辦,年輕人則回答說:“什麼也不辦。”在這裡,黑暗的隧洞成為生存危機的象徵;衝向黑暗的火車則會自然而然地喚起讀者對世界末日的聯想。可當危機來臨時,人們依然把自己封閉在那平安祥和的現實中,不願意看到所面臨的災難。《隧道》的主人公是一個典型的狄倫馬特式的喜劇人物:如果說他之前為了抵禦那令人可怕的東西而可笑地堵塞住了自己全部的感知器官的話,那麼當他直接面對這荒誕的事件時,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去嘗試註定毫無意義的拯救,甚至“輕鬆地”接受了這種他好像等待已久的可能,因為在他看來,無論一個人怎樣試圖去努力,都無法挽救這可怕的現實,正如作者在喜劇《物理學家》裡所說的,面對一個悲哀荒誕的生存現實,“個人試圖去解決關係到大家的事,必然會失敗的”。狄倫馬特在這裡用寫實的手法把習以為常的現實荒誕化,寓言式地勾畫出荒誕的真實、平淡的可怕。評論家常常把小說《隧道》看作是一個典型的卡
夫卡式的寓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狄倫馬特喜劇和偵探小說創作的盛期,這個時期鮮有中短篇小說問世,值得一提的是被視為中篇傑作的《拋錨》,後來又相繼被改編成廣播劇和舞臺劇。這篇小說既有濃厚的偵探小說因素,又像是一出敘事喜劇,同時也與卡夫卡的小說《審判》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拋錨》是“一個仍然可能的故事”,像作者同年發表的著名喜劇《老婦還鄉》一樣,它表現的主題同樣是社會正義和罪責。小說主人公特拉普斯因為半路上車子拋錨,偶然陷入一個由四個退休法官、辯護律師、檢察官和劊子手把玩的審判遊戲中。他要在其中充當被告角色。於是,他身不由己地進入了這個所謂的正義空間,最終成為這個所謂的正義遊戲的犧牲品,命運的玩偶。這個荒誕的審判遊戲促使無辜的特拉普斯最終承認了並非是他犯下的謀殺罪,他的罪責就在於他的上司由於對特拉普斯與其妻子的曖昧關係憤怒而心肌梗死。這就是狄倫馬特所說的“完美的犯罪”。特拉普斯最終被判死刑,而面對自己在“審判”中所承認的罪責,他欣然接受了這個死刑判決;“一種對於更崇高的事物、正義、罪孽和懲罰的預感襲上他的心頭”。時代的正義和罪責就這樣映現在一場荒誕的審判遊戲中。像《老婦還鄉》一樣,《拋錨》的表現充滿荒誕和悖謬,無論從結構和內容上都打上了狄倫馬特喜劇風格的烙印。作者運用象徵和反諷手法,怪誕地勾畫出了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正義”世界以及一個個活動在其中的可笑人物。這種變化莫測和荒誕不經的喜劇氛圍恰恰也體現了作者與眾不同的敘事
風格。
中篇小說《倒臺》(1971)標誌著狄倫馬特中短篇小說創作又一個新階段。它是作者繼偵探小說《承諾》(1958)後相隔十三年之久才發表的一篇敘事作品,也是其唯一一篇採用喜劇式的辛辣嘲諷,直接抨擊極權政治的小說。這篇小說的問世與作者所經歷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他1965年遊歷蘇聯的親身感受和對六十年代末發生在歐洲的學生運動的態度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基調。這一時期,狄倫馬特也發表了一些著名的政論雜文,直言不諱地表明瞭自己的政治態度。小說《倒臺》描寫的是一個圍繞著政治權力的爭鬥以及國家首腦倒臺的故事。整個故事情節頗有戲劇性地發生在一個政治局委員會的會議室裡。在這裡,一場國家最高權力者的盛會變成了各種政治“小丑”滑稽表演的舞臺,演繹出了一幕荒唐離奇的政治鬧劇。小說中,參與爭鬥的政客們都沒有姓名,而只有用字母稱謂的符號;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不是簡單的人與人之爭,而是代表政治權力的符號之間骯髒齷齪的抗衡。從B到N部長們都悉數到場,只有“O部長”缺席。於是,大家圍繞著“O部長”缺席的猜疑導致了各種各樣的陰謀和誹謗,針鋒相對,爾虞我詐。在暗流湧動的較量中,有一種力量攫取了每個參與者的心靈,那就是令人窒息的恐懼。當兩個部長被請出會議室成為可能的清除物件時,你死我活的角逐最終便升級為逼迫“A主席”下臺,並且以群魔亂舞的方式實現了政治權力的更替。可就在這時,只是姍姍來遲的“O部長”突然出現在會場上,這場荒唐的鬧劇便隨之收場了。《倒臺》是一個結構奇妙意蘊深邃的政治寓言,喜劇式的敘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一個極權政體的腐敗、可
笑和荒謬。小說《倒臺》體現了狄倫馬特這個時期所主張的“政治喜劇”原則。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是狄倫馬特中短篇小說創作後期。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包括《阿布·卡尼發和阿南·本·大衛》(1975)、《史密斯兒》(1976)、《皮提亞之死》(1976)、《彌諾陶洛斯》(1985)和《委託》(1986)等。狄倫馬特後期的作品在主題和風格上進一步開拓和深化了早期作品如《陷阱》《城》等對“迷宮”母體的表現。“迷宮”成為作者後期藝術創作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他所說的“迷宮戲劇原則”。這個時期的作品大多都擁有一個共同特徵:世界是迷宮,生存是迷宮,現實是迷宮。上面所提及的前四篇作品可以說是綻放異彩的“迷宮”寓言,作者在其中借用了各種歷史神話,從不同的視角寓言式地展現出“迷宮”所蘊含的現實意義。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稱之為“敘事詩”的短篇小說《彌諾陶洛斯》。古希臘神話人物彌諾陶洛斯是歐洲文學和藝術一個經久不衰的母體。狄倫馬特在這篇小說中賦予這個神話人物及其迷宮一個非同尋常的藝術圖像。在他的筆下,彌諾陶洛斯從一個食人的怪物變成了一個捉摸不透的環境的犧牲品,一個困惑絕望的生存象徵。小說從想成為人的彌諾陶洛斯的視角出發,描寫了主人公在由鏡子構成的迷宮裡追求生存的可悲命運,自然而然地讓讀者在一個神話人物身上看到了現代人的影子。實際上,這種借古喻今的寓言形式最終要追問的就是
現實生存中仁愛和人性的可能。
中篇小說《委託》所描寫的世界同樣呈現為一個誰也無法逃脫的迷宮。精神病科醫生蘭貝爾特委託女電影製作人F,要她去弄清他失蹤於荒漠的妻子緹娜可能遭到殺害的真相。F本來打算製作一部地球紀錄片。於是F接受了委託,踏上了尋找真相的征程,然而自己卻被捲入了這個錯綜交織荒誕離奇的迷宮故事中。隨著情節的展開,這一切似乎都變得沒有可能,F既不可能找到個體的認同,也不可能製作出一部地球紀錄片。F的朋友邏輯學家D告訴F,“我”僅僅是一種想像,是“一個由經歷和回憶碎片構成的聚合,就如同一堆最底層的葉片早已變成腐殖質的樹葉”。當D和F根據緹娜的日記記載討論這個患有抑鬱症的女人是不是因為她覺得受到別人觀察而逃走時,D想像出一種觀察的辯證哲學,被理解為決定自然、文化和政治的準則,受到人需要為那毫無意義的東西賦予意義的欲望所驅使。F前往荒漠之後,似乎弄清了一些真相,遭到殺害的人並非是緹娜,而是一個名叫索爾森的北歐女記者。F在探尋真相的過程中也險些遭到這樣的厄運。而被認為已經死去的緹娜最終則從藏匿的地方回來了。小說《委託》描寫的是一個懸疑重重,甚至有點晦澀的故事,敘事撲朔迷離,錯落有致,充滿神奇的張力。表面上看,它像一個偵探故事,但實際上卻飽含無比廣闊的敘事意境和底蘊;在作者精心構思的斷片式的敘事流中,個體任人擺佈的命運與充滿災難和恐怖的世界迷宮彼此交織,相互輝映,形成了一個萬花筒似的敘事圖像和複雜的命運鏡像:“我就是這樣的感覺,面前始終是一片空蕩蕩的景象,驅使我朝前的是命運。命運在我的身後。生命正是如此,顛倒、殘忍,讓人難以忍受。”這是小說開篇引用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名言,
其敘事用意不言而喻。
總而言之,狄倫馬特創作的中短篇小說雖然篇幅不是很多,但風格獨特,異彩紛呈,與其舉世矚目的喜劇和偵探小說共同鑄就了作者在德語當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成為當經世界文壇上備受讀者喜愛的經典之作,值得一讀。我們也希望讀者能從這本《狄倫馬特中短篇小說集》中獲得閱讀的愉悅,並有所借鑒和受益。由於水準有限,選
編和翻譯疏漏在所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韓瑞祥
2020年2月於北京
目次
目次
前言/韓瑞祥
陷阱/顧牧譯
城/顧牧譯
狗/顧牧譯
隧道/葉廷芳譯
一個看守的筆記/顧牧譯
拋錨/余楊譯
史密斯兒/顧牧譯
倒臺/顧牧譯
阿布·卡尼發和阿南·本·大衛/顧牧譯
皮提亞之死/顧牧譯
彌諾陶洛斯/顧牧譯
委託/顧牧譯
書摘/試閱
城
顧牧 譯
此文出自一名看守的手稿,由市立圖書館一位助理圖書館員整理出版。該手稿共十五卷,標題為《對佈局的思考》,此文為該手稿開頭部分,手稿已在一場大火中燒毀。
每到漫漫長夜降臨,風被攆起,哀號著在大地上亂竄,我就仿佛又看到那座城,依舊是那個清晨在冬日陽光中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樣子。城鋪展在河邊,河水從臨近的雪山流出後,悄無聲息地從房屋下方的深谷中蜿蜒流過,畫出一個奇特的8字,只在西邊有個開口,城市的形狀也就此確定。但那時,小丘後的高山被一層繚繞的輕雲遮蔽,看上去很遠,對人並不構成威脅。城市美極了,晨曦微露之時,光就像有溫度的金子一般穿透屋牆。但我每想起當時的畫面,卻還是感到恐懼,因為走近城市的時候,它的光環也在消退,等到城將我包裹,我便陷入了恐懼的汪洋。城市上方懸著有毒的霧氣,碾碎生命的種子,讓我無法呼吸。同時,我被一種感覺折磨著,就好像自己闖進了一片禁止外來人入內的區域,每走一步,都是在破壞某項秘密的法律。我四處亂走,被沉重的夢境驅趕著,被城市追攆著。這座城就是要折磨從遠方來它這裡尋找落腳之地的人,我察覺到它的興致勃勃,因為它完美、不妥協。從人類有記憶以來,它就沒有改變過,沒有房子消失,也沒有房子新增,建築物沒有分毫改變,也不受時代影響。這裡的街巷不像其他老城那樣曲曲彎彎,而是依照固定的規劃修成筆直的,全都一樣,以至於看上去仿佛沒有盡頭。但街巷並不能給人自由,低矮的房檐讓人走在建築物下的時候不得不低頭彎腰,人因此在城中隱形,也是如此才被這座城市接納。我注意到這裡的人走在街巷中時都小心翼翼,拖著緩慢的步子。他們沉默寡言,像自己生活的城市一樣自我封閉,就算是想跟他們匆匆地隨便聊幾句都很難得,即便是真的聊了,他們也言辭閃爍,似乎是因為缺乏信任,所以不能對陌生人敞開心扉。想要進到這些人的家裡,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坐在那些黑暗的房間裡,一動不動,大張著雙眼,一言不發。在他們身下,一些深深隱藏在表層之下的最醜陋的東西驅動著他們的本性。這一切都隱秘而黑暗,讓我們望而卻步。沒有人知道饑餓為何物,這裡既沒有窮人,也沒有富人,沒有人無事可做,但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兒童的嬉笑聲。城沉默地抱住我,石頭面孔的眼神空洞。黑暗像人與人之間的黯淡疏離,懸在城市上空,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去點亮這片黑暗。我的生命沒有意義,城會丟棄它不需要的一切,它蔑視一切的多餘。它就靜靜地盤踞在巖石之上,接受綠色河水從各個方向的衝刷。河水不斷從旁邊流過,只在春天會偶爾漲高,淹沒城市下方靠近河岸的那些房屋。
想要做出兼顧我們天性的預防措施,只需要看一下痛苦的強度就可以。我們總是需要一個能將自己藏起來的比較安全的所在,哪怕那地方只存在於睡夢中,而這後一種,只有現實生活中處於最下層的地牢才能將它從我們手中奪走。我最感激的是自己的房間,這是我能夠尋到庇護的地方。房間在城東郊的河對岸,那個地方已經不被算作城的組成部分。在那裡落腳的都是些異鄉人,但這些人之間互不往來,為的是不引起管理機構的注意。那些年,有很多人失蹤,我們不知道這些人的下落。有幾個人倒是號稱自己知道,說他們被市政府投進了大牢,但關於這些風言風語,我從來也沒聽到過具體的說法,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大監獄在什麼地方。我的房間是一棟出租屋的閣樓,這棟出租屋跟城郊的其他房屋沒有什麼區別。房間裡有一半的牆都是傾斜的,牆很高,北邊和東邊各有一個凹進去的地方,那裡是窗戶。靠著西邊那面高大傾斜的牆放著床,爐子旁邊是灶臺,房間裡還有兩把椅子,一張桌子。牆上被我畫了畫,畫不大,但是時間久了,也就蓋滿了牆和天花板。就連從房間正中穿過的煙囪,都被我從上到下畫滿了各種人物。我畫的是那些不安定歲月裡的事,特別是人類的那些大的冒險。等到沒有地方畫了,我就開始一幅幅修改那些畫。有的時候,我也會被一陣無名火指使著,將其中一幅畫從牆上刮掉,然後重新畫一遍,這都是我在百無聊賴時的荒唐舉動。桌子上放著紙,因為我經常寫東西,多半都是抨擊這座城市的一些沒什麼用的傳單。桌子上還放著一盞銅燈(垃圾堆裡找到的),裡麵點著一根蠟燭,因為白天光線也很暗。但是,我從來沒有仔細研究過我自己住的這棟樓。儘管房子從外面看著是新的,但是裡面卻又破又舊,樓梯也都在黑暗中。我從來沒在這棟樓裡見過其他人,雖然房門上寫著很多名字,其中還包括市政府的一個秘書。只有一次,我按下一扇門的把手,那扇門沒有鎖,門後是一條走廊,兩邊兩排房門,我覺得似乎從遠處傳來沉悶的說話聲,於是馬上縮回來,回到自己的房間裡。這棟樓是屬於這座城的,因為經常有市政府的工作人員來,但是他們從來也不要求我付租金,就好像我的窮是不言而喻的。這些人一舉一動都靜悄悄的,戴著奇怪的毛皮帽子,穿著高筒靴,而且每次來的人都不一樣。他們說這棟樓是危房,假如不是考慮到城郊住房緊缺的問題,市裡本應該把它拆掉。有時,也會有穿著白色厚外套,胳膊下夾著紙卷的男人過來,他們一言不發地丈量我的房間,然後用尖尖的鋼筆在圖紙上寫寫畫畫,一忙幾個小時。但是他們並不多事,從沒問過我的來歷。他們只進我的房間,從來沒有去過樓裡的其他房間,我從窗戶能夠看到他們從街上直接上樓到我這裡來,等到結束在我房間裡的工作,就會離開這棟房子。白天的大部分時候,我都待在朝東的窗戶邊上,從那裡看著外面那條大馬路。早晨,農夫駕著車離開農莊,從這裡往集市上去。他們一動不動地坐在車上愣神,巨大的車輪比車和車上的人高出許多,輻條的影子不斷從人身上掠過。有時,農夫會跟套在車前的牛說上幾句話。路上經常也會有戴鐐銬的犯人經過,旁邊跟著職位不高的守衛,小臉蠟黃,手裡揮著巨大的鞭子,如果看到這些人,我會一連好幾天不再朝窗外看。最讓我害怕的還是一個被押著從馬路上走過,將要死在某個地方的死刑犯。他被反綁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固定在一輛長條形的木車上,輪子是不很圓的木盤,所以車子走在馬路上的時候,會搖晃得很奇怪。劊子手走在車前面,穿著紅色的外套,戴著黃色的面罩,像背十字架一樣背著他的刀。法官排成長長的,黑乎乎的一列列,沉默地走著。死刑犯枯瘦,他用某種外語大聲唱著一首曲子單調的歌,這首歌在我耳邊久久不去,讓我感到異常憂傷。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