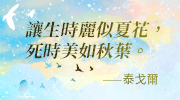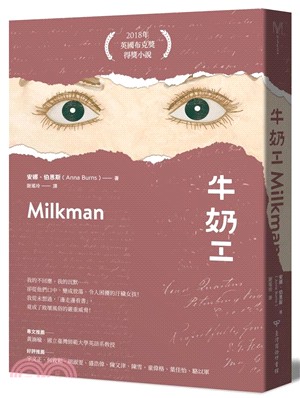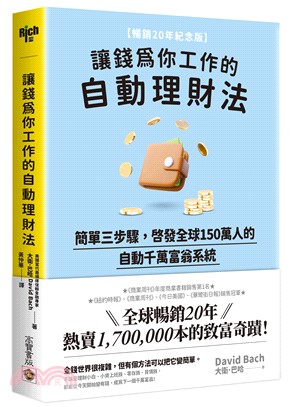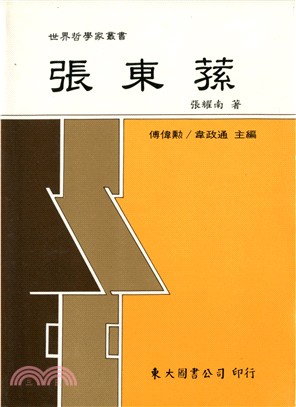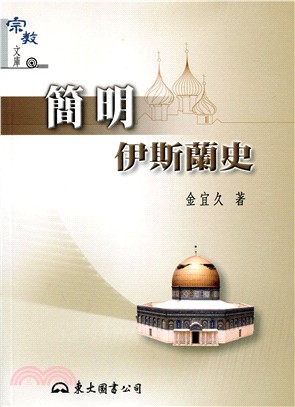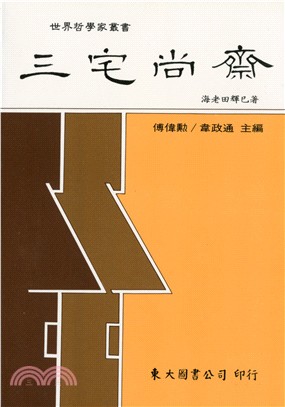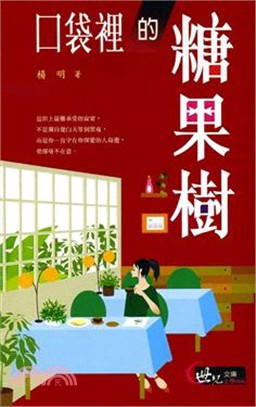商品簡介
「只有那些確切活過的瞬間,才是生命真正的價值所在。」
榮獲英國非虛構寫作最高榮譽山謬.強森獎(Samuel Johnson Prize)
加拿大人類學者、作家、探險家 韋德‧戴維斯
歷經十年研究,實地走訪喜馬拉雅山區,遍讀六百餘本相關著作、訪談相關人士寫成
以二十世紀初一戰後英國的三次聖母峰史詩征途為主軸
結合知名登山家個人傳記故事 、戰爭史、帝國史、山岳文學、探險文學
深刻重現人類與聖母峰交會的壯闊史詩
伍元和|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江秀真|台灣福爾摩莎山域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徐如林|山林文學家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雪羊視界|山岳攝影師
游旨价|台大森林系博士、《通往世界的植物》作者
董威言|城市山人 Mountain Urbanite
詹宏志|作家
詹喬愉 Tri Fish(三條魚)|新生代登山家
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公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謝旺霖|作家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推薦
「因為山就在那裡。」
在經歷一戰的震撼與摧殘後,以留下此名句的馬洛里為代表的一代登山菁英們,
在英國舉國期盼下飛越半個地球,深入亞洲內陸,費盡心力甚至犧牲生命,
只為攀登上那座從未有人登頂的世界最高峰──聖母峰。
而最終馬洛里在聖母峰頂的消失,更成為了二十世紀登山界的最大謎團──他是否為聖母峰登頂第一人?
加拿大人類學者、探險家韋德.戴維斯歷經十年研究,
實地走訪喜馬拉雅山區,遍讀六百餘本相關著作,訪談相關人士,
記下1921、1922、1924年英國聖母峰三次遠征始末,以及一代登山家們的傲然身影與心靈如何養成。
即使功敗垂成,三場遠征仍創下人類登山史上最偉大的紀錄。
本書想探究的,並非馬洛里是否登頂,而是究竟是什麼讓這群登山家寧可犧牲也要奮力攀進,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各界讚譽】
誠如書名,書頁從一戰,再轉入大英帝國和圖博政府紛爭,最後才帶入遠征行程……不得不說作者學識淵博,考據引證相當詳盡清晰,把故事說得娓娓動聽,引人入勝。在讀畢全書後,我才驚覺這不就是歷史重演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情節嗎?聖母峰是座特洛伊,希臘遠征軍裡英雄們圍城十年,而代價是雙方一場又一場的悲劇啊!
――伍元和,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攀登聖母峰到底需要準備什麼?前置作業攸關成功與否?特別是人類的首次接觸,從龐大的人力、物力到細膩的心思,甚至登山者的博學素養與當地文化宗教等磨合、發酵,勾勒出一幅幅豐富且珍貴的抽象畫,人在大自然裡如何渺小?又為何透過攀登它們能讓人類的心變得偉大?看真正的世界第一人――馬洛里與他們的團隊,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帶著傷痕累累的靈魂繼續追尋著聖母峰。
透過歷史長河從源頭到流經之處所留下的蛛絲馬跡……正如八千公尺高峰任何一面峭壁的形成至少得千萬年,能夠攀爬在上何其有幸!即使身心俱疲,靈魂卻因此被撫慰。現代,當世界高峰變成幾個小時的速攀,而非幾個月的走讀,這途中我們所失去的身心靈體悟,將遠遠超過所獲得的。閱讀此書,你可以從不同的面向觀看攀登聖母峰的實質意義與追求的價值。
――江秀真,台灣福爾摩莎山域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聽到聖母峰,這個字眼讓我腦海中浮現那座岩雪山體,穿越了一百年的攀登歷史。它是地球表面上的最高點,攀登者的心之殿堂。在我2017年第一次前往尼泊爾攀登時,我先到了位於南崎巴札(Namche Bazaar,標高三四四〇公尺)的一個村落,那是山區裡最熱鬧的村落。我來到這地方的日子,還不在攀登健行的季節裡,沿途穿梭於揹著貨物及趕牛的當地人之間,各個都為了季節來臨忙碌整備,滿頭大汗。懶散的狗兒偶而抬頭看看我們這些散客,如舊有的五峰旗翩然在沿途的吊橋上隨意放鬆。陰暗而蕭瑟冷清的村落裡,高點有一座聖母峰博物館,直直面對著遠方聖母峰,丹增·諾蓋銅像拿著一支冰斧聳立在那邊,而聖母峰在灰暗下若隱若現,充滿神祕感。那是我真正與祂的初識,令人肅然起敬,卻也讓我閉鎖著眉頭。面對著不久的未來,我將貼近祂的懷中,命運勾勒出一股致命的引力,在我這代中深埋於幽閉光環下的崇高地位。短短的初次見面,在離去時又不知如何說起告別,雖然還無法立即吸引我趨前去敲開祂的大門,但我知道不遠了。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山靜默不語,故事卻從涉足其間的生命中蔓生而出。順著那生於冰面、石面、土表乃至樹幹上的翠綠,一脈輕撫到它的基部,這才發現:故事的根,從整個大地吸取養分,織成一片綿密的大網。
關於聖母峰的首登,英國做為一個掙扎著從戰爭廢墟中站起的老巨人,恐怕再也沒有一個國家付出的代價能出其右。
喬治.馬洛里經典的一句:「因為它在那裡。」成為無數攀登之人向山緣由的詮釋,便是從那個日不落帝國落腳亞洲古文明之鄉――印度做為開端。歷經慘無人道的一次世界大戰洗禮,「首登聖母峰」成為了重振帝國雄風的精神聖杯,驅使著熬過烽火的一整代人們,在那個冰雪的絕境中,超脫生死,寫下了三次遠征的不朽史詩。
我們可以透過《靜謐的榮光》看見作者縝密的調查與精心的編排,藉由大量穿插的書信、戰史描寫與人物甚至風土刻畫,為讀者帶來「人類追尋聖母峰」的起源和過程,以及整個追尋帝國榮光的淒絕大時代,是如何催生這可歌可泣的一切。
各國政治、軍事的角力,在聖母峰的冒險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部混合著火藥與血的史詩,將冰峰染紅、把我們從攀登的純粹中拉出,使攀登者們得以再一次思考,究竟當代的我們,是為何而攀、又追尋著什麼呢?
――雪羊視界,山岳攝影師
爬山的人興許都曾閃過挑戰聖母峰的念頭,在聖母峰已可商業攀登的年代,我們隨意作著登頂夢,卻往往不知為何而夢。《靜謐的榮光》以「戰爭」為梭,編織出二十世紀初,二十六位參與聖母峰遠征的英國登山家的生平。一如書中代表人物馬洛里所言,挑戰聖母峰,只因祂在那裡,那是源於天賦的吸引,但《靜謐的榮光》也進一步揭示,這群登山家對聖母峰的企盼,亦可能源於戰後,內心深處對一個不再有戰爭的新生(或死亡)的追尋。儘管末了,你也許會將《靜謐的榮光》視為一部充滿細節的登山史。但若你能意識到,當年的登山者,面對喜馬拉雅巨峰時的無懼竟是由對戰爭的驚懼所豢養,你此生也許將不再興起登頂聖母峰的念頭,因為你明白,於人類而言,它原是一個如此特別,需要被保留的場域。其存在是為真正無畏之人的救贖與昇華,而非到此一遊的登頂。
――游旨价,台大森林系博士、《通往世界的植物》作者
是登山者引領時代,還是時代造就登山者?是登頂賦予攀登意義,還是過程的漫漫長路?迴盪世界屋脊與政局民情兩極間,小至兒女情長,大至殺戮戰場;從帝國子民心繫的巔峰舞台,到遠征隊員的內心小劇場,戰爭與榮耀、幻滅與創傷、私情與大義、沉淪與救贖,千絲萬縷的相互作用力,盡在《靜謐的榮光》。
――董威言,城市山人 Mountain Urbanite
強大且深刻,一篇集文采、歷史與希望之光於一身的動人史詩傑作。
──《泰晤士報》
出類拔萃……格局恢弘……充滿閱讀樂趣…萬花筒般的歷史記述。
──《華爾街日報》
精采絕倫,引人入勝……當代經典之作。
──《衛報》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或者說――終究會去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十九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
山岳文學的旨趣,可概分為由淺到深的三層:最基本,對歷程作一完整的報告與紀錄;進一步,能對登山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感,給予有特色的描繪;最好的境界,則是能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指出那些深刻影響我們的事事物物――地理、歷史、星辰、神話與冰、雪、風、雲……。
登山文學帶給讀者的最大滿足,是智識、感官與精神的,興奮著去知道與明白事物、渴望企及那極限與極限後的未知世界。
這個書系陸續出版的書,每一本,都期望能帶你離開地面!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
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作者簡介
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
加拿大作家、人類學家、植物學家,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的常駐探險家。他擁有哈佛人類學與生物學學位及民族植物學博士學位,自1985年出版第一本書以來,至今已出版十八部作品,包括《生命的尋路人》(The Wayfinders,繁中版於2012年由大家出版),以及曾改編電影的《毒蛇與彩虹》(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等書。著作共曾被翻譯成十六種語言,全球銷售近百萬本。
他也曾獲得許多獎項,包括探險者俱樂部最高獎「探險者獎章」、加拿大皇家地理學會金獎、因植物學發現而獲得的大衛•費爾柴爾德獎等。2012年他再次因本書獲得英國非虛構寫作最高榮譽山謬.強森獎(Samuel Johnson Prize)。
相關著作:《靜謐的榮光(上):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上下冊不分售)》《靜謐的榮光(下):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上下冊不分售)》
譯者簡介
鄭煥昇
名人/編輯推薦
死亡之前,要過足人生/The Price of Life Is Death
――馬洛里漣漪與《靜謐的榮光》
撰文=詹偉雄
到了一九一六年底,與我共舞過的每一個男孩都己經變成死人。
――黛安娜.古柏(Diana Cooper,二十世紀初倫敦貴族名媛)
一條卡其色的腿、一排三顆腦袋,每個人身體的其他部分都埋在地下,給人一種印象,彷彿他們用盡自己最後一分力,讓頭高過高漲的水位。在另一座迷你魚塘裡,唯一還能看到的是一隻還緊緊抓著步槍的手,它的隔壁池塘則被鋼盔和半顆腦袋占據,瞪大的雙眼冷冰冰看著漫得幾乎與他們同高的綠色泥漿。
――李昂.吳爾夫(Leon Wolff,美國歷史學家),摘自《置身法蘭德斯田野:一九一七戰役》(In Flanders Fields : The 1917 Campaign)
(一座)你可以從九個方向看到的山、(一座)你沒辦法從近處看見的山、(一座)高到烏兒飛過會目盲的山。
――大衛.麥當諾(David MacDonald,英國貿易代表[一九○五~一九二五])
這次的勝算是五十比一,我們是一,但我們還是會全力以赴,讓大家以我們為榮。
――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聖母峰遠征隊攀登隊長),〈致妻子茹絲的信〉
八八四八公尺高的聖母峰與其登山者的故事,主要有兩個:
二十世紀的人,鍾情於紐西蘭養蜂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與雪巴夥伴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的版本,他們兩人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那天,經由尼泊爾端的南坳路線成功登上了絕頂,而且平安下山。消息傳回倫敦已是六月二日,當日適逢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因此英國媒體延後了二十四小時才發布消息。
二十一世紀的人則偏愛失敗者的故事: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英國當時最富盛名的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帶著他來自牛津大學的年輕同伴(二十一歲)、機械整治天才(負責氧氣鋼瓶和面罩校準)――安德魯.柯明.「山帝」.爾文(Andrew Comyn “Sandy” Irvine),聯袂走向連結圖博端北坳營地與東北脊的冰雪之中。在他們永久地消失前,隊友、地質學家諾艾爾.歐德爾(Noel Odell)透過望遠鏡目睹了他們最後的身影:「小黑點在移動,另一個小黑點往上移動與第一個會合於岩壁上,⋯⋯但這個迷人的景象很快就消失了,雲層再一次包圍了它。」這是馬洛里參與的第三次聖母峰遠征隊,他與爾文的殉山,使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與英國山岳會聯手的、密集的「聖母峰行動」嘎然而止。
當然,這兩個組織的雄心並沒有終止,直到希拉瑞和諾蓋在二十九年後完成了它們發端於十九世紀末的願望。
二十一世紀的人更熱切地想記住馬洛里的故事。我們難以究其全因,但可以確認的是,這與一九九九年,馬洛里的遺體在聖母峰北壁八二三○公尺處的山麓被一支搜尋遠征隊發現有關:馬洛里與爾文是否已經成功地登頂,繼而在下山途中失足墜落?如果如此,那麼希拉瑞和諾蓋就不是前兩個登上世界絕頂的人,而是自始至終(從發現它、探勘它到征服它)都永誌不渝的「純正英國人」──馬洛里與爾文。馬洛里揣在外套懷中的護目雪鏡被當作推論的證據之一,因為唯有登頂下山臨近入夜之時,登山者才會摘下保護眼睛的重要裝備⋯⋯。有了這樣的推想,馬洛里做為一個「失敗者英雄」的故事就更完備了,短短一年,英語世界就有八本關於他的新書出版。
或者,也有其更深沉的原因,我猜測這本書的作者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也有近似於這樣的念頭與想法,也就是說:在愈來愈世俗化、消費主義主導的新世紀,許多人的內心其實渴望著仍有一個神聖的所在,得以孺慕或追尋。在後記裡,戴維斯這麼說:「為什麼在命運的那一日,他(馬洛里)理應明知自己走下去會送命,卻仍堅持著繼續前進。⋯⋯他們看多了,因此死亡再不能讓他們動彈不得。比起死,更重要的是人如何活過。」在這一層意義上,那樁將近一百年前的兩位青年的死亡,就連結上當下苦於生命意義的讀者了。事實上,如果你讀完《靜謐的榮光》,可感受到能與你共鳴的逝者,就不僅止於馬洛里和爾文,還包含著三次遠征的二十六名隊友、命喪於一次世界大戰的兩百五十萬名年輕士兵與軍官。
在此,容我來說說兩件最近所發現的兩幅畫面,它們於我,是所謂的「馬洛里漣漪」的一部分:
在我閱讀《靜謐的榮光》最後校稿、撰寫這篇導讀的時刻,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正舉行第十六輪的比賽,踢完這輪,二十支球隊將停賽六週,讓旗下球員回到母國國家隊去踢卡達舉辦的第二十二屆世界盃。這一輪的賽事,正逢英國的「追憶的星期日」(Remembrance Sunday),因此賽事開始前都有一個儀式:一名年邁的軍號手,手持沒有氣閥的銅質號角,伴隨著兩側退伍軍人護持,加上兩位(通常是)地區公職人員代表捧上罌粟花編織的紅色花圈,一齊走上球場的正中央,將花圈放置於翠綠草地致意。同時,這位老邁的號手會吹上一首名為〈最後的崗哨〉(Last Post)的樂曲,它的音高和響度全由老人的唇齒和腮幫子控制,因而不免有些力有未殆地吃緊,但這正是典禮希冀的效果:藉由樂音提引,全場要緬懷喪生於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百多萬名軍士官兵,以及昔日為國殉職的公務人員。對在場者而言,這些都是垂垂老矣的過往,滄桑不僅恰當而且合宜。烽火四年的一次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時宣布停火,英王喬治五世於隔年的白金漢宮首度舉行了紀念式,大英國協成員後續決定在每年十一月最接近十一日的星期日,於各個公眾場合舉辦儀式,而罌粟花即是大戰中西線戰場上盛開的花種,大戰中的生命在它們之間倒下,也滋潤了後起綻放的花苞。
在英超的賽場上,號手左右的兩隊隊員與當年入伍生年歲相當,知道故事的人即便每年都看到畫面,仍不免小小心驚而且悲涼: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方啟,那一年的英格蘭足球季中,就有五十萬人應召入伍,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回來。在一九一六年七月開啟、號稱一戰最慘烈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中,一名帶隊上尉威爾菲德.內維爾(Wilfred B. Nevill)將他從倫敦帶來的四顆足球分給每一排一顆,號召士兵們誰能把球踢進對面德軍的戰壕,就能獲得他的獎品。這個願望當然沒有實現,內維爾在衝鋒出去的那一刻就死了,他的身體懸掛在德軍的鐵絲網上,右手似乎要掏出一顆手榴彈拋擲,但掃射來的機槍子彈迅速了結了他。四顆足球中唯一存留的一顆,目前典藏於多佛城堡的皇家軍團博物館。
這個故事和馬洛里的關係是:馬洛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入伍成員,他也參與了英、法、德軍總共死亡超過一百四十萬人的索姆河戰役;事實上,聖母峰三次遠征隊(一九二一、二二、二四)負責登山任務的二十六名隊員中,有二十名參與過大戰。根據《靜謐的榮光》作者戴維斯透過戰地通訊與傷兵醫院鉅細靡遺紀錄(這是我視本書為非虛構類寫作「聖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所經所歷的慘絕人寰程度遠遠超過馬洛里。即便是以豪奢生活和派頭聞名的第二梯次領隊查爾斯.格蘭維爾.布魯斯(Charles Granville Bruce)准將,雙腿也在戰役中被成排的機槍子彈掃斷過。
第二幅畫面,來自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於去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辦的〈聖母峰:那些曾在那兒過的人〉(Everest: By Those Who Were There)的百年文物紀念展,當年的遠征隊是由皇家地理學會與山岳會共同組成的「聖母峰委員會」推動,雙方約好一方要搞定政治與財務,另一邊則要選派出最強的登山者。不巧一百年紀念日撞見Covid-19尾聲,山岳會挑選了幾十件重要文物放上網路,因而我有幸地看見了第二、三次遠征隊中僅次於馬洛里的重要成員――霍華.森默維爾(Howard Somervell)的一幅水彩畫。在這幅題名「從隘口龐拉所繪的聖母峰,四十五英里之外」(Everest from Pang La, 45 miles away)的水彩畫中,聖母峰交織著雪溝的黑褐山體,被一群白色的山峰和冰河簇擁著,頂上是透著水色的青空,淡淡顯著層次,近處是土黃色的圖博高原,蔓延往觀者這邊又是一片水色,也許是雲,也或許就是畫家想讓主景浮凸出來的烘托,也或許是札卡曲的河面⋯⋯。據說森默維爾都是用暗褐色的包裝紙來作畫,因為圖博一望無際的平坦地帶就是這個顏色。如果是這樣,那他僅是運用青色與白水彩,就顯影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北壁立面。
這幅畫是我見識過上千百個聖母峰影像以來,第一幅如此柔軟、飽滿詩意而又恬適愉悅的畫面,但作畫的森默維爾(由遠征隊的團體照可看出)卻是一個外型非常粗獷、一戰中開過上千台戰地手術,兩次遠征行程中都爬到比馬洛里更高處的壯漢(他被選入遠征隊的理由之一正是「壯得像牛一樣」)。為什麼這麼一位強悍的人卻有如此溫柔的表達?是我們以貌取人的刻板印象所導致的偏見,還是圖博高原的連番遠征行動,對他的靈魂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揉捏與改造?
當我讀了《靜謐的榮光》後,算是真正補充了去年觀畫時的疑問。與馬洛里同樣出身劍橋大學,森默維爾是唯一在帳篷裡和馬洛里讀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奥賽羅》與《李爾王》)劇本的成員。一次大戰的血腥記憶與遠征行程的失敗與傷亡,扭轉了他生命的軌道,一九二四年後,他留在印度創辦醫院,成為外科教授,一直到一九六一年(聖母峰被首登後八年)他才返回英國,除了短暫接任英國山岳會會長(一九六二~六五)外,森默維爾選擇以非常安靜(除了看診,就是繪畫)的方式,過完他的餘生。一九七五年逝世之後,他的兒子大衛整理父親遺物,發現一具沉甸甸的盒子,打開一看,那是一面由一九二四奧運委員會主席、有「奧運之父」之稱的法國男爵皮耶.德.古柏坦( Pierre de Coubertin)所頒贈給他的一面冬季奧運金牌,表彰的是他在二二年那次登上二六八九五英尺高點的成就。「父親生前從來沒跟我說過這事,」大衛.森默維爾告訴英國《衛報》記者說。根據山岳會紀錄,森默維爾可考的畫作有六百幅,其中一百二十六件與聖母峰遠征有關,山岳會本身收藏了三十幅。從他的畫作,讀者可以一窺聖母峰冷冽恐怖外的另一個視角,也可以想像,當年這群遠征隊成員心靈圖譜的變化是何種模樣?相較於我們這一世代的世界登山者,是我們失落得多,還是他們失落得多?
-
要完整地理解「聖母峰與馬洛里」(或人類高海拔探險史)這一棵巨型知識樹,前面所列的兩樁生活小事,只是向著光線抽長到枝枒最外面的幾株葉叢,為關心者增添一些生活的興味而已,《靜謐的榮光》的企圖當然不僅於此。韋德.戴維斯在寫作此書之前,已經是非常有名望的植物民族誌學者與人類學家,一九八六年的著作《毒蛇與彩虹》(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是一本學術意味飽滿,卻寫作生動而又有啟發性的暢銷書:
加勒比海上,與西非奴隸買賣市場有著好幾個世紀淵源的海地島,民間流行著巫毒教(Voodoo)的神祕信仰,相傳部落裡的祭司(bokor)有能力招喚出「喪屍」(Zombis,一種於人死後從墳墓中復生的「新」賤民),為出得起錢的雇主擔任苦力的工作。戴維斯和他哈佛大學的老師理查.伊文斯.舒爾茲(Richard Evans Schultes)對這個研究題材非常好奇,他們潛入海地,明查暗訪,甚至與兩位「喪屍」晤面,結果卻發現了驚人的實情:當祭師相準了目標活人後,會在他家的門檻上抹上帶有神經毒性、由河豚毒和蛤蟆毒提煉而成的粉末,經由皮膚滲入,讓此人昏迷且達到器官幾乎停止運作的類死亡狀態,接著舉辦葬禮,讓此人於眾目睽睽間下葬,然後再於夜深時分,掘開木棺,餵食這人以一種由曼陀羅植物葉萃取出的膠狀物。這種富含癲茄鹼(atropine)的天然藥物能分解之前讓人瀕死的河豚毒素,慢慢讓其復生與甦醒,但同時裡頭另含的莨菪鹼(scopolamine)與莨菪素(hyoscyamine)卻又是威力強大的致幻物質,讓服用者非常容易在外力作用下受到脅迫,祭師在喚醒「喪屍」後對其進行高強度做法,讓「喪屍」真的相信自己來到新世界,獲得了新生,也變成了賤民。
但這些恐怖的情節,卻有著彩虹般高張力的解釋意涵:在海地的鄉村地帶,這曾是一種普及的訓育系統,那些被選中的人,多半是社群中製造麻煩、無法融入群體的個體,透過「喪屍化」(Zombification),社會反而獲致平靜,而資本主義的工場(甘蔗製糖尤為大宗)於此而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毒蛇與彩虹》是戴維斯發揮其為植物民族誌學者本職學能的奇才之作,靠的是非常冒險的田野浸入和生存技巧,書評家認為「他能活著回來」就已經為著作創造了最高價值。在他另外一樁對安地斯山與亞馬遜河所作的探險旅程裡,戴維斯可以置身叢林和高地超過三年,浪跡八個國家與十五個原住民族群部落,蒐集了六千件植物標本,完成了《一條河:亞馬遜雨林中的探險與發現》( One River: 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mazon Rain Forest)這本書,《戶外》(Outside)雜誌對它的評語是:「科學與神話重疊、記憶和幻覺交織、時間變化莫測,以招牌的狂野說故事方式,將傳統的傳記寫作與拉丁美洲最強大遺產的魔幻寫實主義融為一體,最適於他選擇的弘大主題(larger than life subjects)。」此一獨特的評語,拿來判準讀者眼前的這本《靜謐的榮光》,不客氣地說――同樣精準受用。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週日版的《紐約時報》,刊出了關於喬治.馬洛里的四分之一版頭題報導,在這篇題名為〈攀登聖母峰是超人的工作〉(Climbing Mount Everest is Work for Supermen)的側寫裡,遠道渡海來北美演講的馬洛里(演講酬勞是他三次遠征期間失業時的主要收入)回答記者「為什麼要爬聖母峰?」的問題時,隨口回了一句:「因為它就在那兒(Because its there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裡,這句短語成了人人都明白,卻又難思其解的登山形而上學謎團。
然而,在一九九六年由四川成都出發,橫渡過圖博高原,途經拉薩而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六千四百公里行旅中,韋德.戴維斯卻並不買單這麼簡潔的答案。身為一位有著前述老道田野經驗的民族誌學者和人類學家,他敏感到沿途走過的巨大自然地景、針鋒相對著西方價值觀的圖博文明,以及一戰後馬洛里與遠征隊員破碎的心靈狀態(置身於邱吉爾所說「沾染了血污的新世紀」),還有日不落帝國寸瓦崩解下的集體挫敗國民意識,都流露了蛛絲馬跡,共同建構了「因為它就在那兒!」的形而下社會基礎。有了這樣的起心動念,戴維斯開展了他龐大的寫作計畫,包括兩次再度重回圖博的田野,其中一次還復刻了遠征隊由圖博高原進入東絨布冰河,抵達北坳下當年第三營的路線。在野宿於面對聖母峰東面康雄壁(Kangshung Face)的培當仁木(Pethang Ringmo)營地之時,他有無限感慨。除了腳下的高度已經高過整個北美洲,目睹整個山稜線的懾人心魄,促使他與當年「一身粗花呢獵裝」、「雪中讀著莎士比亞」的劍橋黃金世代間湧生出一股同理之心,「能文能武的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群人?拉動著他們前進的又是什麼樣的一股精神?」順著這樣的追索,戴維斯去到了英國國家檔案局、劍橋大學圖書館、帝國戰爭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以及皇家地理學會和英國山岳會卷帙浩繁的檔案庫,造訪大多數遠征隊員的後代,並獲得好幾大卷日記手稿。為了理解當年絨布寺住持札珠仁波切接待英國人時的看法,他還僱請資深翻譯將仁波切的回憶錄《南塔》譯成英文,並親自走一趟絨布寺避難中國遷居尼泊爾的法林寺;他也讀遍了所有關於聖母峰和馬洛里的經典書籍、傳記和八卦,蒐羅了劍橋菁英與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學圈(如今看來)匪夷所思的同志性愛情書與日記。
二○一二年付梓出版的《靜謐的榮光》,是「聖母峰與馬洛里」知識樹的孤峰之作,難以想像還會有另外一個作者,投注以如此龐大的知識熱忱與時間,嘗試為曾祖輩的青春歲月,尋找這樣絲絲縷縷、漂浮於喜馬拉雅天際線的幽微意義解釋。巨大的時代、巨大的地景、巨大的死亡,君臨在渺小一瞬的個人頭頂,除了昂首走去,誰還能做些什麼呢?
問題的骨幹是清楚的:為什麼在命運的那一日,馬洛里明知自己走下去會送命,卻仍堅持著繼續前進。幾個關鍵的分支提供了個人抉擇的命運背景――如卡爾.馬克思所言: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其一,是英帝國與俄羅斯在中亞的大博奕,征服聖母峰意味著地理探勘的完成與掌控,延續了自庫克船長以來聚焦於「冒險」和「發現」的國格定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九二○年代,英國有兩百萬民眾失業,外加五十萬退伍老兵漂流街頭,社會急須一個振奮人心的行動,再次凝聚帝國的向心力;其三,對於歷劫歸來的倖存者,他們在戰爭中徹底喪失了對人的信心,如何找出活著的意義?蒼蒼雪峰與圖博高原、峽谷的「神聖地景」(sacred landscape)或可協助解惑(「他們都是行走在奧祕的空間中」);第四,所有工業化國家都進入了媒體時代與商業社會,新社會迫切需要全新的故事與商品,聖母峰遠征的獨家報導「賣」給了《泰晤士報》,遠征隊「代言」的商品都對應著贊助收入,第三次遠征的主要經費甚至來自電影的「預付款」。
有了理路清楚的分析骨幹,讀起來便舒服、自然,但也許最吸引人的,是作者窮盡了洪荒之力(詳見精采萬分的「註釋書目」),重建了三次遠征隊中二十六位成員的生命史,戴維斯並沒有一股腦地把資料塞在流水帳的章節中,而是順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場關鍵「戰役」與三次圖博「遠征」(這些軍事術語,隱隱諷刺著現代性思維中的侵略本質),慢慢透過主人翁視角鋪張開來。於此,個人的命運裸露在政治權力話術、機槍連發子彈和凶猛冷酷的自然裡,織錦著行動者對意義感的追尋,直直催人落淚。它們為說理的知識骨骼添加了迎風搖曳的花葉,每一個人面向圖博文化世界的不同反思,深邃地建構了這棵知識樹更豐富與沉潛的內裡。
在這些故事中,身為一九二一年探險隊隊長的查爾斯.肯尼斯.霍華-貝瑞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Charles Kenneth Howard-Bury)可能不為聖母峰史學家所熟知,但書中他的故事每每讓我著迷:生為父母兩家貴族的後裔,他有著「霍華-貝瑞」這個二合一的獨特姓氏。照理講,他可以進入牛津與劍橋,但卻選擇了皇家桑赫德斯特軍事學院。在一戰前,他數度化妝整容於中國邊境探險,並把一隻哈薩克小熊(名喚「Agu」)帶回家,撫養牠一生。戰時入伍,霍華-貝瑞數次被俘,因貴族身分躲過一死,並於戰俘營開展出經典般的逃亡,獲勳不少。他因可以說二十七種流利的歐、亞語言而被選入第一次聖母峰遠征隊。過程中,他徹底被大自然與圖博性靈文化所折服,後半生成為一名業餘但資深的植物學家,書中一段由他的手記所寫的描繪是這麼寫道:
返程重新翻越了桑群拉,整個喀爾塔已來到他腳邊時,霍華―貝瑞休息了一下,這是他獨自行動時的習慣。這裡的空氣很清澈,也沒有跡象要下雨,或是下雪。他注意到一隻胸前是紅色的文鳥立在一株侏儒杜鵑上。另外從一欉柳樹上,傳來一隻噪鶥的呼聲,外加烏鶇的刺耳叫聲。整片山谷上,有渡鴉與黑耳鳶飛在非凡的高度上,而在天空的頂點,他看見了一隻胡兀鷲的黑色剪影,朝著東方愈飛愈高。從山口望去,喀爾塔曲就像一條銀線,兩側夾著在廣袤地景上有如玩具的田野與村落。
《靜謐的榮光》同時也是一本信實的著作,甚而可說:信實到近乎髮指的地步,例如對於軍備品的統計:「除了一億零八百萬組繃帶與野戰敷料,皇家陸軍醫療隊還――截至戰爭結束――用掉了兩萬兩千三百八十六隻義眼」、對遺骸的大體解剖學素描:「更讓人不忍卒睹的是臉部的創傷:少年的嘴巴沒了雙唇,該是鼻孔的地方變成了鮮血淋漓的孔洞,一簇金髮連在被砲彈削掉頭皮的腦殼上」、對布魯斯准將豪奢作風的窮追不捨:「在這些補給品中有六十罐鵝肝鵪鶉罐頭,外加四十八瓶香檳,而且還是將軍最鍾愛的牌子與年分:一九一五年的蒙特貝羅 (Montebello)」、對馬洛里遺物的掌握:「兩條手帕,其中一條是酒紅、綠、藍色,另一條則是紅、藍、黃色,兩條都繡上了他的姓名縮寫 GLM」。在註釋書目中戴維斯說,他與團隊的研究工夫可以準確到「幾乎完整地確認出了每一個人在一戰中的每一天,分別被派駐在哪個地點」,身為讀者,我們只能鼓掌、自勉,好好暗地說聲:Bravo!
為什麼在二○二二的台灣,我們值得花上一大把勁,來讀上一本英語世界十年前出版、講述一樁一百年前遺事的遙遠之書?除了高超的寫作技藝、研究與見識,還有呢?
「融入這世界上曾有過的最高貴的幾個心靈」,是我的由衷建議。正如同作者戴維斯在書的扉頁上所提:「這本書獻給我的祖父(丹尼爾 • 魏德 • 戴維斯上尉)」,所有歷史寫作的初衷,都是試圖理解我們的前代人們,在與我們近似年紀的時候,懷抱著什麼樣的世界觀和意義感。作者和讀者都試著挪用自己的生命體驗,接近或揣想他們的感受,從而達成一種貫穿時空的聯繫,以解消現代人無邊際、沒來由的孤寂意識。這本書猶有更勝之處,是它還涵蓋了聖母峰與圖博高原這兩個最孤高、最荒遠的神聖地界,它們沒有隨人類主角的亡故而消失,反而在我們向之訪問之際,不斷揭露逝者體察聖境後的各種生命智慧,不論是馬洛里的,還是札珠仁波切的。探險隊的二十六個主角之一約翰 • 諾艾爾(John Baptist Lucius Noel)說:聖母峰是天空中的崗哨,一個有希望與救贖在等待人前往探尋的目的地;一個在這瘋狂的世界裡,讓人感覺到有些什麼仍一如往昔的象徵。
台灣當下獨特的生命處境是:我們離一切都太近了,也高度地功利導向,所有一切都錙銖必較,卻少了慷慨付出生命的意義感;《靜謐的榮光》對應著當年英國和現今英語世界的心靈困境,說出:「The price of life is death(死亡之前,要過足人生)!」,對台灣仍深有啟發。
一九二四年第三次遠征隊隊長艾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在鎩羽歸來之際,曾悠悠地自語:「在這樂音悠揚的承平時代,還有什麼比像極地與聖母峰這樣的壯舉,更能為大英帝國得以繼續其命脈,為如今已有如風中殘燭的冒險與創業精神,留下一絲火種?」雖然帝國國族的意義在這本書裡不斷地展示其虛妄的面貌,但意義的追索,仍然是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力量――讀一本有重量的書,其實也就是說:我們的探索,永遠在路上。
序
▍序
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早晨,在高懸於海拔兩萬三千英尺(約七一一〇公尺)處一個雄踞在東絨布冰川(East Rongbuk Glacier)上,只比聖母峰北坳岩面邊緣低一點點的冰架營地中,探險隊隊長艾德華・諾頓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Edward Norton)送別了兩名即將孤注一擲來嘗試攻頂的同伴。其中三十七歲的喬治・雷・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是當時英國登山界的翹楚,而年僅二十二的山帝・爾文(Sandy Irvine)則是青年才俊的牛津學者,登山經驗趨近於零。至為關鍵的,是時間。天氣雖然晴朗,但南方的天際有捲起千堆雪,足可驚濤裂岸的雲海,而這顯示季風已經抵達孟加拉,不久就會席捲喜馬拉雅山區,然後如一名登山者所說的,「途經之處將灰飛煙滅,無人倖免。」但馬洛里還是不改其樂天的本色。這樣的他在寄回英國的信中寫道:「我們這次絕對要一帆風順地攻頂,願上帝與我們同在,否則就算是咬著牙含著風,我們也要一步步跺到聖母峰。」
諾頓比較樂觀不起來。「毫無疑問地,」他私下對探險隊的攝影師,在喜馬拉雅探險資歷豐富的約翰・諾艾爾(John Noel)說,「馬洛里知道自己這一趟希望渺茫。」口出此言,或許代表記憶中逝去生命的重量壓在了諾頓的心上:一九二二年,七名雪巴人(Sherpa)被留在山上一命嗚呼,外加這一季又添了兩條雪巴冤魂;一九二一年,蘇格蘭醫師亞歷山大・凱拉斯(Dr. Alexander Kellas)於入山與偵察途中埋骨崗巴宗(Kampa Dzong)。更不用說有多少人曾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了。馬洛里本身是一名身段與力量過人的登山大家,但連他都曾在聖母峰三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諾頓見識過崇山峻嶺的冷酷無情。以北坳為起點,攻頂的路線會經過北脊,而北脊會在極富戲劇性地抽高數千英尺之後,融入東北脊,然後東北脊又會接棒通往聖母峰頂。就在前一天,他跟霍華・森默維爾(Howard Somervell)曾從北脊高度兩萬六千八百英尺(約八一六八公尺)的一處前進營出發。避開了席捲東北脊的刺骨寒風,他們向上攻抵了切開聖母峰北壁,並從形如金字塔的聖母峰峰體底座急墜一萬英尺,直達絨布冰川的大雪溝。森默維爾在兩萬八千英尺(約八五三四公尺)處放棄。凍得發抖的諾頓繼續挺進,但身體顫動到他懷疑自己是不是染上了瘧疾。當天稍早爬在黑色岩石上的時候,他誤判形勢地脫下了護目鏡。抵達雪溝之際,他眼前已經開始出現疊影,勉強站著已經用盡他所有的力氣。他只得在海拔二八一二六英尺,距離峰頂僅九百英尺處掉頭,之後他得到了森默維爾的搭救,並在森默維爾的協助下通過了被雪覆蓋的岩板。在撤退回北坳的過程中,森默維爾自己也突然崩潰,無法呼吸。他重擊自己的胸膛,鬆開了阻塞物,然後咳出了一整片喉嚨內襯。
到了早晨,諾頓已經失去了視覺,暫時性因為陽光而變得目盲。在極度的痛苦中,他思考了馬洛里的攻頂計畫。馬洛里與爾文捨棄了北壁,改而選擇取道東北脊,那兒只有兩道障礙阻擋著通往峰頂金字塔的路:首先是本體為黑岩,存在感十足的巨塔,名為「第一台階」,再過去的「第二台階」是一百英尺的斷崖,沒有辦法行走,只能加以攀登。爾文的經驗不足固然令他擔心,但諾頓並未對此一搭檔的組成加以干預。馬洛里已經全神貫注到老僧入定。身為無役不與、英國探險隊的三朝元老,世上再沒有人比他對聖母峰的狀況更明瞭。
兩天之後,六月八日的早晨,馬洛里與爾文踏出了高營,朝聖母峰邁進。隨著透光的雲堤通過了山脈的頭頂,燦爛的朝陽也騰出了位子給柔和的雲影。諾艾爾・歐德爾(Noel Odell)做為從旁襄助他們的優秀登山者,最後看到他們活著是在午後十二點五十分。他遠遠從峭壁上眺望著模糊的馬洛里與爾文:兩個微小的人影在山脊上踽踽前進。隨著雲霧緩緩湧入,兩人留給世人的記憶也被裹上了一團謎霧,惟有歐德爾親眼目睹。馬洛里與爾文從此再無聲息,而他們的失蹤除了讓一整個國家久久不能自已,也就此成為了人類登山史上難再有事件能出其右的無解之謎。
歐德爾從未須臾質疑過兩人在大限之前抵達了聖母峰頂,也衷心相信讓兩人從印度出發跋涉數百英里,穿越圖博,只為來到山腳下,背後推動著他們的是何等崇高而美好的使命。歐德爾用筆,寫下了他對兩位故人的永恆思念:「我最後的那驚鴻一瞥,看到的是一個秉性如此迷人,任誰都會忍不住要與之親近的靈魂,是天賦的才華洋溢與身心所散發出的無比潛能;我看到的,是他正『勇往直前』,並與伴他同行的另一個正直之人分享著那一幕的神聖莊嚴。能親眼目睹那一幕,是生而有涯之凡人的殊榮;而在有幸能親炙這一幕的幸運兒當中,更寥寥有人能向前邁去,終與那超凡入聖的絕景融為一體。」
-
▍第五章 馬洛里登場(節錄)
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十二日早上,喬治・馬洛里的形單影隻地站在船艏的上層甲板,望穿了破曉時那若明還暗的藍色背景,見證了海霧的升起;而同時間蒸汽船薩丁尼亞號駛過了直布羅陀海峽,進入了地中海。不是很喜歡長途旅行的他,從四天前在梅西河的伯肯海德上船之後,就一直過得有點悽慘,主要是沿著歐洲岸邊下到聖文森角(Cape St. Vincent)的過程為何謂濕冷下了最好的註腳,同時老舊的薩丁尼亞號本身就潮濕狹小到讓人幽閉恐懼感大作。被他留在英格蘭的除了愛妻茹絲,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依序分別是六歲與四歲的女兒克萊兒(Clare)與貝里姞(Beridge),還有還在襁褓中,才七個月大的小兒子約翰(John)。在一封家書當中,他抱怨自己在船上的起居空間,還不如自己在法國待了十六個月的一戰西線。置身於船身外殼的呻吟聲與引擎勉強自己運轉的金屬敲打聲中,外加全天候有燈光照進他的房間,馬洛里在船上可說毫無隱私可言,對此他說「你完全不會有有僻靜或獨居的感覺」。前線的坑道與壕溝是低於地表的存在,姑且不論橫行的鼠患,「你至少可以享有一點孤獨,一點其他地方或許都體驗不到,大地像是啞掉了的孤獨」。
此外馬洛里想從旅伴身上獲得安慰的希望,也同樣落空了。「目前為止,」他在海上短短一天後就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看都不想看到他們——甚至應該說,我的天啊,我厭煩死他們了。」用餐真的是一大考驗,其中晚餐時間又最讓人坐立難安。「我會被夾在一個弗雷澤上校跟一個名叫侯利歐奇,不知道來幹嘛的傢伙之間,其中侯利歐奇從上船以來,就沒有在餐桌上跟左右鄰座開啟過任何話題——所幸他的餐桌禮儀還算是相當得宜。上校是個高高瘦瘦、十分骨感的英裔印度人,外表有點嚇人——但個性倒是非常溫和,而且動作似乎也是我所見過最慢吞吞的一個。我覺得他內心應該是個好人,但就是非常不懂得聊天的藝術,由此跟他講話乾到不行——好的話題落到他的手上,會活活被用亂棍打死,不然又是被他踐踏倒滿身都是灰。我只能倒抽一口冷氣。」
被馬洛里形容為「快活說書人」的船長是他一個小小的避風港,另外就是船上有一名印度陸軍的退伍老兵也有一點類似的效果。這名退役軍人老兵曾經在庫特(Kut)被奧圖曼土耳其人俘虜,但也許是老天眷顧,他竟然從美索不達米亞沙漠的死亡行軍中活了下來。要知道,當時所有的阿拉伯部落都會跑出來對戰俘丟石頭,扒走傷者身上的衣著,甚至還會用沙子塞住戰俘的嘴,不讓他們大呼小叫。這些文字所對應的畫面,讓馬洛里一想到就縮一下。而在信裡對茹絲描述這位印度老兵時,他會躲回到自尊心的制高點上,穿戴上他從進入劍橋就讀之後就慢慢打造出的保護盔甲。「雖然教養差又熱情氾濫,但這人還算善良。」馬洛里貶中帶褒地介紹了對方,但也沒忘了補上一槍說,「但他的問題不在於他醜到讓人受不了,或是個野蠻的食人族,不是這樣的,他的問題在於他無聊透頂。」
真正能馬洛里徹底放鬆的,是開闊的風,是像鷹巢般能讓他居高臨下鳥瞰一切的船艏,是能讓他釋放能量的體能活動。做為運動,他會在甲板上走個十三圈來湊成一英里,還會做一整套肌肉體操來讓人「腰軟筋開」,至少他是這樣對茹絲說的。早在他還在索姆河擔任基層砲兵軍官的時候,他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是在身上帶著一本叫做《傑佛瑞之書》(Book of Geoffrey;典出美國作家華盛頓・爾文﹝Washingon Irving﹞的《見聞札記》﹝The Sketch Book of Geoffery Crayon, Gent.﹞),但永遠不會出版的手稿,裡頭集結了所有他希望以嶄新的方式傳給下一代的道德觀與愛國情操,而如今他也會時不時拿出來複習裡頭的字句。此外他還會閱讀大文豪狄更斯的惡漢小說《馬丁・翟述偉》(Martin Chuzzlewit),品嘗西裔美籍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的作品,狼吞虎嚥他朋友兼前追求者,同性戀英國作家利頓・斯特拉齊(Lytton Strachey)所撰的傳記作品——《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不過說來說去,他最常做的事情還是思念著茹絲,也思念著家鄉。
等到直布羅陀的灰影緩緩地消解,巨巖的全副立體感與輪廓終於以蔚藍的地中海蒼穹為背景,顯露出在他的眼前,他抑鬱的內心終於得以撥雲見日。「隨著日光慢慢升起,巨巖的樣貌也捨棄了模糊不清的邊際,重拾起斬釘截鐵的確切外形,」他在信裡對茹絲說道,「無比壯觀,一如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所說,在宏偉到令人歎為觀止之際,也仍得以保持著單純到極致的美麗——你想像不出世上還能有比這更耀眼的岬角。」他反射性地思考起了登山者該走什麼樣的路線登頂。「巨巖有著非常純粹的表面,其一刀切的垂直程度實在名不虛傳,由此成功登頂的人幾乎可以縱身一躍,就從最高點跳進海面,我估計垂直距離大約會落在七百到八百英尺之間。」
對馬洛里而言,地中海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遠離「波濤洶湧的狂野海洋」,溫暖而明亮的地方。隨著體感溫度的上揚,一種愉悅的改變也降臨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覺到我們進入了一個舒爽的世界,萬里無雲的晴空高掛天上,四目所及都是靜謐而耀眼的海洋。」在北方,粉嫩的雲堤從西班牙的土地上升起,蒼白的地平線外矗立著「潔淨而光芒四射、雪線深及腰際的山脈……創造出雪山聳立於海面上,無法言喻的宜人絕景」。
嶄新的美景每天都會不斷更新,船的右舷橫躺著北非的海岸,距離近到馬洛里靠著雙筒望遠鏡就可以區別出一個個小村子裡的一棟棟屋子,甚至還能辨識出從霧霾與塵埃瀰漫的地平線中升起的斜坡上,種著的莊稼分別是玉蜀黍跟小麥。在天空的另外一端,盤旋在落日之上的,是阿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s)的白色諸峰,遠看就像非洲頭頂上的王冠。四月十五日,就在要登陸馬爾他的前夕,他在給茹絲的信裡是這麼說的:「地中海在日照中美不勝收,還有蒸汽船踽踽前行帶來的平靜步調,而我獨自坐在船艏看著開闊的海面,也看著陸地與我擦身而過……我們將在馬爾他停留六個小時,而我說什麼也要去賞賞花。再會了我甜美的天使,我對妳的愛永無止盡,還有許許多多的吻要給我們的孩子。」
過了馬爾他,下一站便是埃及。隨著薩丁尼亞號進入蘇伊士運河,兩岸可以看見的是散落著的各式戰鬥殘骸,那是戰爭初期由土耳其攻擊所留下的遺跡。那片蒼涼寂寥的地景,這「以戰爭之名集結的醜惡團塊」讓馬洛里油然生起一種「鄙視與反感」。在他的想像中,薩丁尼亞號彷彿是在沙灘上滑翔而過,平靜無波地穿越了運河,唯一的可以挑剔的只有在內心不斷加深的鬱結。原本他對這樣的低迷心情不以為意,他想著那不過是起源於席捲船上所有乘客與船員的痢疾,畢竟連船長都無法與之匹敵而倒了下去。但這種低落的心情不斷向下探底,就這樣當船噴著汽出了紅海,接近到亞丁的燃料補給站之際,馬洛里突然內心一股悸動,感受到了一種黑暗的直覺、一種不祥的預感,由此他在給茹絲的信中提到了「災難或危險的逼近」。到了熱到讓人睡不著的夜裡,他赤條條地躺在臥舖上,任由風扇扇葉攪動著停滯軟爛的空氣。來到白天,眼前所見不是大海就是地平線,能打破那種單調的,只有成群的鼠海豚跟逐浪的飛魚偶爾躍出海面。在橫越完印度洋,眼看要抵達可倫坡的前夕,他再一次陷入了憂鬱當中。「這文明生活的表象,全都是空洞的騙局一場。」他在五月二日的信中寫道。「大海有多美多吸引人,就有多邪惡、多深沉……海中有一道不安的靈魂——即便在徹底平靜無波的狀態下,當海面真的就像凍結在了沉靜當中,其心臟也彷彿仍繼續隨著緩和的長浪在搏動著,而在船上的我們只能無止盡地隨之慵懶而溫和地一起起伏跌宕,就像是要偕海浪一同前往時間的盡頭一樣……那感覺就像是我們身後被自然力量的殘虐陰影追趕著,容不得我們片刻忘記大自然能展現出什麼量級的暴力。」
不過瞬息萬變畢竟是他最突出的個性,馬洛里很快就在一個禮拜後找回了那個熱情洋溢的自己。五月九日他一睜開眼睛,就殷切地期待起了加爾各答。在這之前,他便已經心有所感於印度之令人驚嘆,如他在稍早登岸的馬德拉斯(Madras;今清奈)就待了好幾個小時仍流連忘返。按照他在接近孟加拉灣時寫給茹絲的信中所言,他在馬德拉斯的經驗可說「驚奇到無法言喻——光是這麼多人同時出現在一個小空間裡,就非常難以想像,更別說每轉一個彎,後頭都有不可思議的光景揭露著堪比金字塔跟西敏寺的差距,迥異於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與風俗民情。」
惟隔天五月十日,殘酷的現實在加爾各答重新集結,因為加爾各答將沒有人等著為他接風洗塵。前一晚他在薩丁尼亞號上收到探險隊長霍華─貝瑞的來信,信中指示他要自行登上碼頭,然後頂著豔陽走到兩英里外的海關,因為聖母峰委員已經指派了數千磅的裝備與補給品,要由他負責完成報關程序。帶著對英屬印度知之甚詳且對當地行事作風瞭若指掌的輕鬆口吻,這封信在結論裡要馬洛里先為做為探險隊命脈的補給品確保好通往大吉嶺的輸送無虞之後,再逕自閒步前往火車站,搭乘前往山區的夜車。「我這晚於五點動身前往大吉嶺,隔天中午才抵達目的地。」馬洛里在從加爾各答寫給茹絲的信中說。「我將在此接受孟加拉總督的招待——這裡非常豪華、非常舒適,但我並不期待跟那些官差打交道,而寧可待在我估計布洛克目前身處的聖母峰大飯店裡。其他人現在都已經到大吉嶺了,只有凱拉斯例外,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四月五日爬了一座山,而這也讓瑞彭顯然有點緊張。這裡現在熱到會滴汗,但我還滿喜歡趁早餐之前去溜達溜達。先這樣,喬治。」
目次
導讀|死亡之前,要過足人生/The Price of Life Is Death――馬洛里漣漪與《靜謐的榮光》|詹偉雄
第一章 大山牆
第二章 想像中的聖母峰
第三章 攻擊計畫
第四章 辛斯頓的操盤
第五章 馬洛里登場
第六章 入山的門徑
第七章 鳥兒的盲目
第八章 東邊的入山之路
第九章 北坳
第十章 眾人渴望的山巔
第十一章 芬奇的勝利
第十二章 生命之索
第十三章 生命的代價是死亡結語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