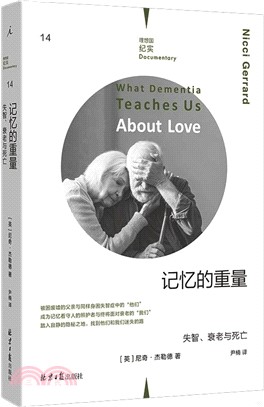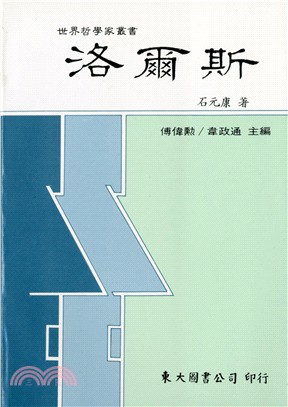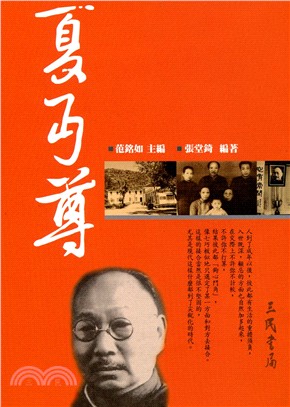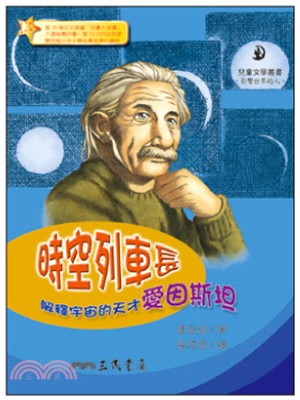記憶的重量:失智、衰老與死亡(簡體書)
- 系列名:理想國紀實
- ISBN13:9787547746318
-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北京日報)
- 作者:(英)尼奇‧傑勒德
- 譯者:尹楠
- 裝訂/頁數:平裝/288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3/07/01
商品簡介
失智症意味著什麼?作為這個時代的瘟疫,它就在我們身邊,或許也在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是身患失智症的人與其照護者的故事。作者從身患失智症的父親講起,延伸到許多人的故事,既包括處於失智症不同階段的人、作為伴侶或子女的照護者,也包括科學家、心理治療師和醫生,以細膩的對話、深入的調查講述失智症是如何逐漸帶走一切的,並探討不同形式的專業干預。
這也是我們的故事。失智症造成的記憶、語言喪失以及帶來的羞恥感同樣可能發生在不可避免走向衰老的我們身上。深入失智症內部,作者帶我們走進隱秘之地,思考“家”的含義、人之為人的意義,以及如何更好地面對衰老與死亡。
作者簡介
尼奇·杰勒德(Nicci Gerrard),英國小說家、記者,長期為《觀察家報》撰稿,2016年獲得英國最重要的政治寫作獎——奧威爾獎。2014年,在患失智症的父親去世後,與朋友一起發起以其父親名字命名的“約翰運動”(John’s Campaign),為失智症患者家屬爭取醫院探視權;2016年,該運動獲得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支持。
名人/編輯推薦
★ “沒有記憶的人生根本不是人生。”——寫給身患失智症父親的挽歌。
作為一種編輯我們生活的方式,記憶將不同的自我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當失智症潛入生活,它會不斷攻擊人類最珍貴的東西——奪走記憶和能力,帶走愛,使人進入自我遺忘的世界。作者的父親與失智症相伴十幾年,最後因治療腿部潰瘍被困醫院五周後完全失去神志。作為父親的記憶看守人,本書既是作者寫給身患失智症父親的一曲挽歌,也是將父親永遠留在身邊的一則人生續寫。
★ “倒計時開始。”——探究不同失智症患者不同階段失去的旅程。
今天,大約在每六個80歲以上的老人中就有一個會得失智症,年齡越大,患病概率越高。除了身患失智症的父親,作者還采訪了不同年齡、身份的失智症患者,講述了從處於早期階段的猶豫不決但還能表達自身感受,到變得“無憂無慮”“把自己的孩子當成兄弟姐妹”、失去同理心、不能自理、不再給出響應、被 “非人化”、成了“活死人”,處於破碎和遺忘狀態的過程,以及生命的余波——死亡、哀悼和善終。
- “痛苦、疲憊和絕望。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崩潰。”——被“隱身”的照護者的故事。
在英國,大約有70萬人在照護失智症患者;其中, 60%至70%的照護者是女性。作為照護者,他們逐漸由配偶、子女變為護工,除了要做到細心的身體照顧,還要成為計時員、記事簿保管員,不時面對大吼大叫或一臉冷漠,能做的就是在無法堅持時繼續堅持。本書通過采訪不同的照護者,展現了他們努力保持自我的方式。
★ “認可至關重要。”——怎樣做才是最人道的干預形式。
本書從醫生、護士的角度探討失智症患者需要的醫學支持,從在進行的藝術項目分析藝術對失智症患者起到的幫助,並延伸探討了荷蘭、丹麥等國先後出現的失智症村、美國發起的“失智症友好倡議”協作運動、日本啟用的用來監測和照顧失智症患者的設備……從情感與醫學角度講述怎樣做才是對失智症患者最人道的干預形式。
★ “走著走著就走了。”——每個人都將面對的衰老和死亡課題。
作為一種“世紀病”,失智症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家庭中,或許也在我們自己的未來,這是對我們每個人的挑戰。此外,從處於破碎和自我遺忘狀態的失智症患者身上,我們也會看到曾經的自己和未來老年的自己——記憶衰退、被無視以及羞恥感。探討失智症意味著什麼,也是在探討我們可以為身邊的人、為未來走向衰老和死亡的我們做些什麼。
序
序 曲
哦,心靈啊,心靈溝壑縱橫,
那墜落的懸崖,
如此駭人,陡峭,深不可測……
父親去世前一年,他和我們一起去瑞典避暑。當時,他已經和失智症(dementia)共同生活了十幾年。他在逐漸消失——他的記憶衰退了,語言能力退化了,認知能力也下降了,一切都在離他遠去。整個過程和緩、平穩,他對此也毫無怨言。但那個假期,他過得很開心。他很愛大自然,置身其中自在不已。他叫得出英國許多鳥類、昆蟲、野花和樹木的名字。我記得小時候他會帶我去家附近的樹林裡聽鳥兒們清晨的合唱。站在樹下,沉浸在嘹亮的歌聲裡,他會告訴我哪首歌是槲鶇唱的,哪首是烏鶇唱的。至少,我想我記得曾經有過這麼一幕,但也許這只是我難過時給自己編的故事。
在瑞典的時候,他會去森林裡采野蘑菇,參加歡樂的小龍蝦派對。在派對上,他會喝阿夸維特酒。他還會頭戴花環,坐在水彩畫的調色板前,凝視著屋外的草地,盡管他的畫筆從來沒有沾過畫紙。一天晚上,我們帶他去蒸桑拿。他喜歡蒸桑拿,因為這會讓他想起曾經在芬蘭度過的美好時光,那時候他還是個無憂無慮的年輕小伙。蒸完桑拿,我們扶著他下湖遊泳。那是個美麗而靜謐的夜晚,光線朦朧,樹影婆娑,一片月光灑在湖面上。我還記得那晚的寂靜,只是偶爾響起湖水拍打防波堤的聲音。
父親年老體衰,遊了幾米後就開始唱歌。這是一首我從未聽過的歌,而從那之後,我也再沒聽過這首歌。他一邊繞著小圈遊泳,一邊放聲歌唱。他似乎非常滿足,甚至可以說很快樂,但同時這也是最孤獨的一幕:仿佛世界上已別無他人,在這晦暗不明的夜晚,在這充盈的寂靜中,只剩他一人,與湖、與樹、與月亮和散落的星星為伴。
自我的邊緣十分柔軟,自我的邊界單薄且充滿空隙。那一刻,我相信父親和世界融為了一體,它滲入他的體內,他則清空自己與之融合。他的自我飽受歲月摧殘和失智症的折磨,在這仁慈的時刻,他的自我超越語言、意識和恐懼,迷失在紛繁萬物中,融入浩瀚的生命奇跡之中。
或許,這就是三年後的今天我想對自己說的,我試圖理解一種疾病的意義,它有能力摧毀自我,它就像深夜潛入一座耗盡畢生精力建造的房子的強盜,肆無忌憚地破壞和劫掠,在破碎的門後竊笑。第二年的2月,父親因下肢潰瘍住院,傷口愈合緩慢。醫院的探視時間規定嚴格,後來,他又感染了諾如病毒,病房幾乎被封鎖,這也意味著一連幾天他都孤單一人待在醫院:沒有人握著他的手;沒有人喊他的名字,告訴他有人愛著他;沒有人幫他與外界保持聯繫。他的下肢潰瘍最終得以治癒,但由於離開了深愛的家,脫離了熟悉的日常生活,被一群陌生人和機器包圍,他很快失去了心智,以及對自我的脆弱控制。關心和護理之間有一條巨大的鴻溝,而我的父親就墜入了這條鴻溝。
最後回到家的時候,父親已經骨瘦如柴,形容枯槁,而且口齒不清,無法行動,失去了意識。他再也不能去蒸桑拿,再也不能去森林或湖泊,再也不能戴上花環。他並非被疾病的微光籠罩,而是深陷愈加濃重的黑暗中。之後的幾個月裡,他經歷著緩慢的死亡。秋冬交替,寒風凜冽,他還是離開了我們。我不禁回憶起父親最後幾個月的可怕經歷:底樓的小房間裡,他就那樣躺在病床上等待著,卻什麼也等不來,他心愛的鳥兒們仍舊飛落在窗外的鳥食架上;例行公事般的盥洗、喂食和活動身體;醫生、護士和護工,以及有關疾病和死亡的整套體制做法;明明知道意識在消亡,身體在崩塌,卻什麼都做不了。為了避免想起這令人窒息的漫長的終結過程,我將對父親的記憶定格在了瑞典的那個湖中。柔和的暮色中,萬籟俱寂,自我與世界不可思議地融合在一起。
我過去常說,我們是由記憶組成的,可是,當我們失去記憶時,會發生什麼呢?那種情況下,我們是誰呢?如果我們陷入瘋狂,真正的我們又身在何處呢?如果我們喪失心智,我們的人生故事將如何續寫?即使是在痛苦的生命尾聲,我也從未覺得父親不是他自己,盡管與此同時,我覺得他已經失去了自我。他雖已離開,卻仍在;他雖然缺席,卻仍有很強的存在感。在語言和記憶之外,另有某種東西在延續,也許只是某種痕跡,就像河水侵蝕岩石,生活也在他身上留下一條條印記。他仍舊和藹可親,他的過去藏在他的一顰一笑中,藏在他挑起濃密的花白眉毛的動作裡。他的過去也藏在我們心裡。他可能認不出我們,但我們能認出他。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這種無法磨滅的本質,曾經,它被稱為“靈魂”。
文明、控制和安全感在深水之上形成一層殼。在我們所有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不安意識:我們對自己的控制是多麼地不堪一擊,我們對自己的心智和身體的控制是多麼地岌岌可危。失智症——各種形式的令人痛苦的失智症——讓我們不禁要問:何為自我?何以為人?
它常被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它也是“世紀病”。
2015年,英國估計有85萬人患有某種形式的失智症,而未確診的失智症患者人數據說與之相當。隨著人口的老齡化,預計到2021年,這一數字將會增加至100多萬,到2051年則將達到200萬。而在美國,2017年,估計有550萬人患有失智症。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世界大約有4700萬人患有失智症。大約每三秒鐘就有一個人患上失智症。
人們提起失智症就好像在談論定時炸彈。事實上,這顆炸彈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爆炸,只不過是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悄無聲息地炸開來:隱秘的破壞。患有失智症的人通常會成為“失蹤人口”——被重視獨立、繁榮、朝氣與成功,厭惡脆弱的社會遺忘和否定。而他們只會提醒我們:我們都會變老,我們都會衰弱,我們最終都會死去。失智症是我們目前最恐懼的一種疾病。它是“痛苦的故事”,而與痛苦一樣,它會一直持續。
這種痛苦從個人蔓延到那些照顧、關心他們的人身上,甚至還會蔓延到他們的社區,乃至整個國家。正如一位醫生對我說的那樣,失智症“極度不尊重病人、照護者、醫療保健系統、社會關懷……它無法融入我們創造的社會體系”。無論是從對患者本人的影響,還是從對患者周圍的人的影響來看,沒有哪一種疾病能像失智症這般由其影響定義。它的意義涉及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政治和哲學等各個方面。它讓我們付出的代價無法估量,我不是指經濟上的代價,盡管這方面的代價巨大。(據阿爾茨海默病協會估算,僅在英國,人們為它付出的代價就高達320億美元,而全世界為其付出的代價高達8180億美元,而且這一數字一直在穩定上升,到2018年預計將達到1萬億美元,遠高於癌症、中風和心臟病的支出。)我指的是它讓人類自身付出的代價:羞恥、困惑、恐懼、悲傷、內疚和孤獨。它引發了一系列深刻的道德討論,關於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我們所持有的價值觀和生命本身的意義等。
與此同時,我們是第一代真正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在我小時候,很少見到失智症患者,這種疾病幾乎不被承認。我的外祖父患有失智症,我的祖母也得了相同的病。雖然我知道他們得了這種病,但也並沒有什麼表示:他們曾經是我生活中一抹鮮活的亮色,現在則是自然而然地逐漸被抹去。我或許還曾為他們感到難堪,他們曾經是權威人物,現在卻如此無助。這種疾病的病征還讓我感到些許厭惡,我沒想過身患疾病的他們有什麼感受,也沒去想象正在上演的是一場怎樣的悲劇,有時候它是以令人厭惡的鬧劇形式登場的。這種疾病是一種恥辱,是羞恥、恐懼和否定的源頭,在緊閉的門後,它無聲蔓延。那個以D開頭的單詞。
現在,我們對失智症的認知與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全新的認知喚醒了社會、政治和道德責任感。現在,我們可以看見之前隱藏的東西了。20世紀70年代,英國大約有30萬人患有失智症,他們分散在英國各地。今天,這個數字已經是那時的三倍。在未來25年的時間裡,這個數字將達到170萬左右。而在美國,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僅阿爾茨海默病導致的死亡率就增加了55%。走進醫院病房,即使是普通病房,也會發現幾張或大部分病床上躺著的都是失智症患者。養老院的情況也與之類似。不妨再看看那些訃告。(當我考慮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試圖列一張所有死於這種疾病的名人名單,但我最終選擇放棄:這樣的名人太多了,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我來不及更新。)看看那些新聞故事,無論是令人振奮的,還是讓你悲傷得號啕大哭的,我幾乎想不出誰與這種疾病沒有過密切聯繫。它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家庭中,在我們的基因裡,或許也在我們自己的未來。(大約每六個80歲以上的老人中就有一個會得失智症,年齡越大,患病概率越高。這種情況就像花園裡藏著個狙擊手。)即使不是我或你得失智症,也會是我們深愛著的某個人。
我們不能只是談論“他們”了——現在是“我們”的問題,應該如何面對這一挑戰,成為我們人類集體的問題。在高度重視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時代,我們迫切需要提出一些問題:我們該為其他人做些什麼,我們該為自己做些什麼?誰比較重要?為什麼一些人似乎沒有另一些人重要?為什麼有些人會被忽視、無視、忽略和拋棄?何以為人?何為人的行事方式?我們經常脫口而出“我們”這個詞,它代表著集體、民主和合作。它要求發出集體的聲音,正如政客們喜歡說的那樣,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嗯,是的,不過,有些人在頭等艙,可以欣賞海景,晚餐時可以來一杯雞尾酒,有些人在底層船艙,還有些人則根本看不見。陽光不會照到他們身上,我們甚至意識不到他們和我們一樣在船上。另外,還有不少人掉進了冰冷的水中,被無盡的黑暗吞沒,而船上的樂隊還在繼續演奏。
那些我們看不見的人,那些我們不關心的人,那些我們不為之感到心痛的人,那些去世前一直被我們忽視的人……如果我的父親生前是個重要人物,我想在他最需要關懷的時候,可能會受到不同的對待。當然,他是重要人物,但只是對那些認識他、愛他以及與他的生活緊密相連的人而言如此。我們的系統和社會應該珍視每一個生命,這樣,我們就不必為了拯救彼此而強調情感認同。我們都有義務拯救彼此,甚至對我們的仇敵也不例外,因為世界為“我們所共同擁有”,我們需要分享和傳承。沒有你就沒有我,沒有我們就沒有我。我們最終都要依靠彼此,我們應該對每個人、任何人都持有熱忱的、明確的義務——尊重他們不是出於愛,而是出於共同的人性。
……
但是,就像悲傷有不同階段一樣,失智症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盡管和悲傷一樣,這些發展階段並沒有那麼清晰和穩定。對於失智症的診斷並非一句話了之,而是一個過程的開始,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這個過程中充滿希望、善意、冒險,以及恐懼、悲傷和令人心痛的失去。
這本書展現了那些不同階段的失去的旅程,從最初模糊的病象,發展到晚期直至生命終結時的失智症。在病情發展最嚴重的時期,它似乎是一種對自我的殘酷破壞和對生命意義的啟示。對於失智症患者和那些深愛著他們的人,這本書提出了一個問題:失智症究竟意味著什麼?這本書探討了最仁慈和最不人道的專業干預形式,並追問專業人士能在多大程度上“關心”我們關心的人,以及個人和家庭必須承擔多少可能壓垮生活的負擔——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這本書既從外部探索失智症,也盡可能深入地從內部進行探索。它著眼於關於失智症的令人不安的新人文發現,我相信,這是一種情感現代主義的形式,有助於我們想象那些難以想象的事物,為本質上無言的事物找到一種語言,將我們引至黑暗的門檻。它聚焦於人們在走向黑暗的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悲傷,這些人既包括患有這種令人悲哀的疾病的人,也包括那些關心他們的人。它關注生命的余波:死亡、哀悼和善終。它講述了護士、醫生、科學家、治療師、哲學家、藝術家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它講述了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和陪伴他們的人的故事,後者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化身前者的看門人、記憶和聲音。失智症與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所說的“靈魂的耐力”遙相呼應。
我的父親一直是我的向導,他起初精力充沛,而後逐漸衰弱,有時候還會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他也曾是我的靈魂。一直是我的靈魂。
……
我的一個朋友50歲就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與腦瘤共存了十年。他去世十年後,我仍然經常夢到他。他是我的夜間訪客,見到他我總是很高興。我記得我是多麼想念他。在最近的幾個夢裡,我們一起在跳蹦床。有時候,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了,但我知道,我們會談起這個話題。有時候,我相信他已經復活,他的死是個誤會,只是一場夢,或是超出清醒世界認知的存在。但到目前為止,我從沒夢見過我的父親。他從不來看我。也許,這是因為我完全不相信他已經死去。我內心隱約覺得還有第二次機會,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更快看出他身上發生了什麼,阻止它發生,讓帶他走到生命盡頭的時鐘倒轉。“嘿,尼克。”他會伸出手跟我打招呼。
我想記住父親患病前的模樣,其實我記得——但最常在我腦海中閃過、令我措手不及的畫面,卻是他生命終結前最後幾個月的樣子:我透過窗戶看著他,他倚靠在病床上,凝視著他親手打造的心愛的花園。父親已經走了,同時卻仍停留在這裡。生活的一部分隨之而去。父親去世後不久,我和一個朋友發起了一項運動,為失智症患者爭取更富同情心的醫院護理服務。當然,我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我想要拯救我的父親,雖然他已無法拯救。因此,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意識到,其實我“之所以寫出來,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懺悔”,或如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所言:書寫即是在乞求寬恕。
目次
序曲
第1章 面對
第2章 變老
第3章 大腦、心智和自我
第4章 記憶和遺忘
第5章 診斷
第6章 羞恥
第7章 照護者
第8章 通過藝術交流
第9章 家
第10章 晚期
第11章 醫院
第12章 最後
第13章 告別
第14章 死亡
重新開始
注 釋
參考書目
致 謝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