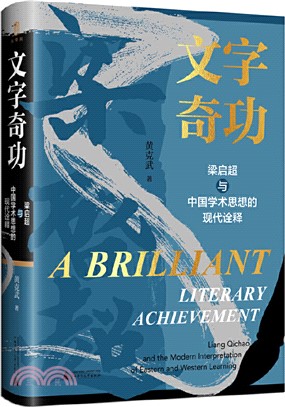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為一部研究梁啟超與近現代中西思想文化之關係的學術著作,全面梳理其一生中學術思想的流變過程、研究進路,展現了其豐富而深刻的學術探索和精神世界。
作者以梁啟超為研究物件,對其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做深入分析,並聚焦於其學術研究對近代中國轉型的影響,旨在以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來呈現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的複雜過程。此外,作者還闡釋了梁啟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來解析各種議題,並以中西比較的方法探索中國的獨特性,建立新的學術典範,並最後歸結到“新民”“新國”與“鑄造國魂”的現實關懷。
作者簡介
黃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著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研究》《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等。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賣點
1.梁啟超研究專家黃克武重磅力作,著名學者教授許紀霖、楊念群、歐陽哲生一致推薦。
2.一部研究梁啟超思想的專著,全面梳理了梁氏學術研究的方方面面。結合梁氏成長經歷中的幾個節點,全面展現其在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學術思想方面的研究進路、流變歷程,挖掘其著作中的思想內涵,打破學界所謂“梁啟超思想膚淺、駁雜”的觀點。
3.追溯“新民說”理想的現實來源,展現一代啟蒙先驅的家國情懷。在作者看來,梁氏學術研究盡管涉及方方面面,其研究路徑卻始終是以中西比較的方法探索中國的獨特性,來建立新的學術典範,而最後歸結到“新民”“新國”與“鑄造國魂”的現實關懷。
4.探討梁啟超如何以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推動現代中國學術轉型。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梁啟超從未放棄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價值的追尋,並試圖會通中西,以一種新的概念、新的角度回觀傳統,對其進行現代詮釋。而這樣的詮釋無疑為現代中國學術轉型奠定了一定基礎。
5.一本乾貨滿滿的輕學術著作,帶給你輕鬆又不失深度的閱讀體驗。作者學術基礎扎實,治學態度嚴謹,論述有理,分析有據;行文則平實易懂,深入淺出,娓娓而談。在版面安排上,各章注釋均以尾注形式呈現,正文閱讀輕鬆連貫,尾注則能進一步深化理解。
編輯推薦
“文字奇功”是胡適寫給梁啟超挽聯中的一句,提綱挈領地點出了梁啟超一生的成就——以“驚心動魄”的文字繼承舊傳統、引進新思潮,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作者以此作為書名,足見其對梁啟超的讚賞。
毫無疑問,梁啟超是公認的近代中國啟蒙先驅之一。然而從學術思想層面,現當代很多學者對他的評價並不高,認為他學術興趣雖然廣泛,卻思想膚淺、駁雜,沒有深刻的內涵。黃教授卻不以為然,他說:“有些朋友喜歡問我,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賞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無疑問是梁啟超。”是的,他對梁啟超的定位是“思想家”。這也是他30年如一日對梁啟超思想進行研究之後得出的有力結論。在這本書中,黃教授以這30年來的研究成果為據,涵蓋了梁啟超在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方方面面的思想成就,挖掘其著作中的學術價值,為梁啟超思想正名。
在做這本書之前,我對梁啟超的認識可謂淺薄。最初的認識來自那篇大家耳熟能詳的課文《少年中國說》,其激勵作用延續至今。後來對他的了解也不多,更多限於他的個人經歷和生活情趣等方面,對他的著作閱讀僅浮於表面,缺乏深度思考。而通過黃教授深入淺出的解讀,我得以用心重溫梁氏那些經歷時間檢驗的作品,真正走進這位啟蒙先驅的思想深處,一窺他豐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都說“文如其人”,對一個人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閱讀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讀懂一位學術思想家,或許還需要一位領路人。於我而言,在讀懂梁啟超這條路上,黃教授就是那位領路人。
序
序:我與梁啟超研究的因緣
一、學術淵源
我從小就喜歡閱讀梁啟超的文章,在中學國文課本中就曾讀過好幾篇他的文字,例如《學問之趣味》《敬業與樂業》《最苦與最樂》等。從中學歷史課本中我還知道了他是“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但那時對他只有很簡單的印象,知道他的文字很感人,是和康有為、章太炎、嚴復、胡適等人齊名的一位學者。我買的第一本梁啟超的著作是1973年文化圖書公司(臺北)印行的《梁啟超全集》(其實是一本選集),還在上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閱讀痕跡。後來又買了臺灣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1983年版)與《飲冰室專集》(1978年版)。
一直到赴美讀書,進入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從1992年開始,我才在墨子刻教授的指導以及張灝、張朋園等先生的協助下,比較系統地閱讀梁啟超的作品,並寫成我的第一本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在此過程中,我的指導教授墨子刻先生對我研究梁啟超深有啟發。有關墨子刻先生的生平與學術貢獻,可以參考我所寫的《墨子刻先生學述》一文,以及我為他所編輯的中文論文集《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
1992年在墨子刻先生的指導下,我開始研究梁啟超。
我研究的重點是梁啟超思想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文本《新民說》。1992年,我趁著修課的機會完成一篇大約50多頁的文章。墨先生看了不太滿意,要我更系統地分析二手研究的成果,以及梁氏思想的內涵與轉變,再將梁啟超的調適思想與譚嗣同(1865—1898)的轉化思想以及孫中山的思想做一對比。於是我又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與墨先生往復討論,再修改、擴充、增補,在1993年初寫出十多萬字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的初稿。
書稿寫完之後,我寄給兩位我很尊敬的梁啟超專家指正,一位是張灝先生,一位是張朋園先生。後來兩位張先生都給我回了信。
張灝先生大體讚同我的觀點,但他在信中特別強調梁任公思想中民族主義的一面。他說,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具有強烈的中國情懷,反對帝國主義,關心“中國往何處去”,梁啟超那一代更是如此。後來我看他的作品與訪談才更為了解此一情懷。1959年張灝先生到美國之後,閱讀了中國30年代的作品,“發現了中國和作為中國人的意義”。在1960年代寫作博士論文期間,他曾出於強烈的“民族情感”而“左”傾,終於“在海外找到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我不知不覺地進入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一旦發現了qun體的大我,個人小我也無所謂了”。從這個角度他回觀歷史,而看到轉型時期是民族主義通過新的制度媒介在中國廣為散播的一個時代。張灝先生的梁啟超研究與此一心境有密切的關係。他斷言:“早期的改革者因而開啟了一個趨勢,這個趨勢在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變得更明朗,就是他們把民主融化在民族主義中,而看民主不過是民族主義中的一項要素。”張灝先生此一想法深受史華慈有關嚴復研究的影響,至1980年代他開始思索“幽暗意識”的問題後,才逐漸有所轉變。
張朋園先生也在1993年兩度回信給我,他比較肯定我的著作,原因可能是因為他長期研究“立憲派”,而且他和李澤厚一樣認為我們應對以“革命典範”為中心的論點加以反省。他說:
你的大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我拜讀了一遍。正好出版委員會要我審閱,我就先睹為快了。我非常細心地讀你的大著,告訴老兄,我完全被你說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回想我三十年前討論梁的思想,那時受的訓練不夠,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沒有今天那麼周密,加上當時的研究環境十分簡陋,我自己的見解,想起來就汗顏,你不批評我,反而使我不好意思…… (《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3月3日)
他又告訴我:
你談近年來對梁啟超的研究,我讀了有進一步的體會,我很高興你也對梁有興趣……我們對梁啟超的了解尚不夠全面,他寫的東西太多了……要是有大量的人力也投入研究梁,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來。 (《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4月4日)
在兩位張先生的支持下,拙作在1994年2月問世。這本書出版之後,我立即開始有關嚴復的研究計劃。我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來從事這一項研究,2001年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2008年我的英文書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我又寫了《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再後來將我的嚴復研究整合成《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一書,2022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嚴復研究的主旨即在呼應上述梁啟超研究一書中所強調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追求“會通中西”的理想時,儒家傳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思想史研究上,我最感謝的是墨子刻先生,正是他對我研究梁啟超、嚴復思想的指點與鼓勵,使我從一個初學者,漸漸登堂入室,了解其中的精髓。他不但為我的兩本中文書、一本英文書撰寫序言,大力推薦,而且有一次他還跟我說:“你的梁啟超的書寫得比張灝好,你的嚴復的書寫得比史華慈要好。我很為你感到驕傲。”
這可能是恩師對我的溢美之詞,鼓勵我將來能“青出於藍”。不過我真的很感謝他過去二三十年來對我的幫助。簡單地說,我有關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繼承了墨先生在《擺脫困境》一書中的理念,並嘗試提出與史華慈、張灝等兩位近代思想史名家不同的一個解釋。
二、追尋啟蒙者的身影
我在寫完梁啟超的專書後,又開始與中國大陸以及日本學界做梁啟超研究的同好切磋、交流,訪問梁啟超生前在各地留下的蹤跡。這些經驗也逐步拓展了我對梁啟超思想的認識。
1993年11月底,在張朋園先生的介紹下,我首次返鄉,到中國大陸的廣州參加“戊戌後康梁維新派學術研討會”。在會上,我不但有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達到“以文會友”的目的,而且走訪了南海、新會的康梁故居。我對新會茶坑村的梁啟超故居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開始了我與大陸學界的交往,並赴各地探訪與梁啟超相關的史跡,而對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認識。
位於廣東新會茶坑村的梁啟超故居是他出生與成長的地方,在1989年被列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整個建築建於清光緒年間,是用青磚、黑瓦建造的磚木結構,建築面積有400多平方米,由故居、怡堂書室、回廊組成,是富有當地特色的民居建築。梁啟超的祖父與父親都有志於仕途,但祖父僅考上秀才,父親連秀才都沒有考上,因而對梁啟超寄予厚望。他在此地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11歲中秀才,16歲成舉人(1889),獲得了“神童”的稱號。隔年他認識了康有為,這時康尚未中舉,然而見識遠遠超過了梁啟超。任公說康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三十自述》),使自己“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清代學術概論》),在萬木草堂與學海堂接受各種思潮的洗禮,“乃雜遝泛濫於宇宙萬有,芒乎湯乎,不知所終極……學於萬木,蓋無日不樂”(《南海先生七十壽言》)。這一次我亦走訪了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的康有為故居與他曾潛心修學的西樵山。南海與新會的訪問之行讓我對康梁師徒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1896年梁啟超主筆上海《時務報》,1897年11月到次年3月,梁啟超應黃遵憲、熊希齡之聘赴湖南時務學堂任教。康有為還勸譚嗣同“棄官返湘”與任公合作,在湖南開展維新活動,“大倡民權”。這一時期是梁啟超的思想最為激進的階段。他借由康有為的“三世之義”“大同之說”來求變,又通過傳教士的譯書來學習西學。時務學堂的學生須先將《春秋公羊傳》和《孟子》反復鉆研,明白其中微言大義,然後擇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較參證,以了解“變法”的重要性。任公在此培養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後來時務學堂師生聯合發起自立軍及護國軍等救國運動,影響深遠。2004年我與張朋園先生應耿云志先生的邀請赴湘西吉首大學參加“第一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研討會”,本書的第二章《鑄造國魂: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就整理自在這個會上發表的演講。會後,我與張先生坐火車赴長沙訪問,周秋光教授帶我們參觀了岳麓書院,還去看了1922年梁啟超重遊長沙時所書“時務學堂故址”的紀念碑。時務學堂是今日湖南大學的前身,是在湖南創辦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標志著湖南教育由舊式書院制度向新式學堂制度的轉變,也是湖南近代教育史的開端。
25歲時梁啟超和康有為一起發動“戊戌變法”。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流亡日本14年,在此期間,他受到日本學界的影響,通過日文書刊打開一個新的學術視野,使他對中學與西學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對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的深入挖掘,要歸功於京都地區的日本學者。在1993年廣州的研討會上我認識了狹間直樹、齋藤希史、竹內弘行等日本學者。後來因為張朋園先生的關係,我了解到日本“關西學派”的學者在狹間先生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梁啟超研究會”。這些學者於1993—1997年間研究梁啟超通過日本認識西方的過程和內涵,並於1999年之後,先後以日文、中文和英文出版其研究成果,肯定“梁啟超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向現代化的推動者”。
狹間直樹等人在籌組這個集體研究時,因緣際會,能夠一方面研究梁啟超,另一方面翻譯丁文江、趙豐田編著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翻譯工作從1993年開始,主要的參與者有10人:島田虔次、狹間直樹、井波陵一、森時彥、江田憲治、石川禎浩、岡本隆司、高嶋航、村上衛、早川敦等京都大學教職人員。此外,也有關西地區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參與。
2003年底,我赴京都搜集資料,曾在石川禎浩先生的邀約之下,有幸參加了梁啟超研究會《梁啟超年譜長編》翻譯小組的第三百多次例行聚會。日譯本在2004年由東京的巖波書店出版,共5卷。此一翻譯本因為增加了許多注釋,又精確解讀了許多人物背景與典故,學術價值甚高。這種對學問的執著很能反映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問的特點。
我也在赴京都大學訪問時多次參觀了梁啟超研究會所收集的梁啟超曾閱讀過的日文書籍。他們不但編輯了一個詳細的書目,也盡可能地收集紙本圖書。在京大有一個書柜,陳列的就是他們所收集到的梁啟超著作中提到的各種日文書籍,其中有許多文本都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後來狹間先生也慷慨寄贈好幾種重要史料與我,本書第三章《宋明理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陽明學》的寫就即參考了狹間先生所寄贈的《松陰文鈔》《節本明儒學案》。
199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狹間直樹教授來臺北訪問。其間,他發表了題為《梁啟超研究與“日本”》的演講(後刊載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對梁啟超與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善鄰譯書館”進行鉤稽,指出此一譯書館的出版品是梁啟超西學知識的重要來源。狹間先生強調我們必須掌握中、日、西三方面“知層”板塊之間的嵌合關係,才容易厘清梁任公有關中國現代化之構想的底蘊。
狹間教授也邀請我與張朋園先生參加了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傅佛果教授主辦的“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國際研討會,本書第五章《西方哲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與康德》的雛形,就是在這個會議上發表的文章。
總之,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十余年間,我與日本學者的接觸拓展了我對梁啟超在1898—1912年間流亡日本時期思想的認識。和日本學者較不同的地方是,我認為日文書刊無疑豐富了梁啟超的知識來源,但他並非單純地吸收新知,而是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看這些來自日本的西學。此一論點在本書中亦有詳細的論析。
這一方面的研究也使我想要追蹤梁啟超在日本的史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湯志均的《日本康、梁遺跡訪問》(《文物》1985年第10期)與夏曉虹的《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關梁啟超的部分。夏曉虹的尋蹤幾乎涵括了梁啟超在日本活動的主要地點。我只去過東京近郊的橫濱。
1906年,有一位華僑富商麥少彭先生(廣東南海人)將他在神戶郊外一個叫“須磨”的地方的一棟別墅“怡和山莊”借給梁啟超及其家人,梁氏從東京搬到神戶。梁思成說,這棟別墅有一個大花園,連著一片直通海濱的松林,住在此地可以同時聽到波濤聲與松林中的風聲,梁啟超於是將之命名為“雙濤園”。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梁啟超離開神戶返回中國,於1914年定居天津,並在天津義大利租界的馬可波羅路旁購買空地建宅,自己設計了一棟磚木結構的意式二層小樓。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則建於1924年,位於故居樓的西側。2001年天津市政府斥資重修,並在此地建立了“梁啟超紀念館”。2003年10月12—16日,我受邀參加了由天津梁啟超研究會召開的“紀念梁啟超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去天津開會,也借此機會參觀了梁氏故居,對這兩座外觀漂亮、氣勢雄偉的歐式小洋樓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從1993年我赴廣州開會,認識世界各地梁啟超研究的同好,又進而認識梁氏後人,並走訪啟蒙者留在各地的遺跡,這也算是用行動印證了董其昌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裡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吧。
三、重新挖掘梁啟超的學術思想
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我寫過有關梁啟超的一本專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與多篇論文。2013年5月我曾在臺北做過一場公開演講,題目是“文字奇功:嶺南才子梁啟超”,那一次演講的海報一直貼在我辦公室的門口。這個演講主要介紹我對梁的整體認識以及他身後的各種評價。在這之後我很想寫一本有關梁的書,但是卻一直延宕下來。其實在市面上已經有不少梁啟超的傳記。這些傳記大致有兩個類型。一類是介紹梁的生平事跡,如李喜所、元青兩位先生的《梁啟超新傳》,以及許知遠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另一類是從梁啟超的師友關係來展現他的交遊網絡、社會關係及一生的變遷,例如解璽璋的《梁啟超傳》。這二者各有優點,前者以時間軸為中心,敘述任公的一生發展,對其一生的變化有較為清楚的呈現;後者則打破時間的序列,以任公與幾個重要人物的交往,來編織他的一生。我覺得這兩類書都對讀者了解梁啟超有所幫助,但是也都有一定缺失,讀完之後我們除了認識梁啟超流質多變、跌宕起伏的一生,並不易產生一個清晰的圖像。這緣於上述的傳記在任公學術思想方面剖析得都不夠深入,而學術思想才是他一生的靈魂。
在現有的梁啟超學術思想研究成果之中,有兩個人的著作給我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第一是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年)一書中有一章談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第二是我的老師張朋園先生所寫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不過蕭公權與張朋園兩位先生都沒有深入探討梁啟超的學術思想,這是我想要撰寫此書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是我研究梁啟超的因緣,以及對他一生概括的認識。現在梁啟超的作品好像已經不那麼吸引年輕朋友的注目,而我覺得他的作品有如一個礦藏,值得人們深挖。的確,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有其缺點(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所批評的“封建遺毒”),然而也有其精致、優美而感人的地方。梁啟超正是中國文化精華的一個化身,他的作品是從傳統中綻放出來的現代花朵。
本書的主書名“文字奇功”是胡適寫給梁任公挽聯中的一句話,全聯是“中國新民,平生宏許;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我覺得其中的“文字奇功”四個字提綱挈領地概括出了梁任公一生的成就。簡單地說,他意識到自己身處“兩頭不到岸”的“過渡時代”,因而以“驚心動魄”的文字繼承舊傳統、引進新思潮,成功地推動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轉型。
本書的主旨在以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來了解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的複雜過程。在此過程中,梁啟超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來解析各種議題,並以中西比較的方法探索中國的獨特性,來建立新的學術典範,而最後歸結到“新民”“新國”與“鑄造國魂”的現實關懷。直至今天,這無疑仍然是一個“未竟之業”,有待吾人繼續努力。梁啟超的思想深邃複雜,本書只能呈現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熱切地希望讀者能通過拙書而了解梁啟超,並進入他的思想世界。今年是梁任公誕辰150周年,謹以此書向這位啟蒙先驅致以最深的敬意。
黃克武
2023年5月20日於南港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刪節。)
目次
序:我與梁啟超研究的因緣 1
第一章 導論:有關梁啟超學術思想的一個爭議
一、前言:“百科全書式”的巨大存在
二、有關梁啟超學術思想的一個爭議
第二章 鑄造國魂: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
一、前言:從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辯論談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變”?
三、鑄造“國魂”:晚清時期梁啟超的“國民”思想
四、“中國不亡論”與“國性說”:梁啟超的“文化民族主義”及其影響
五、余論:“遊魂說”與“新啟蒙”
第三章 宋明理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陽明學
一、前言:儒家傳統與梁啟超的思想轉變
二、梁啟超思想的內在邏輯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並蓄:陽明學與梁啟超思想的取舍問題
四、小結
第四章 諸子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的墨子學
一、前言:清代墨學的復興
二、《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的墨子學
三、20世紀 20年代梁啟超的墨子學
四、小結
第五章 西方哲學的現代詮釋:梁啟超與康德
一、前言:梁啟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學者對梁啟超譯介康德之評估
三、從“カント”到“康德”:梁啟超對康德中國圖像的建構
四、梁啟超對康德思想的闡釋與評價
五、小結
第六章 熔鑄一爐:梁啟超與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
一、前言:清季的“新史學運動”
二、實證史學、道德知識與形上世界
三、熔鑄一爐:新康德主義與佛儒思想會通下的新史學
四、對梁任公史學思想的評價——代結論
第七章 民初知識分子對科學、宗教與迷信的再思考:以 嚴復、梁啟超與《新青年》的辯論為中心
一、前言:20世紀初有關靈學的爭論
二、中西文化交流與近代中國靈學研究的興起
三、上海靈學會的“科學”宣稱:科學、靈學相得益彰
四、中西靈學之融通:嚴復對科學、宗教、迷信關係之思考
五、《新青年》對靈學之批判:科學與迷信之二分
六、思想的延續:梁啟超與科玄論戰
七、小結
第八章 結論:梁啟超對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
附錄:略論梁啟超研究的新動向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清末民初的很多知識分子相信傳統文化不死,即使如反傳統者所宣稱的那樣,傳統已經衰亡,他們仍鍥而不舍地要“為故國招魂”,並期盼讓“舊魂引生新魂”。這一思路源於梁啟超求索“中國魂”與《新民說》中“采補”“淬厲”並重的想法,以及嚴復“會通中西”的理論,嘗試將儒、釋、道的生活哲學與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及進化論的宇宙觀、歷史觀等結合在一起。
從“人種論”到“民族主義”: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
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反復討論的幾個問題包括:“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有沒有可能遭逢‘滅種之禍’?”以及“國人應如何救國保種,乃至‘進種’?”等等。
對於上述問題,清末以來的思想界有兩種主要的答案。
一類是轉化式的看法,認為“方死方生”,中國人只有拋棄舊傳統、擁抱新文明,中國國家、文化才能獲得新生。如陳獨秀認為中西之間是對立的,接受西方就得唾棄中國。這時放棄傳統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的目標(上文所說“主觀願望”)。至1933年,胡適在芝加哥大學演講“儒教的使命”(The Task of Confucianism)時曾說:“何鐸斯博士在演說的末尾說:‘儒教已經死了,儒教萬歲!’我聽了這兩個宣告,才漸漸明白——儒教已死了——我現在大概是一個儒教徒了。”他所要強調的是“儒學已亡”,而儒學的死亡是使儒學具有新生命的開始。平心而論,這還是一種主觀願望,但在胡適看來,儒教的死亡顯然已經不是目標,而是“事實”。對此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化路向,錢穆描寫得最好。他說:這些學者“好為概括的斷制。見一事之弊、一習之陋,則曰吾四萬萬國民之根性然也;一制之壞、一說之誤,則曰吾二千年民族思想之積疊然也”,“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反傳統主義者、全盤西化論者與科學主義者多半抱持這種觀點。此一觀點也契合上述列文森的解釋。
第二類答案則是調適型的“繼往開來”,或稱為“更生之變”的主張。他們也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缺失,卻希望從傳統之中去蕪存菁,融入西方文化的優點,走出一條再造文明的路。清末民初采取調適型思路的知識分子,與轉化型學者一樣,面對民族、文化存亡的生死戰,而企望有所作為。借用余英時描寫錢穆思想時所用的字眼,他們相信傳統文化不死,而且即使如反傳統者所宣稱的那樣,傳統已經衰亡,他們仍鍥而不舍地要“為故國招魂”,並期盼讓“舊魂引生新魂”。這一思路源於晚清梁啟超求索“中國魂”,與《新民說》中“采補”“淬厲”並重的想法,以及嚴復“會通中西”的理論,嘗試將儒、釋、道的生活哲學與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及進化論的宇宙觀、歷史觀等結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中西文化分歧、合流的歷史處境與會通中西的目標,嚴復、梁啟超等調適型學者的思想在理論層面並不具有“兩面性”[即史華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中所說的“賈努斯臉”(Janus-faced),意指兩者的分歧與矛盾],無論這個兩面是指中與西、體與用、形上與形下、“價值理性”與“工具性理性”(韋伯意義之下),或科學與哲學。他們肯定中國倫理價值與涉及“不可思議”和“幽冥之端”的形上世界,同時也接受西方有關追求富強與民主的技術和制度安排。對他們而言,這幾方面可以互補、融合,也都是建立一個理想的自由國度所不可或缺的。此一會通的信念也使他們不具有列文森所強調的理智與情感的分裂或所謂精神迷失、茫無歸著。
上述“會通”的思路從清末士人追索“國魂”開始,至民國初年發展為學界挖掘“國性”“國粹”,“立國精神”或“民族精神”,並追求中國精神文明與西方物質文明的結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梁啟超看到西方文明的危機,出版《歐遊心影錄》,而奠定此一觀念之基礎。梁任公所揭橥的新方案是:“我們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其具體的內涵是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結論部分所說的:他“確信”以先哲之理念為基礎,可調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個性與社會性”,由此而“拔現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諸高明”。
從晚清到“五四”,調適型知識分子都以會通精神來闡釋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中國傳統所具有的價值,也堅持中國必定不亡的信念,然而其論證的基礎卻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晚清主要是以“國民”來鑄造“國魂”;至“五四”前後則強調“國性”“國粹”“立國精神”與“民族精神”。換言之,前者可以說是“政治民族主義”,後者則是“文化民族主義”。不過這兩者只是側重點上的區別,並非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相反,我們應視之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故國招魂”的延續性發展,而且他們的想法一直具有影響力。這幾個路向其實都可以在清末民初梁啟超的思想之中找到原初性的探索,並且形塑了20世紀思想界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之討論的基本方向。這樣一來,梁任公在《清議報》 《新民叢報》與《國風報》 《庸言》上的言論,一方面帶起了像胡適那樣新學青年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同時也為後來調適型知識分子繼往開來的精神開拓了寬廣的思路。
梁啟超的思想從晚清到民初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變遷。梁啟超在清末強調的是一種“政治性”的“國民想象”,他借著結合中西思想,而建構由現代國民所構成的一個現代國家,企圖在傳統的根基之上思索中國作為政治體的未來。然而在民初,他更為強調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文化”想象,或可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他所提出的“中國不亡論”與“國性”的想法,都源於此一想象。
任公在《時務報》與《清議報》階段即曾提出“中國不亡論”,但當時他的重點主要在於中國的“四萬萬同胞”之“人種”的不亡。此一人種的概念,與政治性的國家概念是重疊的,同時也與他所提出的亞洲“黃種人”相依對外的“亞洲主義”結合在一起。然而,至1901、1902年之後,尤其是從《新民叢報》開始,梁任公轉而強調“民族”一詞,在他看來,“民族”是“種族”加上“文化”;由“民族”一詞又進而產生“民族主義”的觀念。梁啟超之所以從“人種論”轉向以文化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和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呂邦(勒龐)的國民心理學理論有關。呂邦等國民心理學家認為:民族國家必具共同的歷史背景和國民心理,它的組成分子是所謂“心理的品種”而不是生物的品種。如此一來,構成民族的重要成分不再單純是血統性的種族(或人種),而是要加上歷史與文化所構成的心理因素。
在《新民說》中,梁任公解釋他之所謂“民族主義”,其中已透露出人種不是唯一的標準:
自十六世紀以來(約三百年前),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梁任公認為民族主義之根源是一種“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亦即一種精神上、心理上的特質。在梁任公看來,中華民族之所以長久存在,即是因為此一民族之特質:
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於qun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
大約從1902年開始,任公開始多方面地闡釋此一中國“特質”的具體內涵,並相信該特質可以與西方文化的優點結合在一起,從而保證中國不亡。他在1911年《國風報》(當年三至五月)上發表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正是此一心態的反映。61這篇文章整理自任公與友人湯叡的對談。該年二月任公攜長女令嫻與湯叡遊臺灣,在旅途之中兩人日夜相對,討論國事,此文應是當時談話的記錄。在該文之首,有一段“著者識”:“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邊烽燧,一日數驚。日唯與吾友明水先生圍爐相對,慷慨論天下事。劌心怵目,長喟累欷,輒達旦不能休。 ……”
這篇對談主要是針對晚清時流行的“中國必亡”的說法。由明水(湯叡)來陳述此一“中國必亡論”,再由梁任公(滄江)加以辨析,而表明中國不亡。根據明水的陳述,當時不少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衝擊之下認為:一、列強虎視眈眈,企圖瓜分中國,中國可能步朝鮮之後塵而亡國;二、中國政府財政窘困,入不敷出,加上國民生計出現危機,很可能不久之後“全國破產”;三、政府失職,無力處理當前危機;四、國民具劣根性,一國風俗頹壞,人心腐敗。
梁任公不以為然,他認為國人所具有的“渾融統一之國民性,即我國家億萬年不亡之券”。 梁任公的談話與他在臺灣旅行的經驗有關係,他發現即使在日踞之下的臺灣,“其男女曾無一肯與日人雜婚者,避地內渡,歲不絕”,“臺灣且然,況乃中原”。
此外,二人還很具體地談到中國國民性之長短,在優良的方面:一、中國社會實現四民平等之理想;二、國民具有自營自助之精神;三、國民常能以自力同化他族,不但能自保,且能吸收他種文明。至於國民性的短處,明水提出國人缺乏科學觀念、尚武精神,無愛國心、無政治能力等梁任公曾在《新民說》中所反復陳述的觀點。梁任公認為並不盡然,如在尚武精神方面,他曾寫《中國之武士道》,舉證“我國古代尚武之風本甚盛”,至秦漢之後才漸消弱,但是“其根器之受自先民者,終不失墜,有所觸而輒見也”。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梁任公的想法無疑具有陽明學與佛教“唯心論”的色彩,也和上述“國民心理學”有直接的關聯。梁任公說盧般(呂邦)認為國民心理中有“潛伏不現之特性”,在時勢急需之時,“摩蕩而挑撥之,不期而同時並發”。 梁任公顯然相信中國國民性中這些潛伏的正面因子,會如“弱女之計”那樣在危急的情況之下施展出來,“拯所愛於焚溺”。
總之,梁任公企圖指出:
持中國必亡論者,即亡中國之人也。是故吾輩當常立一決心以自誓曰:“中國之存亡,全系乎吾一人之身。吾欲亡之,斯竟亡矣;吾欲不亡之,斯竟不亡矣。”
這篇文章刊出之後曾引起許多回響,我們可以舉錢穆和左舜生為例。錢穆當時16歲,就讀於常州府中學堂。他讀了這篇文章之後,深為任公的“中國不亡論”所感動,從此萌發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他後來在香港新亞書院演講的時候,多次提到梁任公這篇文章“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誠如余英時所述,“他深深為梁啟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左舜生也是如此,當時他18歲,在湖南長沙從長邑高等小學肄業,與同學易克疆是好友。他們非常喜愛閱讀《國風報》上的文章,當其他學生均已就寢之後,他們兩人還在自修室討論。尤其是“梁任公、湯覺頓辯‘中國究竟會不會亡’的問題。把我們兩個青年簡直弄得熱淚長流”。
任公對中國國民性的信心,至民國以後,並未消減。1912年他在《庸言》所發表的《國性篇》《中國道德之大原》,乃至1915年的《〈大中華〉發刊辭》等文中,都反復地從“國性”,亦即“繼繼繩繩 ……一種善美之精神”,來論證中國不亡,並勉勵國人“發揚淬厲”此一優良傳統。
從上述“發揚淬厲”的觀念可見梁任公有關“國性”的想法一方面源於歷史的積澱所產生的文化、心理特徵,另一方面也具有包容性與創造性,“我國民於他社會之文明,非徒吸受也,且能咀嚼融化之,而順應於我國民性以別有所建設”,此即上文所述會通中西的精神。梁任公在1920年的《歐遊心影錄》中更充分地表現出“會通”精神的延續發展。這時歐戰所顯現出的西方文明的弊端使他更為堅信中國文明的價值。他引用柏格森的老師蒲陀羅的話——“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 ……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生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說明此即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任公同時也呼吁國人要有“中國不亡”的信心,而且“我們只管興會淋漓的做去便了”,“不可著急”。
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以“文化想象”為中心所提出的“民族主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當時有不少人在類似的信念鼓舞之下,努力地尋找國家的精神基礎,以證明中國不亡。如嚴復也同樣提倡“國性說”,在1913年的演講中,他說:
大凡一國存立,必以其國性為之基。國性國各不同,而皆成於特別之教化,往往經數千年之漸摩浸漬,而後大著。但使國性長存,則雖被他種之制服,其國、其天下尚非真亡。
除了嚴復,任公的思想也帶動清末民初其他中國士人從歷史文化中挖掘中國不亡的各種根據,有關“國魂”“國粹”“國學”“國故”的探究紛紛興起,“有人以為此‘魂’寄托於歷史,有人以為哲學(儒家與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為文學才是‘魂’的凝聚之地”。錢穆所謂“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與任公所開創的思路便有直接的關係。難怪錢穆在寫給余英時的信中就說:“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
除此之外,當時在香港抱持著相同志向的還有大家所熟悉的唐君毅與牟宗三等新儒家。他們不但和梁任公一樣,在傳統思想傾向上具有肯定陸王、批判程朱,又接受佛學的哲學立場,在西方思想方面尊崇康德,而且主張以漸進改革、繼往開來的精神,會通中西文化,企圖將中國傳統精神資源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以建立一個新文明。難怪有學者認為任公所開創出的思想視角,正是為牟宗三、唐君毅所繼承、開展,二人因此而可以被定位為“現代新儒家的第一開拓者”。
錢穆與新儒家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他們均一方面深入中國傳統“尋找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並認為此一根據主要是中國歷史文化獨有的“精神”價值;另一方面則苦心孤詣批判西方的現代性,並接引民主與科學的制度設計與精神價值,“本中國內聖之學解決外王問題”,以“重建儒家與生活世界的關係”。這一思想系譜展現了近代中國在激進反傳統主義與張之洞乃至梁漱溟的保守思想之間,另有一條“中間道路”。他們所想象的中國不但是一個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以國民精神為中心的政治共同體,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共同體。這樣的志氣德行與事業文章,一直到今日仍然發揮著莫大的鼓舞作用。
(《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第二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