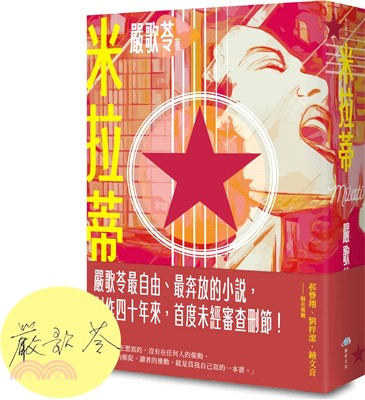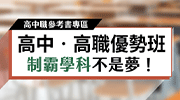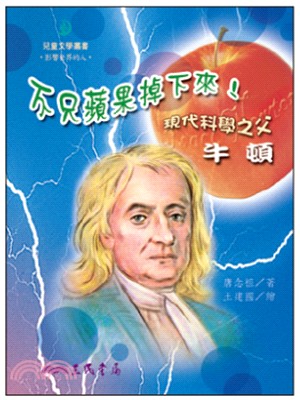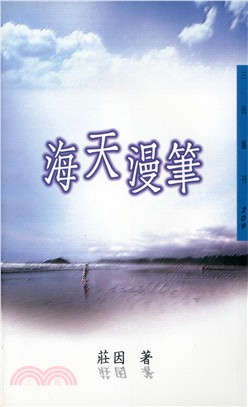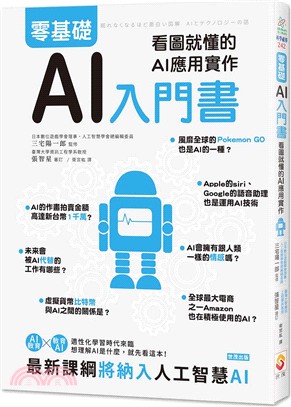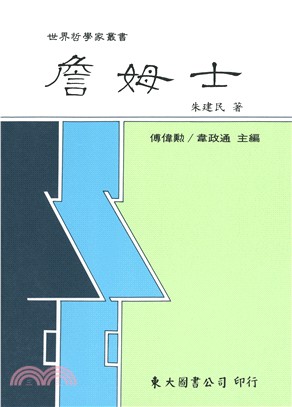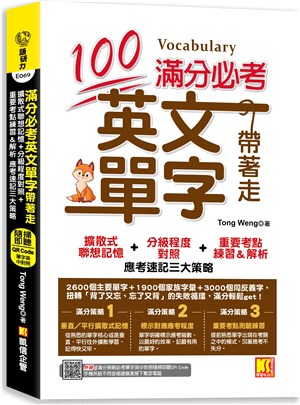商品簡介
嚴歌苓最自由、最奔放的小說,
創作四十年來,首度未經審查刪節!
***
「這是我真正想寫的,沒有在任何人的催動,
或是約稿的催促、讀者的推動,就是為我自己寫的一本書。」
***
郝譽翔、劉梓潔、鍾文音 聯名推薦
猶如過了戀愛期的人又重新戀愛,
八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
體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民主、性愛⋯⋯
然而,這段魔幻時光卻在八九年夏天,瞬間幻滅。
故事圍繞女孩米拉蒂的個人經歷,見證了中國兩代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幻滅。八〇年代初,二十歲的米拉蒂從軍隊文工團轉業,她的人生也經歷了最關鍵的轉型——從被動表演的舞者,變成獨立思考創作的作家。
八〇年代,為米拉蒂帶來了一次觀念大洗牌:自由、民主、性愛⋯⋯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彷彿在一夜間發生了顛覆性改變,曾經的不可能變成了可能,而且可能性似乎是無限的:婚外戀、一夜情、迪士可、黑燈舞會、地下出版、裸體模特兒⋯⋯
八〇年代,也是中國人告別毛時代,對獨立自由等普世價值第一次產生巨大渴望的年代。米拉蒂和她的朋友以及他的父輩,首次站在了世界文學和藝術同一地平線上,看到自由思考和表達,自由創作的無限可能性,他們興奮、振奮,以為從此就會理所當然展開無限的可能性。
然而,一切卻在八九年六月,戛然而止⋯⋯
書籍特色
① 繁體中文版,獨家收錄作者序
② 扉頁限定!嚴歌苓簽印典藏版
*********************************
首刷限定隨書贈禮,全站佳片免費觀賞 ——
Giloo紀實影音 ✕ 惑星文化
「八〇年代如夢似幻|嚴歌苓線上策展」
◎活動說明:凡購買新書可免費線上看 ▸ Giloo全站觀影 14 天序號
◎兌換期限:2024/05/01 ▸ 2024/12/31
◎兌換方式:進Giloo官網點選【序號兌換】,輸入序號,完成會員註冊、登入後即可觀賞
作者簡介
生於上海,少年從軍,二十歲從文。1986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同年加入華人作家協會。代表作有《扶桑》、《人寰》、《白蛇》、《少女小漁》、《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釵》、《穗子物語》、《陸犯焉識》、《媽閣是座城》等作品。
嚴歌苓於1989年赴美留學,就讀於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獲文學創作藝術碩士。自1990年起陸續在海外發表了近百篇作品,在台灣、香港以及中國獲得多項文學獎。2007年出版第一部以英文創作的長篇小說《赴宴者》,受到英、美評論界的好評,並入選BBC小說連播。
根據嚴歌苓的小說改編、並由本人參加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天浴》,分別獲得亞太電影節六項大獎和金馬獎七項大獎;改編自《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分別參展於柏林和坎城影展。嚴歌苓的小說已譯為英、法、荷、意、德、日⋯⋯等21種語言。
名人/編輯推薦
序
對我來說,中國的八十年代是Magic。似乎一夜之間,街上開始流行喇叭褲,蛤蟆鏡,男人們的頭髮長了,女人們的辮子散了,公園的晚風把鄧麗君竊竊私語般的歌聲吹來吹走,那是自發的露天舞場開張了。白天的街道,天黑之後便成了港澳服飾的跳蚤市場,這被稱為夜市的所在,就是當時時髦男女的時尚發源地,雖然已是落伍歐美數年的時尚。不久,公園的露天交誼舞把一些夫妻跳散了,也把一些陌生男女跳成了情侶。我父親那樣的老輩藝術家朋友,從被發配的農村和邊遠地區回到了城市,鬧起了離婚,開始了戀愛(我們當年戲稱「亂愛」),跟我們一起盡享青春,儘管他們是花期二度。那時我所在的成都,出現了一些勁爆的新詞,比如「姦宿」,我猜那指的就是一夜情吧。還有個更具刺激性的詞,叫「群姦群宿」,大概就是熄燈舞所導致的即興情愛。
當時初涉文學的我,更有興趣的是我們的小團體活動。活動包括私家舞會,但舞場下聊的話題都很有趣,多半是聊小團體成員寫的或讀的文學、戲劇、電影作品。我們那個小群體成員的父輩,半數以上都是文學、戲劇、電影、藝術界的老輩兒,都是不久前剛恢復了自由、名譽,甚至工資,重歸他們社會地位,也重新拾起他們荒蕪十年的創作。我們的小團體分享剛剛舶來的卡夫卡小說,班雅明的《悲劇的起源》和《抒情詩人》,然後是沙特和波波娃,再轉到薩繆爾・貝克特、迪倫馬特、田納西・威廉斯⋯⋯平行討論的還有卡繆、弗朗索瓦、福克納、沙林傑、索爾・貝婁,以及美國整個「垮掉的一代」。終於,中南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抵達了我們,讓我們醍醐灌頂地意識到,小說能超越怎樣的疆界,能怎樣地反叛和顛覆。那時,文化、文明的大門朝我們轟然大開,新奇的文學和戲劇、電影和音樂,讓我們應接不暇,恨不能生吞活剝每一部作品。
八十年代的標記不僅是鄧麗君、沙烏地阿拉伯、卡繆、馬奎斯,還有北京民主牆上的文章,星星畫展和傷痕文學。人們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受的創傷、以小說來展示「傷痕」,反思和療癒「傷痕」。還有更早的「傷痕」:延安整風,蘇區肅反,土地改革中冤死的幾百萬土地擁有者。一切都能成為「傷痕文學」的題材,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揭露和控訴的,對於我們那批年輕的文學創作者,中國人幾十年的苦難和物資貧瘠,給與了我們的一條挖掘不盡的豐富礦脈。那時我二十出頭,對於自己幸運於父輩的創作自由,感到理所當然,受之無愧。我真的認為,我們生爾逢時,恰逢民族的大覺醒;我們的大時代來了,它就是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天真而狂妄,認為八十年代僅僅是開端,以後就是才人輩出,進入文明史的大作品將一部接一部地問世,再往後,就是幾十年、幾百年的輝煌。中國人命苦,但撐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總算輪到我們輝煌了。但沒想到,到手的自由,在八十年代結束時,又被收走了。我所認為的大覺醒,恰是一場大夢。我們曾經的同道,不少像書中人物一樣,在八十年代結束後流落國外,儘管終獲自由,但也不得不接受與自由同來的些許「副作用」,比如命運的無定、未知,甚至叵測。
一九八九年年底,我告別了祖國,赴美國留學。他人給於的自由會得而復失,那麼就自己給自己自由吧。在國外回望那如若magic的八十年代,感覺它像一道耀眼的閃電,照亮了我們這代人的整個生命。沒有那十年,就不會有我今天的寫作歷程。我感覺自己跟書中主人公米拉蒂一道,激情而瘋狂地享受了那樣的十年,繼而對那時我們的精神和生命狀態不休地緬懷,尤其當下,中國的自由空氣尤為稀薄,更有「大夢誰先覺」之感。中華民族,對於天賦的自由,何時能享之為天賦?(2024/4/19)
目次
米拉救人
吳可初遇李真巧
子教三娘
私生女
阿富汗人
舞會
過渡人
吳可無不可
米拉扯皮條
梁多被捕
吳可的新劇《排隊》
馬斯洛娃
孫霖露的新房
吳可結業
芙苑之死
新郎老米
重演
暗戀你
老米和小米
李真巧上海行
人流
老米滬上行
梁多出國
真巧出獄
個人問題
真時尚
MILA
人物們的下落
餘音⋯⋯
書摘/試閱
鬥敗他們她更是心酸;換了米拉,他們是不會看的,看也是清風拂過,不忍用看她真巧那樣油爆目光看清水一汪的米拉。她心酸地想著米拉推開門,逆著光直溜溜地站在米瀟門口,走進來時,白色半透明涼鞋露出她乾淨的粉粉的腳趾頭。她又想到米拉的藏藍軍裙,剪短了起碼兩寸,吊在離膝蓋一寸的位置,那一對膝蓋頭兒小得像兒童,均勻地包著一層乾淨的皮肉,雖然兩條長腿一絲不掛,那也不招惹小伙子們看她真巧那樣看。對,就是不忍;小伙子們替她護住她的「清」,護住她以免受他們自己的污損。
見了米拉第二天,李真巧在家裡翻天覆地,多年不收拾的破爛給她扔在紙板箱裡,拖到閣樓上去。泥土地倒是頭一年給水泥蓋上了,但下雨從街沿上進來的泥漿似乎從來就沒乾透過,在水泥地面上畫地圖,深一塊淺一塊。她跟自己冷笑,從這種地面上能走出什麼乾淨人。挑來井水潑上去,用把粗鬃毛大刷子刷,母親下班的時候,地面乾淨了不少,高檔不起來,是升級的低檔。就像母親去見米瀟,臉上搽點痱子粉,多少是個補救。真巧媽虎起臉,用鼻子說,又作怪了。媽的意思是,頭一年把黑土地耕翻,鏟出去,鋪上水泥,是作怪,此為「又作怪」。上回鏟除泥巴地面時,媽問她作啥子怪,真巧以同樣的風涼話回答:挖金條訕。母親心情好的時候,比如代銷點內部分打爛的雞蛋,分受潮的菸絲,或者來了印錯花的棉布,以便宜到近乎白給的價錢賣給店內員工和熟人,成年黑著臉的母親會給她娃娃們一點笑意。真巧也會趁機開銷媽一句:海外來信了?要不就是:金條兌到好價錢了?有一次一個打傳呼電話的顧客給了五毛錢,著急慌忙地來去,忘了拿找零,真巧媽一巴掌摁住那四毛五分,環顧左右,趁同事不注意,把錢順進她的工作服大圍裙口袋裡。她狠狠心,往四毛五分裡添了三毛,買了三個茶蛋,三個孩子分三個蛋黃,蛋白都歸自己。細看蛋白淺褐色表面,一層深褐色碎瓷紋路,看著是貴重的。一人一月才半斤雞蛋票的一九七九年的成都,二毛五一個的茶蛋,實質上也是貴重的。媽把它們切成細牙牙,裝了個難得上桌的細瓷盤,又找出一小串銀器——一個銀環套著五件小玩意,一根剔牙棒,一把挖耳勺,一隻捏眉毛的鑷子,一個微型西餐叉(據說是吃切塊水果用的),最後一個小東西,鏟子不鏟子,鐝頭不鐝頭,是吃螃蟹用的。母親獨自坐在後門口,倒一盅紅苕酒,用那根純銀剔牙棒挑起細細一牙兒茶色蛋白,擱在兩排還算整齊還算白的門齒間,抿著嘴細嚼,端起酒盅輕咂。她此時眼神很呆,看風景看迷了那種呆,而「風景」是靠別人家牆搭的蘆席棚,當中打了隔斷,一邊是廚房,另一邊擱個大馬桶。這種時候,真巧絕對相信自己是個達官貴人的私生女,而母親絕不是生來就這麼糙皮橫肉,也嬌滴滴過,也曾是依人小鳥。那一串銀器就是物證:下江人才吃螃蟹,巴蜀的水是不養螃蟹的。重慶當年雲集多少四海才俊,五湖梟雄,真巧寧可做某個偉岸梟雄一夜風流的後果。
再見到米拉,是個禮拜日。老米到不遠的公園下棋去了,米拉在給父親洗卡其外套。老米春天穿髒的外套,現在洗洗乾淨過秋天。米拉坐個小板凳,衣服比盆還大,又厚又重,跟她兩只細白的手直扯皮。她看著這個十八歲女孩,裹在改窄的軍褲裡的兩條腿向外撇,快要撇成一字線,像在舞台上扮演洗衣班。那額頭白白的,那眉眼淡淡的,那個清啊!真巧忍不住在她臉蛋上摸了一下,說,當兵的,是衣服洗你吧?米拉笑笑。她把她從板凳上扯起來,對她說,當兵的,看好,我們兵團戰士咋個洗衣服。她從床下拖出一個木盆,連水帶衣服,兜底倒進木盆,然後脫下上衣,捲起褲腿,再蹬掉鞋,跨進盆裡,在衣服上踩得咕吱響,一會兒把半盆水踩黑了。
米拉拿起真巧脫在床上的外衣,一件深藍絲絨舊貨,腰收得黃蜂一樣。真巧說,穿下我看嘛。米拉眼睛亮了。穿老百姓的衣服,當兵的覺得刺激。真巧看當兵的把衣服套在白襯衫上,胸部有點空,袖子有點短,但是米拉膚色乾淨得出奇,顯出深藍的高貴來。給你嘍,真巧說。米拉眼睛瞪大,臉皮跟著就通紅,簡直是一份艷福!她真巧的時尚全四川省找不出第二家,這一點小當兵的是留意到的。真巧把米拉往後推一把,嚴肅地上下看,然後嚴肅地說,啥子衣服穿在兩條草綠色灰面口袋上都看不得。說完伸手到腰間,解開紐扣,那條黑色直筒褲被蛻皮一樣蛻下,又給扔在米拉身上:二天穿小姑這件衣服,不准穿你的綠色灰面口袋。
招待所的門廳裡有個穿衣鏡,米拉跑到那裡去照。直筒褲和絲絨上衣讓米拉又抽條一截。鏡子裡,她筆直的腿給鏡子下面貼的一道骯髒膠布歪曲了。必定是給哪個服務員甩拖把摔爛的。真巧穿著綠色面口袋跑來,上身除了乳罩什麼也沒有。米拉說,你怎麼不穿衣服就跑出來了?!真巧說,這不是衣服?她蹲下來給米拉抻褲腳。米拉說,你快回去!真巧笑了,是我的,我都不怕看,你怕啥?外國人上大街還沒我穿得多。米拉扭頭跑回去,在米瀟房間門口,她探出頭來喊:大家都來看!李真巧左右看,一個房門響了,她兩手抱住頭臉就往回跑。
進到房裡,真巧把手才挪開。米拉問她,胸前那麼大兩坨,怎麼不把它們捂住,臉有什麼捂頭?真巧說,捂住頭臉,人家不曉得身子是哪個的。她壞笑。米拉瞪著她,慢慢意識到小姑有多壞。文化局招待所,穿軍褲的只有老米女兒。米拉跺腳,原地打轉:解放軍的臉都丟完了——人家以為解放軍阿姨長兩個那麼大的奶奶!
後來老米的過渡期延長,從招待所過渡到紡織學院筒子樓,真巧常常直接去文工團找米拉。幾乎每天都帶一飯盒菜,不是麻辣這個,就是怪味那個,菜市場撿的垃圾她李真巧都能燒成招牌菜。米拉十九歲發福,真巧是要負一部分責的。不久小姑就成了全團的小姑,連五十多歲的劉團長見到李真巧,老遠看見她拎著飯盒來了,也呵呵地打招呼,小姑來啦。真巧不是回回奉獻,也會索取,有次帶來兩個女孩,叫米拉給她們上舞蹈課。米拉跟她鬼臉耳語,兩個女娃都缺一樣東西。真巧問,缺啥子。米拉說,缺脖子。真巧說她們是她廠子的領導家屬,米拉有義務幫她走通並維持上層門路。這就保障了她真巧活蹦亂跳地休病假,保留免費醫療和二十五元零三分的病休工資。
米拉的領導不幸發現,米拉的腦子比手腳好用,決定派她去藝術學院走讀,學舞蹈編導。編舞劇必須寫文學大綱,領導又不幸發現,他們究竟打不過米拉的父系基因;培養她跳舞多少年,那麼吃力,一夜之間就被那基因搶奪回去了。於是領導們讓她不要惦記舞台了,老老實實做個筆桿子。沒了「四人幫」,筆桿子吃香了,到處都缺筆桿子。米拉的文章在報刊上登出來之後,領導們再次不幸發現,那些文章是不適合穿軍裝的筆桿子寫的。她的父系基因太厲害,早就在米拉生命裡布局,暗中把著米拉的手,因此米拉注定寫不出部隊需要的英雄故事,英雄人物。米拉在一個私人創辦的雜誌發表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小小說之後,米拉的領導被領導的領導找去談話。辦這種雜誌的人,剛勞改過,估計不久還要送回去勞改,領導的領導說。米拉的領導想說,孩子才二十歲,可以教育嘛。但首長一個手勢讓他閉了嘴。手勢很輕,中指和拇指往雜誌上一彈,劣質紙張的雜誌又薄又輕,給彈出去一尺,接著在玻璃板的滑溜,落在地上。這個米拉蒂,可以讓她走人了,部隊不能養這樣的筆桿子。被首長接見的米拉的領導,就是劉導演。劉導演兼劉團長,一百八十斤的體重,一百六十斤是劉導演,只有二十斤是劉團長。比重大得多的那部分劉存信作為導演是捨不得米拉的,冰雪聰明的女孩,卻很好養,事兒特少,過去傻乎乎的一天到晚練功、跳舞,後來編舞也編得不錯。這天劉團長迎頭撞上拎著飯盒走進大門的李真巧,他一揮手,小姑你來一下。真巧笑笑,心想,解放軍團長也是人,也是男人。再一想,也好,米拉給無脖子女娃上舞蹈課,搞定了她的廠領導,她沒有理由不幫她心愛的姪女搞定她的領導。劉團長前頭帶路,李真巧後面跟隨,也不問去哪裡搞定。只見米拉的領導邊走邊脫下軍帽,走走,又脫下軍裝,剩在身上的就是一件洗烏了的老爺們汗衫。李真巧心裡笑,路上就脫起來了。兩人來到團幹部宿舍,沒進門就聽見劉家孩子在練鋼琴,於是真巧給帶進了廚房,一個正做飯的胖老太太被介紹說是「我母親」。真巧趕緊「劉伯母好。」再看此刻的米拉領導,導演和團長都消失了,消失進一個痛心疾首的老漢,用河南鄉音佐料的普通話說,她小姑啊,你要勸勸米拉這個孩子,筆桿子咱就不當了,還回去跳舞吧。真巧一問,劉團長把他上司的訓話說了一遍,末了說,米拉差不多就是我看著長大的,一直以為她比人家少點心眼子,不成想她長的是不一樣的心眼子!這不一樣的心眼子,跳舞沒事兒,耍筆桿子,那就是立場問題,思想意識問題。真巧說,啥子問題嘛?劉導演此刻讓位給劉團長了,一百八十斤都是解放軍長官。他用菸薰黃的食指比劃說,筆桿子,分紅的黑的白的。米拉她爸米瀟,文革的時候,罪名不就是黑筆桿子嗎?真巧笑笑,很榮耀的樣子;黑筆桿子,你們一般人當一個試試。她小姑,我知道你笑啥;米拉不至於是黑筆桿子,不過她也不是部隊需要的紅筆桿子,只能算個白筆桿子,最多是灰筆桿子。文工團領導的色譜讓「她小姑」眼睛瞪得多大的,說,我三哥哥說,米拉出手不低哦。劉存信看了一眼真巧,意思是,看來要費點事才能跟米拉家的人講清。他點了一根菸。真巧也從自己的小包裡拿出一盒菸,抽出一支細長菸捲,夾在她尖尖的手指間,跟劉團長伸出手。劉團長恍惚一下才明白,她這是向他申請對火。劉存信頓時就是個壯年男人,猛吸一口菸,把大半個菸屁股遞給真巧。真巧對了火,把菸屁股還給壯年漢子劉存信,揚起下巴,噴一口帶薄荷味的雲霧,曉得壯年漢子正對面前的女特務目瞪口呆。菸夾在她左手食指和中指尖,手指短粗,但指甲留得長,修得尖,也讓那手妖冶。真巧笑笑:進口的。她抽出五根菸捲,往劉團長面前一放,嘗下嘛,抽起好耍的。團首長沒有推辭,在一旁切麵葉子的首長母親眼睛涼涼地在真巧臉上一刮。去年開始,真巧要所有熟人給她介紹對象,堅決嫁到國外去,除了老撾越南柬埔寨,哪國都行。最多的是港澳同胞,其中一個姓崔的老闆,白面書生的,還順真巧的眼。洋菸是崔老闆付的淺層肌膚接觸代價。
部隊不能讓她寫那種東西,她小姑,明白了吧。真巧見劉團長說此話時,眼睛盯著她擱在小桌上的菸盒。團長口中的「東西」,是米拉寫的,跟這盒菸,似乎是一種「東西」,異己,另類,都不能稱謂文章,而是「東西」。她小姑,你勸勸米拉,筆桿子咱不當了,咱還跳咱的舞,米拉才二十歲,腦子也好使,當編導也是有前途的。此刻劉團長退居幕後,說話的是劉導演了,話很真情,真巧愛聽。一眨眼,劉導演又讓位給了劉團長。劉團長說:我一直以為米拉是個心地單純的好孩子。最後這句話不好聽,真巧有些不高興了,好像米拉的「好孩子」是個大騙局,她從少年到青年在布這個局。
真巧轉達了劉導演的話,但沒有勸的意味。米拉馬上抓住綱領:留在部隊,只能跳舞,要想寫,走人。屆時米拉的窗口走過幾個男舞蹈隊演員,挺拔俊逸,一條條修長健碩的美腿,從全國上億條腿裡被選拔出來,他們說著最傻的笑話,用小本蒐集豪言壯語,同樣的豪言壯語出現在他們的批判稿和情書裡。但他們軀殼完美,走過去像一群移動的雕像。米拉說,再回去,跟他們一樣?真巧小姑懂姪女的意思:現在我米拉腦子開發出來了,再回去,那就要假裝沒腦子。米拉老了似的,慢慢搖頭:再說我現在這麼胖。真巧對胖了的米拉毫無歧視,反而更能在她身上辨認出老米瀟。她不知自己咋回事,是因為喜愛米瀟而鐘情米拉,還是反之。假如她對米瀟真的懷有愛,那也只是因為米瀟可能是她那個四散在世界各地的父系大家庭的一小部分,稀釋了很多很多的一小部分。而她對米拉的親,是因為她不能把這份親給米瀟。米瀟和米拉,都是真巧非血統街娃兒的人證。
剛才走過去那幾個,其中有一個,過去一直對我好,米拉忽然說。真巧問,哪一個?現在看,哪一個都無所謂。那時候,他給我一把鑰匙。房門鑰匙?米拉瞪了真巧一眼;你以為男女間就那一樁事。一把鑰匙,開了鎖,箱子裡放的東西,想吃就能拿。那你跟他好了嗎?「好」字在真巧嘴裡,是個動詞,少男少女幾年下來,他能不「好」你幾次,算白做一場男人。米拉嘆口氣,反正怎麼說真巧小姑都不會信。那個人後來把女朋友帶到團裡來了,米拉就把鑰匙還給了他。還的時候,是冬天,米拉獨自走進庫房,他那個箱子還在,打開後,發現裡面空空的,就放著幾件舊練功服。她把鑰匙扔在箱子裡,鎖上了鎖。再後來呢?他跟那個女朋友結婚了。媽喲,咋能想象那個位置原來是空給我的!米拉兩手把自己一抱,做個打寒噤的動作,幸免於難,後怕。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